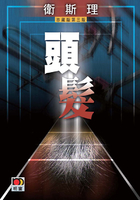雨,说到就到,霎时之间便倾盆而下,并且夹带着蚕豆那么大的冰雹,劈头扑脸打来,人们简直遮挡不暇。受惊的马,在雨雹中睁不开眼睛,狂乱地暴跳着,使人难于控制……正处于无奈之际,忽然发现靠左手树林中撑着一个帐篷。不知谁叫了一声,大家便不约而同拨马赶去。这帐篷在狂风中鼓胀着,飘荡着,像一只颠簸不稳的小帆船,而他们也正像坠水者抓住了救命的船边,不管人家是否答应,就一个紧跟一个钻了进去。
帐篷里,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牧童。起初他很惧怕,但经秋枝三言两语说明,他立时安定了,并且,喜形于色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张罗款待起来——他意识到自已是主人。
雷文竹摸摸孩子的头说:“就你一个人吗?”
“还有阿爸。他到大庄子上换盐巴去了,怕得要雨过了他才能回来呢!”
小主人在帐篷正中燃起牛粪,许是他觉着火苗太小,还不住往火上加些碎柴。而后他提议:
“快脱掉衣服吧!脱下来烤干!”(没有第二身衣服的牧人都是这样做的。)
经这孩子一提,大家不觉打量一下自己。他们淋雨时间虽很短,但已完全像从水里打捞上来的。特别是没经过这种遭遇的倪慧聪,更显得狼狈不堪。现在,她可怜地弯着腰,向上曲伸着两臂在拧落头发中的雨水。湿透的衣裳紧贴住身子,显现出她整个体态的轮廓来。
无疑,主人的话很对,如果不脱下衣服烤干,不仅很难度过寒冷的夜晚,明天也将无法上路。而且很容易受凉得病——雷文竹已注意到,倪慧聪牙齿在格格打战。看样子,她很难再支持下去了。
但,五个人围在火边。站着,谁也没有动静。
“我看!这么着吧!”雷文竹决断地对两个马车员说,“我们三个人还是赶到刚才瞅见的那个小庄上去歇一晚,明天大伙再一同走!”
“住得开!就在我们篷子里吧!”牧童连忙说,“等一会儿,你们烤完了衣服,我就把地下都铺满垫子,能住得开的,我们有毛垫子!”
“天都黑了!瞧!”秋枝接上说,“那么大的雨,怎么能走呢!你们准会迷路的!”
倪慧聪双手向后理理潮湿而粘连的头发,侧身朝外边望了望,对雷文竹说:
“得了!一块在这火边站站吧!也许雨就要停了。”
“不!这样的雨你不要指望它会很快住下。”雷文竹又扭头对两个不太情愿的马车员,多少带点逼迫的口气说,“走吧!”他说着先自钻出帐篷。
外边,狂风吓人地呼啸着。夜来了!雨更大了!
倪慧聪醒来,觉得闷气,为了不惊动秋枝,她轻轻掀开小主人为她们盖在身上的老羊毛毯,便悄悄出了帐篷。她在门口伸了个懒腰,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
拂晓的山谷是这样清爽而又恬静。除了草丛中什么小虫在唧唧作乐之外,什么声音都没有。群星,好像知道黎明即将到来,尽量在高空闪放它的最后的余光。天,异常的晴朗,如果不是遍地的积水,简直看不出昨夜曾经有过那样一场经久不息的暴雨……记起暴雨,倪慧聪便有些懊悔起来:那时,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把雷文竹他们强留住的。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找到了投宿的地方呢?找到了!一定找到了,山民们乐于收留遭难的行路人。可是,会不会真的走迷了路,走到什么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去?不会!这里离那小庄子原是很近的呀!她这样反复想着,走到了大树下。十几只母羊,同时抬起头来,用那迟滞的哀怨的眼光向倪慧聪望着,仿佛要对她诉说一夜受屈的苦衷。倪慧聪真有些可怜它们,鬼东西,忍着点吧!回到农业站,一切都会使你们满意。而后,她把斜搭在肩上的料布袋解开,想趁早把两匹马喂一喂,天一亮,便到庄上去找雷文竹他们一同上路。
就在这时,听见背后有什么声响。倪慧聪回头望去,只见四五条黑影快步向帐篷逼近。他们手中好像提了什么,是枪!到了帐篷口,一个留在外边,猫腰探头向四外窥测着,其余三个一拥而进。
接着,帐篷里传出秋枝尖厉的撕裂夜空的惊叫和那牧童的嚎哭。又接着听见激烈的挣扎之声。
“快!快呀!”站在外边那人粗野而慌张地嚷道,“快拖出来!拖出来!拉走!”
坏人,是坏人哪!
倪慧聪发根骤然一紧。她本能地从地上抓起两块石头,她要冲过去,去救援秋枝……但,她猛地止住了步。她觉悟到,凭自己单单一人,凭手中的两块石头,怎么去对抗四五个持枪行凶的人呢?那不仅不能解救秋枝,定会一同被拖走,一同被杀死。看来只有赶紧到那小庄去,赶紧去把雷文竹他们找来。于是,她扔掉石头,迅速从树上解开马缰,两手一扶,纵身跳上马背——平时她绝不可能这样跳上去的——又在马胯上拍了一巴掌。那匹精灵的马,好像也明白目前情势的火急,它一动步便纵驰如飞,烂泥积水从蹄下四溅起来。
不消说,这匹跃走的快马已被发觉!随即枪声响了!一枪、两枪、三枪……
倪慧聪只觉有人从背后搡了一把,用力是那样猛,几乎把她推下马去。她双腿夹紧马腹,把身子俯低,尽量俯低。心中不住地对着马说:快!快!还要快!求你再快些吧!
靠近山庄一带是凹凸不平的。马,像一辆将要倾翻的车,开始乱颠乱撞,倪慧聪前倒后仰,扭动身体,拼命地保持平衡。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备上皮鞍。忽然,马头向下一栽,打了前失,倪慧聪随着扑到马脖颈上去了。她双手死死抓住马鬃,而这马又忽地跃将起来,不择地势向前奔去。这样,倪慧聪便像表演骑术似地被悬吊在马颈上,丝毫不敢松手。终于,在跃越一道相当宽阔的壕沟时,它把它的骑者摔开了!摔开去好远好远。
倪慧聪腾空跌落在地上。轰然一震,她觉得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大约是感觉到背上的负荷突然取消,那匹马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倪慧聪跟前,垂下头去,在她身上嗅了嗅,无可奈何地喘着气,打着鼻响。随后,又高仰头颈,抖动着长鬃,连连向远方嘶鸣起来。
倪慧聪似乎是被这马嘶惊醒的。她很快恢复了知觉。她觉得浑身酸痛麻木,她觉得神志昏眩沉重,像通常在恶梦中所有过的,欲言不能,欲动不得。她强撑着想要挺身站起来。可是她摔倒了。右腿失效地折曲着,支不住身体,仿佛是一条不属于自己的假腿。她明白了,这腿被摔得脱了臼,她再也不能站立了!于是她顿时感到一阵寒心,感到软弱无力,也感到孤单无助,她甚至要哭叫出来了,然而那四条黑影又在她眼前显现,秋枝的惨叫也在她耳边响起。她立刻觉得神志真正清醒过来了。她奋然将头一扬,把散落在脸上的头发甩到后边。她决定爬!爬!爬到那小庄子上去。
像是在游泳;倪慧聪的两臂交替着向前伸去,手,抓住草根。胸部匍匐在泥泞中,脱臼的腿死板地被拖带着,在身后留下一条车辙似的印痕。她爬着,竭尽全力向前爬着……
雷文竹和马车队员听见连声枪响,预感到有所不测。他们没讲什么,一骨碌站起来,提枪冲出土房拉了马就走。有几个前往相助的青年山民也掂着老式步枪紧紧跟随在后边。
倪慧聪抬头见几匹马闪出村口,向她直奔而来。可以看出,为首的骑者便是雷文竹。她随即摆着手向他们呼叫道:
“不要!不要到这里来!快去……那边,帐篷那边!……”
倪慧聪竭力喊叫,觉得自己的声气很大。事实上,她那沙哑的、颤弱的、仿佛被窒闷了的叫喊根本没有被谁听见。他们仍旧驱马朝这厢奔来。
到跟前,雷文竹一切都明白了!
当他跪下一条腿,俯身去抱起倪慧聪来的时候,发觉她右肩上有血。血,隔着衣袖浸透出来。血,染红了她所匍匐的一片土地。于是,雷文竹毫不犹豫地扭住倪慧聪的领口,顺手从她的衬衫上撕下一块布,迅速地包扎住伤口。
直到这时,倪慧聪才知道自己受了伤。而她一知道,便立刻觉着剧痛难忍。她咬住下唇,忍着。并且拒绝别人扶持,用责令口吻,对雷文竹和两个马车员说:
“怎么还呆在这儿!秋枝,秋枝……被拖走了!拖走了啊!”
雷文竹异常激动,紧握了一下倪慧聪受伤的手,把她交托给几个山民。他和两个马车员跃身上马,拼命挥着鞭子向帐篷那边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