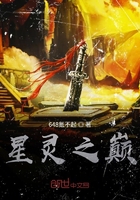雷文竹也随着站住,林媛这么语气严重地一问,他有点慌了。仿佛他的话将会引起可怕的后果,于是他忙接上去改口说:
“……我是想提醒,提醒你经常留意气温突变。要不然,到临时我们应付不了……走吧,再往前边转转!”
别说这位技术员关于气候问题的提出是那么做作,即使他的嘴再巧些,也不能挽转自己造成的局势了。林媛不缺心眼,只听他那句少头无尾的话,她心中已经有了七八分。等他再慌神慌气一改口呢,她全然明白了。转念之间,她已经肯定了事态的全部真实。她本无须乎再要他提醒什么,无须乎再向他探问什么。但,她不相信,她不承认。她不愿意承认。所以她还是要向他探问,不,简直是追问,仿佛女畜牧师申请调走的动机只有雷文竹才了解,而他却替她百般掩藏。
雷文竹含混其辞,笨拙地拖延了一阵,终于无可奈何地说:
“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想……可以说,这,也许和你有些关系!”
这话是林媛已回答了自己的。可是,听到由另一个人口里说出,仍然不免为之一震。她偏过头,站立在那里,仿佛思想和周身的神经都已凝结了。她的失神的大眼睛,呆呆地盯着去而不返的河水。
而雷文竹却因为这样点明道破的话语而立刻镇定下来,立刻变得冷静如常了。他用类似教训的口吻接上说:
“他们是同学,无论从哪一方面比较起来,他们都在先。只是说相识吧,也要早得多。当然,我不是说,你没有那种权利。可是,你做什么要妨碍别人?难道你能够看着一个人因为你感到痛苦?”
林媛依旧没动,没作声,她没听。
最后,雷文竹还慎重地补充了一句他认为必要的不可不说的话。但,当他要说这句话时,却侧过身背着林媛,似乎他的话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着荒野,针对着夜空。同时,声调是那样困难,还带着竭力避免的颤音:
“你要知道,她爱他!她很爱他!”
5
倪慧聪今晚就寝特别早,但她不能人睡,久久不能人睡。
她带着羞愧的心情回忆起当她拿到农林厅公函时是怎样高兴;她马上就到长途汽车售票处,担心着还会有所变更。接下去,又记起到农业站来的第一个夜晚:
在公路终点,她就迂回着由陈子璜口中探知了一项足以使她感到扫兴的消息——兽医到牧区去了,过一个月才能回来——她所以没把自己的到来预先告诉苗康,原是想使他喜出望外的。尽管如此,总还是到这里来了呵!
当晚,所有的人都忙于整治步犁,安装拖拉机,几乎没有谁顾到女畜牧师。好在站长特意嘱托过林媛,因此,她以对待每个新来人的热心招待了倪慧聪,以至使后者无法过意。她还抱来很多干草,在自己室内的另一端为倪慧聪打了一个舒适的地铺——按说,畜牧师不仅应有单独的住室,而且还应该有办公室。没办法!唯独马车队旁边还闲着一口土窑,但又颇有倒塌的可能。
林媛有这样一种习性,或许是本能,凡是跟她年岁相仿的女子,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情:爱说好动的、稳静拘谨的、谦逊的、傲气的、热情的、怪僻的——她全可以跟你一见如故。她能够迅速地消除你和她之间的距离,促使你当即跟她熟识起来。倒不是这个女孩子有什么独到的本领,事实上,她不过是凭着自己固执的、火一般的亲热,以及主动的、推心置腹的攀谈。而对于倪慧聪,当然就愈发不能例外,因为,这是她唯一的将要长年共处的女伴,不!女友。
就寝之后,气象员结束了关于农业站繁琐的介绍和解答,开始向女友询问起来:
“哪儿人哪?”
“东北,哈尔滨!”
“怎么南方口音挺重的?”
“从不满两岁离开,直到现在,我还没去过东北。‘九一八’以后,我们家逃到天津,‘七七’事变那年,又逃到重庆。”畜牧师回答说。
“重庆我去过,什么都好,就是太热,像个大锅炉。……那么说,你从初小到专科都是在重庆上的?”气象员又问。
“不,专科在成都,金陵大学由南京迁到大后方之后分出来的。”
“哎!你一开始怎么选上了这一门的!”林媛更认真地问,“听说畜牧科女同学很少很少,几乎没有!”
“谁晓得!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总之是很喜欢!你呢?怎么选上气象这一门呢?学了多久?”
“什么学呀!根本不能算学过。我爸爸,你知道不?就是此地工委书记,带我来,可是做什么呢?我什么也做不了。正碰上这里要气象员要不到,就把我给送到航空局去,请人家大致教了教。今天还是一知半解,不过勉强应付应付就是了。本来我是想去考学……?”
“考什么?”
“艺校。”
“呵!要当歌唱家是不是?”
“去吧!听我这豆沙嗓门。怎么能唱歌呢!我是想学跳舞,小时候在剧团里跟一个白俄练过芭蕾。可是,只能算胡来!在那种环境当中,谁有心思真正学点什么!还不是……”
“我听人说基本训练很重要。你既然经过基本训练,那就有了一定条件,如果能够再……”
“得啦!你知道,做一个舞蹈演员当然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狈重要的一项是身材。看我!”林媛自己笑起来,那么坦然,“再过些日子不知更要胖成什么样子了。我真羡慕你!”
“快别提我吧!笨死了!”倪慧聪也笑起来,“在学校连课间操都做不好。”
如此,话一扯开,题目相当宽广,并且变化莫测。最后,以青年女子们纵情畅谈时所不易忽略的一个项目做了收场。
“恋爱了吧?”林媛问。
“你呢?”倪慧聪以攻为守。
“怎么说呢!也算也不算。”
“为什么?”
“其实,不过只是日常那么在一起聊聊。我的意思是说,还并没有,并没有肯定什么……可是……”
“可是各自都明白!是不?”
这话在林媛听来格外快意,以致使她全然沉浸到陶醉的感觉里去了。但,她总还没有忘记用显然是故意的、淡漠的口吻说:
“不过,我倒并不希望太快。干嘛那么早?慢些可以多了解,缺乏真正的了解怎么行呀!况且,在一起的日子还长……”
“这么说还就是我们农业站的?谁呀?”
“反正,以后你自己会知道,现在告你说你也不认识!”
倪慧聪猜想林媛隐告名姓的不是别人,正是和她同路的那位农业技术员。这并非有什么根据,因为她在汽车上就曾奇怪地想过,像他这样的,对于姑娘们“危险”最大。现在,她甚至已经在替林媛感到满足和高兴了。
“他担任什么工作?”倪慧聪的语音显然是明知故问的。
“兽医。他是我们团支部组织委员。”
“……!”
对方不作声了。一直不作声。
林媛如梦初醒,记起了畜牧师的旅途劳顿,于是颇有歉意地结语道:
“哟!看我,你一定困极了,睡吧!”
倪慧聪不能入睡,久久不能入睡。
相随这些回忆,产生了一个敏感的疑问:天这样晚了,大约已经快到了做记录的时间,气象员怎么还不回来呢?她揣度着,想像着……,终于,她作出一个决定——明天搬出气象台——既然这样,你应当退避,自觉地退避。为什么要站到别人当中?为什么要让人家感到碍手碍脚?但,她存心冷静地劝戒自己的当儿,两颗滚热的泪珠从眼角悄悄滑落到枕巾上去了。
6
和林媛分手后,雷文竹没有回家,却独自沿河而下,继续蹓达了很久。此刻,他的心境是异常矛盾的。时而,他觉得内心很平静,甚至很满意自己。今夜和气象员的谈话他事先并没有明确的打算,而是临时意识到的。然而这谈话对于他,却仿佛是完成了一件有准备的、重大的工作。对的,我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就又当别论,既然是知道,那我就有责任……不过,雷文竹内心却又禁不住有些纷乱,以至于懊悔起来。他简直弄不清刚才的行动是为什么,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是谁的事就让谁随意好了!他开始承认,这样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甚至是愚蠢的……
雷文竹仰起脸盲目地走着,忽然发现前边有人影,月色朦胧,看不大清。只见那人把一匹马赶下河去,随即很熟练地从溜索上滑过河去了。雷文竹想起了上月里轰动更达的那帮偷马贼。他立即警觉起来。但那人过河以后并没有上马而去,却从马背上卸下了什么东西。接着,雷文竹模模糊糊看见他摸索着把牲口套了走来,开始在耕作了。有这么勤俭的人哪!几乎是半夜了,还到地里来,是谁呢?
这是老斯朗翁堆。
前两天,农业站第一期步犁训练班开课了。附近各庄都有人来报到。但是,当地最富有经验的老农斯朗翁堆却没有来。站长陈子璜觉得这未免有些煞风景,就亲自去请他。但他不在家,割草去了。
步犁训练班全部课程都是套着牲口在坝子里进行的。所以,除去报过名的正式学员之外,常常簇拥着更多的“旁听生”。其中包括那些来往过路的外乡人,起初,他们只是由于好奇想凑过来看看热闹,但是,他们的好奇很快就被好学代替了。他们往往大吃一惊,猛然觉悟到在这里耽搁太久,误了行程,于是不得不快马赶路
斯朗翁堆上山割草时,步犁训练班正在上第一堂课。他本想绕弯来看一下,但是被路遇的叶海折了兴头。
叶海从地里回去取修理工具——拖拉机出了点小毛病——和斯朗翁堆走了个碰面,他随口招呼道:
“忙呵!到哪儿去?步犁训练班你报名没有?”
“报名?”斯朗翁堆反问。
“报名。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唔!这么说你没报。那你去瞧瞧吧!呶!在那里!”叶海指指忙碌的人群,“你瞧瞧!瞧我们犁地是怎么个犁法,瞧我们套牲口是怎么个套法。快去吧!”
叶海讲话时带着明显的挑衅的神色,并且扮出一副狡狯的、胜利的笑脸,这立刻就使老斯朗翁堆更改了他原来的打算,他一面转身走去,一面拒绝道:
“不!没工夫呵!我要割草去呢?!”
为了套牲口的事,斯朗翁堆曾经过于憨直地教训过朱汉才和叶海,后来他暗自有些愧感了。(那时候,谁晓得他们竟是两个会驾“狮子”的、有能耐的人呢?)不过,叶海刚才的态度却实在使斯朗翁堆不快。尤其是对一个上了年岁的山民,这简直是一种伤害,他从心里恼了:为什么非得去瞧瞧你们犁地怎么个犁法?为什么非得去瞧瞧你们套牲口怎么个套法?我自己不会犁地吗?我自己不会套牲口吗?
然而,在事实面前,斯朗翁堆常常是屈服的。
几个要好的邻人见斯朗翁堆没到训练班去,黄昏时不约而同都到他家里来闲坐了。他们谈起“狮子”,语气总是客观的,仿佛是谈着神妙莫测的事。但一谈起步犁,每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形容和热情的评语。原先,斯朗翁堆最担心牲口吃不消。可不是!牲口木犁还拉不动呢,更不用说这种全身是铁的步犁了。但据这几位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恰恰相反,步犁虽全身是铁,但轻巧得出奇!根本用不着抡鞭子,只消吆喝一声,牲口就会毫不吃力地往前走去。对掌犁的人来说,那就越发省劲了;你只消松宽宽地扶住就行,根本用不着曲背弯腰去按住犁身。至于犁铧,斯朗翁堆就想不出它会有什么用场。但据学员们述说,犁铧简直像一只万能的手,它把翻起的新土顺序拨到一边,把杂草严严地压住……总之一句话,步犁是无可非议的。
斯朗翁堆不能不从实际出发为自己盘算一下: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也到农业站去借一头牲口借一架步犁呢?天气一天一天在变,母牛又不知什么时候生犊子。那几块地总搁着不翻,等上了冻可怎么办哪!可是,他又有些不甘心这样做。别人会怎样谈论呢?看吧!老斯朗翁堆终究也还是米求农业站了!特别是朱汉才和叶海,他们会怎样来奚落这个老头子呢?再说,步犁是不是真的就那么灵便!这也还不一定。最后,斯朗翁堆要求邻人把借来的马和步犁转借给他。他要亲自到地里来做一番考察。如果步犁
不得力,那也就死了心;如果步犁真的那么灵便,那就趁天黑,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两块河湾好地翻一翻,其余的以后再打主意。
雷文竹想知道这是谁黑更半夜到地里来干活,他不声不响从溜索上过了河。斯朗翁堆刚刚开始耕作,见雷文竹意外地出现在面前。他不禁有些惶恐起来,仿佛自己是在干一件不名誉的事。
“我当是谁呢!你呀!老斯朗翁堆!怎么这时候下地呢?”
“我……横竖也睡不着,我是想……”老头子支吾道。
“唔!在做试验!好啊!好啊!”技术员高兴极了,他原以为这老头子要固执到底呢,“怎么样?这东西还可以吧?”
雷文竹这样兴致,使得斯朗翁堆也立刻自然和快活起来。
“倒是顺手,很轻快,不过要是能再犁深点,犁宽点,那就越发管用了!”斯朗翁堆遗憾地回答说。
“怎么!太窄吗?来!我看看!”雷文竹接过步犁。
斯朗翁堆尽顾忙着到地里去试用,他只简单听人家讲了一下。关于如何调节犁沟深浅这一层技术,他并没有弄明白。现在,经雷文竹一指点,他才吃惊地发觉,原来步犁不是件死的,而是件活的东西。你只消把那根小铁棍抽出来换一个孔洞,犁沟的深浅宽窄就可以随之发生改变。斯朗翁堆被这意外的发现震惊了。当他亲自调整了步犁,得心应手地继续耕作时,欢喜得直对牲口乱喊乱吆。
雷文竹跟在背后走了几趟。他很赞叹这老头子的粗糙而灵巧的双手:
“斯朗翁堆!你明天到农业站去扛一架步犁来使唤吧!用不着进训练班。你完全可以自己使用它了!”
“那!牲口呢?你晓得,我那头奶牛怀着犊子。”斯朗翁堆带着坦率的、感激的口吻说,“要是能行,我还想借头牲口,用不了很久,也就是几天的工夫。”
雷文竹想了想答应道:“行!我给站长说说,就从马群里抽给你一匹。”
“你说马?我是想借一头犏牛。马是打仗才……唔!这没有什么两样,就借给我一匹马吧……唔!对!我想起来了!”斯朗翁堆变得那样兴奋,显然,他对自己忽然产生的念头感到非常满意,“你刚刚提到马群,不是说农业站要找一个放马的人吗?”
“是啊!我们打算请一个放牧员!”
“你看我那个小女子能行不?要是行,明早上我就叫她去。横竖她在家里也做不了什么事,光知道耍。”
7
放牧员秋枝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热心,每天傍晚还要和她的“拈香姐姐”一同到马厩去切草。按说,这项工作不在放牧员职责以内,也不在畜牧师职责以内。因为饲养员白天在步犁训练班忙一天,黑夜还得起床几次喂牲口,她们俩想自动帮他们做点事。同时,这些天女畜牧师的心情也不好,她不愿意有一刻的空闲,所以尽可能往自己身上揽些事情干。只要忙着,心里就会稍为轻快一点的。
秋枝双手挟着干草向铡刀下掖着,一面仰起脸来问:
“倪慧聪姐姐!你说,真的能学会吗?”
“你眼睛要看着点呀!小心我把你的手指头切掉。学会什么?”倪慧聪吃力地按下铡刀,她的头发,随着身子的动作一抖一散。被切断的碎草从刀口处飞溅起来,“唔!你是说学会驾‘狮子’,是不是?能!怎么不能呢?谁都能学会!”
……这些天,拖拉机在耕靠河岸的一条地。每当夕阳西下,马群走出山谷到河边饮水时,秋枝就从马上跳下来,向“狮子”跑去。于是,朱汉才会立刻煞车,让她上来,在机器轰鸣中提高声音给她讲述:怎样转弯,怎样倒退,怎样可以走快些或走慢些。并且还让她坐在他的位子上——这位子软软的,能够把人弹得一跳一纵——他甚至放心大胆地让她驾驶了不短的一段。她紧紧握住震动的方向盘。这时,她的心充满了欣喜而又充满了恐慌。她高兴,当这奇怪的圆盘完全在她把握之中,“狮子”照样驯驯服服地在向前走。她又害怕,也许“狮子”会趁着朱汉才没有亲手捉它,突然乱拐乱窜,或是暴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