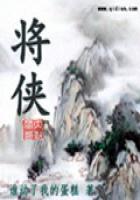五月初四,天阴如铅,乌云滚滚,隐隐见得些闪电。
顾沉衣深拧着眉,站在常家府宅门口,抬头盯着那微有些歪斜的匾额,右手合拢的扇柄正往左手上一打,周遭就听得“啪”地一声轻响。
附近冷清清无一人,连偷食的猫儿都不曾路过。风卷得杂物满地都是,灰尘极大,连那贴在门上的“封”字也染了几分飘摇之感。
身后的两小厮面面相觑,几欲上前跟他说话,却又有些担心犹豫。踟躇了许久,方才出声道:
“公子……咱们回罢?”
顾沉衣收了目光回来,闲闲瞥了他一眼,眸子里倒看不清是什么神色,那一个不敢再开口,旁边的就只得站出来接着劝道:
“公子,老爷说了,不让再和常家人有联系。您往这里来了好几次了,恐让他晓得了,咱们俩可都得挨骂啊……。”
顾沉衣笑了一下,不以为意地看他:“怎么?你是怕老爷多一些还是怕我多一些?”
“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公子。”那边那个这才有胆附和,“这主要是咱们家以前还向常家提过亲,本来就很惹人怀疑了。要是再看见您往这里来,那些个多嘴的难保不会去偷偷添油加醋,万一让人说是我们勾结常家通敌卖国这怎生是好?”
“是啊公子,如今情况非常,您就别再和老爷抬杠了……。”
“行了——”顾沉衣不耐烦地挥了挥扇子,往他两个人头上分别敲了一记,“一口一个公子,这口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公子呢,到底是谁主子,嗯?!”
“是是是,小的知错了,小的知错了。”两个小厮赶紧跪下来认错,“自然公子才是主子,小的一辈子都是奴才,公子息怒啊公子。”
“诶……。”顾沉衣听得他们这话,又不禁头疼地摁了摁眉心。
到底这事情来得突然,哪晓得常知书会被人参一本,且证据确凿,不过一日就被抄家处斩了。
他将折扇往腰间一插,一手提着地上那两小厮的衣领往前慢慢走,心里却是不由担忧。
常歌那日跑了,能勉强躲过此劫确是好事。可是如今亦不知她身处何处,又知不知道家中所出的这事情。如若她并不知晓,或是知晓后仍想跑回来看一看……要不信被朝廷追捕的人瞧见了,那可就……不妙了啊。
白云台在灵山山峰之巅,像是祭台一样的东西,成方形,四个高大石柱竖在四角,柱上刻有许些古怪纹饰,凑近看时,那石台之上亦雕了不少符文,凌乱里带着有序的线条,异样的气氛诡秘的压抑。常歌未敢细看,移了视线,转向别处。
桑鬼早早便就到了,仍旧是一身黑色的精锻长袍,只是今日连里面的道袍也没有穿。空城就站在他不远处,背对着他,一个人望着对面的山峰。
这里很空荡,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除了他们几个以外若还说要有的,大概就是头顶的浮云,洁白无尘,绵软又清浅,静静躺在苍穹之上。
是不是正因如此,所以才有名为“白云台”?
“来了?”
桑鬼对着非墨颔了颔首,表情淡淡的。
非墨没有答话,只把肩上的两个布袋扔给他,未置一词。不知道是不是赶路太累了,他显得比她还要疲倦。
空城走上前,拉开袋子的一角,看了看,莞尔道:“挺好的。”他起身,数着旁边的几样的东西,喃喃自语。
“千人血,百狼胆,沉渊太极,活死人,白骨。”
偌大的两个酒缸里传来阵阵腥臭味,不用想也知道那是什么,常歌微有些厌恶地捂着鼻子,小心往后面退了一步。
空城自将她动作看在眼里,不觉笑道:“你们也幸苦了,先去后面的小屋子里休息休息罢。这里由我和桑师弟来布置,若无意外等明日辰时一到,就能开始了。”
“……四师父。”常歌轻轻唤了他一声。
“嗯?”空城回过头来,“怎么?”
她咬了咬下唇,看了非墨一眼,然后又垂头,“你这法子,当真……行得通么?”
默然半晌,他抿唇一笑,伸手往她头上摸了摸,“不用担心,明日你就只管睡觉。等醒来,四师父就能送你一个活生生的公公。”
“……。”不明白为何,这原本应是调侃的话,在她听来却半点感觉也无,胸口闷闷的,空气里竟是压抑的气息。
非墨伸手牵着她,柔声道:“我送你去歇息。”
常歌无力地点点头,由他领着往那间简陋的木屋里走去。
屋子的确很狭小,但幸而床还有两张,倒也不必尴尬睡觉的事情。常歌和非墨都累的一身疲惫,几乎是头一挨枕就睡着了。
夜里,屋外的风很大,吹得门扉咯咯作响。
眼皮外照进一点灯光,朦朦胧胧的,非墨皱着眉缓缓睁眼,透过半掩着的小门,尚能看见前厅里亮着的光芒。
看这般时候,已经子时过了,会是什么人?
他心中奇怪,随便披了件衫子就下床,推门走出去。
桌上的油灯被缝隙里进来的风吹得摇摇晃晃,常歌一个人坐在前面,头微微有些耷拉,白日里绑在脑后的那一把青丝如今都散了下来,覆在背上。长长的黑发一直垂到腰间,昏黄的颜色映在她脸颊,头一回,非墨觉得她其实很柔弱,甚至比寻常女子更加不堪一击。
以往,她一向是不服输的,唯一一次在他面前哭得伤心欲绝也是那日知晓自己身世之时,但即是如此打击却也没见她消沉多久。
仿佛她的心情总是很好,只有看着她笑,他才会感觉心中愉悦……
他原以为她就该如此,哪怕没心没肺也好,哪怕打他骂他也行……只要不受伤,不难过。毕竟……他能给她的,实在太少了。
常歌把排在手边的几枚铜钱慢慢翻开,炉上的轻烟缭缭升腾,随着火焰的方向流动得缓慢。
她嘴唇略有些颤抖,指腹在铜钱凸出的纹路上来回抚摸。
这一卦,是大凶。
肩上忽然沉了一沉,她吓了一跳,反射性地浑身轻颤。转头看去,才发现身上搭了一件薄毯。
非墨眉眼含笑,自在她旁边坐下,拉了她的手在自己怀里暖着,温然道:
“作甚么还不睡?”
“没、没有什么。”常歌不动声色地把桌上的铜钱收起来,勾了勾嘴角,反而问他,“你没睡好吗?怎么起来了?”
“没有。瞧见外面灯亮着,我就出来看看。”他老实回答。
“……吵到你睡觉了?”常歌忙站起身来,拍了拍灰,“我还是回屋里睡的好。”
才走出几步,手忽然间就被他拽着,非墨稍稍用了一点力,就将她拥入怀中,闭着眼小心叹了口气。
“是不是近来心情很不好?……我看你好像有些心神不宁。”
常歌脑子里凌乱至极,几下从他手里挣扎出来,摇着头道:“没什么,兴许是有点担心,我如果现在叫你放弃,你肯定不愿意的罢?”
非墨微微一愣,不知怎么回答。
常歌也没给他太多时间考虑,只轻轻道:“你要救你爹,是人之常情。唉……我睡觉去了……。”
她说完低着头掀开帘子走近里屋。
忽来的风,把灯光吹熄,薄薄的一缕烟瞬间消散开来,眼前便尽是黑暗,非墨在原地默然许久,终究靠在那墙上,合上眼,长长叹息……
遥远的北方,汴梁宿姓府宅的小院中,明亮的烛光自窗户映照而出,隐约能瞧得不少人影攒动,府里的下人忙忙碌碌端水端药,在如此本该寂静的夜里显得分外的吵杂。
屋内的床上躺着一个十来岁的孩童,额上满是汗珠,嘴唇苍白龟裂,双目紧闭,面无血色,似是难受非常的大口喘气。
红药替他施了针,又取出一粒丹药来喂他服下,看着这孩子脸上的痛楚勉强消除了些,站在旁边的宿姓夫妇不由喜极而泣。
“师姐,这孩子的病……。”石青上前一步,深皱着眉问她。
红药摇了摇头,眸中惋惜,“是中了毒。幸而毒素尚未伤及他五脏六腑,性命还可保住。”
宿家夫人哭得泪眼滂沱,上前抓住她的胳膊,声音凄厉:“道长,求你救救小儿罢。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倘若他去了,索性让我也陪葬……。”
“夫人,你且莫慌。”红药握着她的手,宽慰道:“令郎并无性命之忧,不过他所中之毒十分厉害,我目前也无法调制出解药,为今之计只能先将毒逼至他腿上,但是……恐怕自此,令郎的双腿可能就……。”
那边的宿老爷蓦地一震:“……道长的意思是?”
朔百香同情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我师伯的意思就是您儿子往后恐怕就要坐轮椅过下半辈子了。”
“百香。”苏卿无奈地用手暗暗掐她胳膊,低声道,“好生些说话。”年纪也不小了,却总是不分轻重。
“我又没说错。”她不以为意地挣开他的手,颦眉不悦。
“……。”思量半晌,宿老爷咬牙狠下心,别过脸哽声说道:“道长只要能救我儿子……便是如此,也认了。”
“宿老爷不用太过担忧,其实若能找到解药,想彻底根治此毒也不是无可能。”红药对着苏卿颔了颔首,吩咐道:“师侄,你且将方才宿少爷吃的那盘糕点拿与我看看。”
“是,师伯。”苏卿依言,把桌上的食盒提了来给她瞧。
朔百香看得分明,连忙摆手辩解:“师伯,我可没下药啊。”
“你放心。”红药笑着宽慰她,“我知道不是你。”
取了手边的筷子将糕点分开来,凑在鼻下仔细嗅了一嗅,继而便放下食盒,面向着石青,淡淡道:
“师弟,这毒,的确是桑师弟所下。”
同门师兄弟,自是清楚对方功力深浅,此毒毒性甚猛,想是原本用作对付他而制,却又怎知他会将糕点推赠于宿家的孩子。如今害得这般年幼的孩童受毒蚀骨之痛,倒不如当时他自己吃了为好!越想越觉胸中气闷,石青手握成拳,青筋突起,往桌上狠狠砸去!
“混账,他简直是胡闹!”
红药眸色复杂地看着他,轻摇头:“事不宜迟,我们需得赶紧去灵山白云台。”
“桑师叔杀了那么多人,又盗取了玄溟鬼域的宝剑,只怕要找他算账的人还不少。”朔百香笑着用手肘捅了捅身侧的苏卿,“你说是不是?”
他闻言,只敷衍性的扬扬嘴角。
脑中却浮起那日夜里同非墨说过的话。
——“你要觉得不做便无法安心,那何不尝试一下?凡事要难以抉择那就不要抉择,顺应自己心意去活。”
会不会正是因这句话而误导了他?
联想他近来的所作所为,那一日烦恼之事应当便是这个。
只可惜他当时并不知晓他盘算着什么,要早知他是计划如此一件荒谬的事,他也不会说这番话了,只是如今要追悔,好像也有些晚了吧?……
刮了一夜的风,今日天刚亮时,天色就暗沉沉的,似乎随时可能将下雨。
因晚上睡得并不好,常歌醒得也很迟,睁开眼时,就听见耳边吵吵嚷嚷的,不时还有刀剑相碰之声。
这个时候,辰时想来已经过了!
脑子里尚存那丝模糊此刻也猛地清晰起来,她顾不得多思虑,匆匆起身穿衣,随意洗漱了一阵,拉开门就往白云台的方向跑去。
雨前的清晨,大雾弥漫,远远看去,就如白云飘渺缭绕,聚散飞卷,染着些许仙境之意。石台上正见桑鬼和空城盘膝分坐两端,合着眼,面色沉静,两手轻放在膝上,似是耗用内力过度,自他二人后背处不时就有白色烟气冒出。
台之中央,摆着那具完好无损的白骨,白骨两侧分别放有那两具已有些腐烂的活死人身躯,上面全是鲜血,想必是用千人之血浇灌而成。
干长九和非墨负手站在旁边,静静看着台上的变化,耳畔却尽是叫骂之声。常歌微喘着气,转头望上山的斜坡处瞧去,这一看却让她吃惊万分。
那坡上黑压压一片竟都是人,自衣着看来,有青衣的玄溟鬼域弟子,朱色衫子的朱雀帮门徒,以及南面并不常见的凌风岛门下弟子,少说也有两三百的人。看样子都是冲着他们而来,但前面只仅仅有桃花山涧的弟子尚在抵挡,原本桃花门中弟子就不算多,虽靠使毒还可撑一段时间,可眼见实在是万难取胜。
“姓桑的妖人!”行在前头的乃是玄溟鬼域的白长老,他年纪瞧着不过而立,但据说武功深不可测,已有七八十年的功力,连派中掌门亦要礼让他三分。
“速速将我派宝贝还来!”他言罢便挥剑斩杀那扑来的桃花门弟子,冷哼道:“否则,我立刻就让你的徒弟全葬身此地!”
“师父——”眼看他并非是玩笑之话,到底是不愿看见门中师兄弟死伤成那般,常歌焦急地往桑鬼那边跑去,正要开口,却不想非墨一把拉住她回来。
他皱着眉提醒道:“小伍,师叔眼下在运功,不可扰他。”
常歌指着山下就将杀上来的人,有些语无伦次:“那……眼下该怎么办?再过一阵,其他弟子或许都会死的。”
坡上的江湖群雄仍旧喧哗不断,高声怒骂。
“桑鬼!你这杀人不眨眼的妖道。我今日就要替天行道,亲手取你性命!”
“桑鬼,你杀我门下那么多的人,我要你偿命——!”
“桃花门不愧为江南第一邪门毒派,往日只道你还算安分,没想你居然下如此狠手!你就不怕遭天谴吗?!”
“杀了他!杀了他——!”有人高呼。
不知是自何处飞来的一支羽箭,斜斜往那边的桑鬼身上逼去,非墨抬眼,瞬间闪身过去一把接住。
“来了,来了!”
人群里忽听得这般喊叫,不过片刻,群情汹涌,就闻得数人兴奋嚷着。
“是石青道长!石青道长来了!”
听到这人名字时,桑鬼眉上才微微动了一下,他缓缓扬起眼皮来,神色有些不宁,甚是不悦的往非墨那边看去,沉声问道:
“他如何来了?我不是让你给他下了毒么,是你心软了?!”
非墨亦心中奇怪,他眸中一凛,摇头道:“我也不知……我确实是已下了毒在他食物之中,不明白为何会……。”
未等他道完,常歌便一把揪住他,不可置信地望着他双目,嘴唇轻颤,“你……你给你师公下毒?你竟给他下毒?!”
“不是的小伍……。”他这一瞬觉得有些解释无力,只能摇头道,“不是你想的那样。”
“非墨。”桑鬼不欲听他们两个纠结这事,方才那瞬的失神已让他体内气息凌乱,如若再不归整,只怕会前功尽弃。
“你去顶着,只要撑半个时辰,一切就好了。”
“……半个时辰?”他眼里犹豫,想起对方是石青便不禁轻咬了咬下唇,踯躅着,“我……不敌他。”
“我当然知道你不敌他!”桑鬼不耐烦地喝出声,“只是叫你撑半个时辰,莫非你连半个时辰也撑不了吗?!”
“我……。”看他仍迟疑不决,干长九上前来,索性一把扣住他胳膊就往坡上推——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让他不由踉跄往前迈了几步。正一抬头时,对面便就是石青的那双阴冷的眸子,半点情感也没带。
他无端的心虚,像是做了贼一样,根本不敢去正视他……
朔百香和苏卿分立在他两边,看得非墨过来,亦是心情复杂,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道起。
就在此时,头顶的天空猛然响过一道惊雷,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