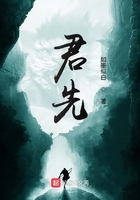‘船不靠岸,加强守卫’这八字命令于船室下达时,守卫们并没有特别在意,只当做是船内的大人们要乘船观赏这淮河雪景。
某个晕船的守卫,私下里还打趣的说,这淮河结冰下雪我看了二十几年,到现在也没看出那叫什么兴来。我感觉还是娘们身上那俩兔子更有那什么兴,看着有那个兴,吃着捏着更有那个兴!这守卫说完引来一阵哄笑,本来也相附和着笑笑,嘴巴一张就跟黄河泛滥似得,趴在船栏杆上吐个不停。
一众守卫在自己晕船同伴的呕吐声中一过就是三天,这三天对那八字命令不以为意的众人,从脸上的轻松写意慢慢变得神情严肃起来。这倒不是那帮跑江湖的人,乘船追杀而至,而是源于在耳边回响了三日的乌鸦叫声。
说来也怪,自从那日命令下来,船室内的大人便没有出过门,连每日送上的瓜果饭菜也原封未动放在门前。
那晕船守卫是众人中出了名的口无遮拦,有一夜大人们住的屋子传来剧烈的几声呻吟,回去后就跟自己好友打趣说屋子里的四位大人有龙阳之后,估计正在里面一丝不挂缠绵着。你看这头上的乌鸦没,这八成就是老天爷看不过去,叫他们别干这些伤风败俗的事儿,赶紧靠岸呢!
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开了,而且越来越邪乎。若不是那位持刀立在门前的锦衣卫阻拦,胆大的守卫便想破门而入一看究竟。
第四日天刚亮,终于传来了船舶靠岸的命令,而那一直盘旋在商船上空的乌鸦也不知怎的消失无踪影。
船舶靠岸后,那几位大人终于出了房门。除了那被庆王背负的忠武王看不清面容,其他两老一少都是面色苍白颤颤巍巍的下船。
一众单膝跪地的守卫,各个眼神奇怪,偷偷目送着几位大人下船。心中想着,这位小皇子要逃婚,原来是有龙阳之好啊!你看那两老一少的样子,不但口味挺重而且精力还挺旺盛,真不愧是天子之后。
光凭这份坚挺!就比某些京都里的达官贵人们强了百倍不止。
老韩头人老成精,一出屋看那守门的锦衣卫眼神就猜到个一两分,下船这一瞧那帮守卫的眼神,就知道他们心里想着的是啥。
老脸臊的跟猴屁股似得,恨不得将这帮小子的眼睛都给挖下来。他瞪了眼旁边低头走道的李精忠,恨不得一脚踹死他。
上了回营马车,老韩头终于按捺不住心情,指着李精忠破口大骂:“你说那针也没扎在你身上,你大惊小怪扯这个公鸭嗓子啊啊个什么劲!你看看船上那群小犊子的眼神,这要是谁编个段子传出去,让我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李精忠你别跟我装没听见,要不是老子现在没力气,我非拿指头戳死你!”
李熙寒抱着熟睡的少年一阵偷笑,李精忠则靠这马车犄角那闭着眼睛装睡,老韩头瞪着牛眼睛喘着粗气,骂个不停。可骂着骂着声音却越来越小,竟脑袋一栽,呼噜响起,流着哈喇子睡着了。
马车行了不多时便到了镇北大营。不知怎的,有百名银甲白马背弓的士卒,将马车拦在了门前。
只见领头的那位持枪披甲的少年郎翻身下马,单膝跪地,抱拳大声喝道:“末将杨景参见庆王。”
“六郎,为何拦本王的车?”
杨景并未起身,抱拳说道:“回庆王爷,末将是奉门主之命,特来接忠武王爷回营。”
庆王李熙寒听到门主二字时摇头苦笑一声,看着怀中看似熟睡的少年,自言道:“没想到你我分别之时来的这般快,小皇叔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连睁眼看我都不愿。”
那闭眼似是熟睡的少年,睫毛颤动,但终究还是没有睁眼。只是两行泪水滑落,算是一种回答,也算是一种送别。
李熙寒用手将那泪水擦干,说道:“小皇叔,答应熙寒一定要好好活着,你若死了,熙寒在这世上就真真没亲人了。”
李熙寒眼圈泛红,最后望了一眼闭目流泪的小皇叔,微笑下了马车。
他将那一直单膝跪地的杨景扶起,打断了这位忠烈之后解释的话,说道:“六郎不用解释,我知道那里进不得。这一路上马车尽量慢一点,回去复命时,替我跟里面的几位老人家问声好。”
杨景恭敬的称是,替下了车夫,临行时看着李熙寒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但终究没有问出口,在一众白衣白马士卒护卫下,策马驱车而回。
马车上本来闭眼熟睡的李树生睁眼起身,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低语询问道:“六郎,熙寒那小子是不是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驱车的杨景嗯了一声以示作答。
李树生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追问道:“六郎,跟你比怎么样?”
杨景似乎不太厌烦,回答道:“反正比你强!”
李树生听此,撇了撇嘴,回道:“六郎,三年不见你怎么还是这个鸟样,三句话没到就跟吃了火药似的。还有什么叫比我强,想当初小爷的美貌可是在京都都能上榜的人物。”
杨景听此冷笑一声,讽刺道:“我记得你最后一次在京都的时候是八岁!”
李树生翻了翻白眼,抠抠鼻子,回答道:“八岁怎么了,那说明八岁时候的我,美貌已经冠绝天下。虽然这几年风吹日晒长的有些过头了,但也算是咱镇北营中一只草,武烈门里根正苗红的一枝花。”
杨景呵呵笑了两声,实在不愿意搭理这个脸皮厚的跟城墙,吹起牛来甲天下,争论起来不认账的滚刀肉。
李树生喊六郎半天也不搭理他,只好自己在车里叽里呱啦说个没完。杨景皱着好看的眉头,恨不得停下马车把这位王爷的嘴给撕烂。
李树生或许是说累了,也或许是没人理睬自知无趣,坐在马车里直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突然一安静到让杨景不适应起来,询问道:“怎么突然不说了,想什么呢?”
李树生两只手搅动着,说道:“六郎,熙寒给我写了十年的信,我却一封未回,营中等了我三年,我却未曾说过一句话。你说,我是不是有些太无情了。”
杨景沉默了片刻,回答道:“确实无情,或许他们还没走,要不我们掉头回去看上一眼?”
李树生掀开马车帘,坐到六郎身边,望着前路越来越近的那处写着武烈的营门,说道:“不回去了,想想还是不见最好,省着我哪一天一命呜呼,他哭的太惨给我这个小皇叔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