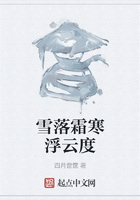白土地上正站着一个四面张望的女人。她穿着奇异的衣服,是用白色塑料做成的。白色塑料衣服从头到脚裹实着她,只留出一双乌黑闪亮的眼睛。之所以判定她是个女人,是因为她的胸前有非常高耸的乳房,她伸出的手是一双属于美丽女人的手,她踏在白土地上的脚是一对属于美丽女人才有的脚。她的身后,背着一只隆起臌胀的大包,那包还毫不谦虚地显示出了它的内部藏有不少东西。她站立的姿态令我心动,在白土地上,我从没有看见过这种亭亭玉立的样子。
她是谁?她从什么地方来?
她终于发现了修建新祠堂的白土地人,于是她毫不迟疑地朝他们走去。但她也许吃惊了一下,她在靠近残疾传染的白土地人一定距离时停止了。然后,我看见她向他们招手。
有一个人走过去了。本来有许多人在争抢着走过去,但似乎是谁出来制止了大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在谈论着什么。他们谈论着什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发急。我诅咒那个白土地人,该说什么话也要先由统领来说,你算老几!我还想,我是不是该走下木楼,走到她身旁,仔细看她这个哪里来的怪女人。 也终于,白土地人把她领到老祠堂方向来了。我心里却更加发急。我看到那女人没有半点的害怕恐惧感,她大义凛然,一副潇洒自如的神情,似乎人听人怕的白土地人对她没有任何危险。她是不是真正的人?如果她不害怕白土地上瘟疫一样的传染,她是人吗?如果她不害怕白土地人的病,那白土地人是不是就该怕她了?她到底是谁?她来干什么?她有更可怕的病菌吗?
我呆站在木楼的阳台上,心里忐忑不安,想法乱七八糟。当我听到木楼梯上的声音消失,转过身子,外来户女人就站在了我的面前。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把我所想的问题还没有理顺,我该问她什么也还没有想好,她却伸手过来,嘴里说:“嗨,你好,太子统领,我叫美的传播者。”
我现在距离她最近,我看见她的塑料衣服又新又好看,我发觉她的眼睛又锐利又漂亮,我认清她是四肢健全健康没病的人。
我不知道她伸手要干什么,因此我后退了一步。
她不介意。她笑着。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这两句话在我心里打着转儿,我却口吃木讷,问不出来。恐怕太子统领最为尴尬的一次就是这个场面了。
美的传播者不容我答应,就独自走进了祠堂。我听到她对祠堂里面悬挂着的画像发着惊讶的称赞议论。
“她从哪里来?”我问最后跟上来的白土地人。
白土地人指指天上,一副懵懂的迷惑的模样。
“她从天上降下来的?”我有些难以相信。
白土地人点点头,下了楼。
我仰首望着天空,一团白云缓慢地流动,红太阳在云朵遮不住的地方,露出神秘兮兮的笑意。红太阳似乎也要捉弄我,并不给我确切答案。一团白云过去了,一团白云又来,我不知该问哪团白云才能得到确切消息。在大西北我的落后的白土地上,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白土地,就只有建立在愚昧这个基础上的希望了。
是的。这个怪异的天上降下来的女人这时就在做着怪异的事情。她卸下身上的大背包,拉开链子,从中取出一个透明圆筒(后来她说那是玻璃器皿,谁知道呢!),在我的祠堂四周细致地喷洒着一股水(又不像单纯的水,有异味)。
“你要干什么?”我大声喝斥。
美的传播者一点也不生气,她抬起头,用眼睛嘲笑我后,说:“太子统领,你这祠堂充满病菌,我用药物帮你杀死它们,如果你同意,今晚我就住在这里啦。” 药?我没有听过。可是,天下有这样的女人吗?不过,想过之后我也才真的明白,原来她真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我开始害怕,这样的女人跟我睡在一起会怎样呢?她是不是也有神秘的东西,是不是也要让我像对待白土地上的那些女孩那样,帮助她兴奋快乐?但无论我怎样想,我都觉得我无法与美的传播者进行交流。或者,她对我根本不屑一顾,没把我放在眼里。这在白土地上,是从来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想,来者不善。
晚饭被送上楼来,我独自享用。美的传播者又拉开她的大包,从中取出也是塑料袋装的酥软的食物和塑料瓶装的不知是水是药的液体,她又取下头上的塑料帽,露出一张绝对年轻美丽的脸庞,我怅呆于她的那张脸时,她咬一口食物,喝一口液体,看也不看我一眼。
油灯点亮后,我的女人黄叶儿拖着病身摸索着艰难地爬上楼来,用她看不见的眼睛看了一次天上降下来的女人美的传播者。然后叹了口气爬回了她的住处。 我躺在我的木板床上,美的传播者又从包里拽出一张花纹鲜艳的塑料纸铺在木质地上,躺下来看一本纸书。
我望着木楼顶,心里烦乱极了,矛盾极了,复杂极了。我不知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我隐约觉得,她的到来绝对对我形成了不利。那么,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天上降下来的小妖精,谁能制服她?我懒得理她!谁愿意理她?
一会儿有了一些轻微的声响,到听到沉重的木楼梯响动时,美的传播者爬起来仿佛是干了些什么,又静下来继续看她的纸书。
我知道谁来了。我的女人黄叶儿总是会在我为难的时候为我排忧解难。她能解决一切我所遇到的而又解决不了的难题。
大模子推开门,脚步沉重地走了进来。我侧过身,望着他慢慢靠近美的传播者。我心里仍然很复杂,我有些不愿意让美的传播者这么快就死亡。尽管我对这个天上降下来的女人一无所知,可我确实不愿看到这么美的女人在大模子的拳脚下一命归天。女人,如果她什么都干不了,总还可以看。何况美的女人,更有看头。而假如美的传播者能答应做我的女人,代替黄叶儿,那就……
大模子一拳砸下去的时候,我心里发了一声叫。但很快,大模子笨重的身子就跟着他的拳头一齐倒下去了,把木楼震得轰隆一声,摇晃不定。我明显看见美的传播者其实只是用脚轻轻一蹬一勾,大模子就倒了。之后,我看见她飞快地用一只带有明晃晃的细针头的玻璃管子在大模子脖子上按了一下。我知道那是药。我想我的簇拥者大模子已经完了,也许永远将不会再爬起来。连病菌都不怕的女人和她的药,对付害怕病菌的大模子恐怕是再简单不过了。
我恐惧地躺在木板床上,没敢再想那可怕的女人——美丽的美的传播者。我为我的簇拥者大模子心里默默垂泪。我的大模子,为我做了多少事啊,最终也是丧生在了为我做事上。
我一夜没能合眼。美的传播者一夜很安静地睡觉。直到第二天清晨,我才不知怎么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红太阳爬上了三竿。我一睁开眼,就想起了昨晚的事,我低头寻找,美的传播者和大模子都不见了。
狗子和斜头走进来,狗子爬在我的耳旁轻声说:“太子统领,你知道吗,黄叶儿听到昨晚的事,张口就喷出了一股红血。”
“大模子呢?他的后事……”
“什么后事?他在楼下,正忙着搬木头呢!新楼即将竣工了,你该高兴一点。” “那个天上降下来的女人……”
“她么,一早就到各个家户去了,正用针管给大家打针,说是能够控制病菌蔓延的药物。你不知道吗?她说是你吩咐的。药物,什么是药物?”
“别听她的!告诉大家,那是让人快点死亡的东西!”我说。
狗子领命而去。
我心里长长出了口气,我让斜头也出去,我说我想静一静。但他们跨出门,我又叫住他,强调说:“那是叫人死亡的药!”斜头点了点头。
我彻底明白了。天上降下来的这个女人才是白土地上祖先几代所期盼的那个希望。尽管我目前仍然对她所说的一切有所怀疑,但我相信,她肯定在事实上有能证明的东西。那么,我呢?是不是我将从此失去一切,包括我的统领头衔、我的权力、我的威风、我本身带给大家的那个希望?那么,我从此将怎样再生活下去,怎样再成为大家心目中崇高无上的领导者?有了美的传播者,谁还会再听我的?
我躺在木板床上,楼顶的细粉末不断地降落下来,在空中各自打着旋转,落到我的被子上,逐渐聚集成了厚厚的一层。红太阳从外面探进眼光,打量着我纷乱哀伤的思想。
如果美的传播者真的让白土地人转移了心目中的那个希望,如果她代替了我成为白土地上新的主宰者,如果她让白土地人不再残疾成为像我和她一样的健康人,如果白土地人心中不再需要希望,如果白土地上长出茂盛的庄稼、葳蕤的草木,如果……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如果一切都变了样,转化过来,我还能拥有目前所具有的幸福吗?还有白土地人看我时眼神那么敬仰吗(我想不会有,例如和我一样健康无病的美的传播者看我根本就是视若未睹)?如果真是那样,我也将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那时,残缺的恐怕是我,而不是所有白土地人了。既然如此,美的传播者对我就是一大危害了,我的一生损失,都将从她开始。
是的。我得想个巧妙办法,得让美的传播者从我的根据地上消逝,然后保证我的一切原原本本不受损失仍然回归于我。
我起身穿好衣服下了床,走到木楼外。我看见即将竣工的新木楼高高耸立,高大雄伟,辉煌无比;白土地人忙忙碌碌,建设正忙。我还仿佛看见美的传播者正出出进进,从东家到西家,用她的破烂玻璃管子在为大家的手臂上输送药水。我抬头望天,万里无云,睛空中的红太阳照耀得正野,而脚下的白土地生发的干燥一阵更比一阵浓烈。
没错。这时的美的传播者确实挨家挨户在为大家治疗(治疗一词,来自美的传播者为大家所作的解释)。她用她妖艳的美吸引蒙骗了大家脆弱无助的目光,她又用她灵巧的小嘴哄信了大家软沓沓的耳朵。她讲解得既好听又清楚,使可怜的没经见过大世面的白土地人竟信以为真,以为真的天上降下来了救星,以为希望真的变成了现实。其实,天上不过就是降下来了个女人,她也吃食物,她也讲人话,她的形状完全是人间的女人,用特别根本说明不了她什么。
几天里,在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对付美的传播者的方法时,美的传播者跑到了我的女人黄叶儿的窑洞里,苦口婆心要为黄叶儿治疗。但态度坚决的黄叶儿执意拒绝了她。这个消息传来,我为我的女人黄叶儿感到骄傲和自豪。
几天里,美的传播者早出晚归,到每一户白土地人的家中前去进行她的骗人把戏。我渐渐发现她的可笑行为既伤害不了大家又坏不了我的事情,便也由她行动,置之不理。她很晚才回来,很疲劳的样子躺倒即睡,清早在我不知不觉中悄然而去。我也学会了,对她视若无睹。
而就在我尚无好的法子时,一直暗中观察着事态发展的我的女人黄叶儿却有了好计谋。
那一夜,我照例躺在我的木板床上苦思瞑想,美的传播者亦如往常一样爬在木质地板上看她总也看不完的纸书。一会儿,楼上来了人。我看到美的传播者又一次摸摸索索做好了应敌准备。推开门进来的是我的簇拥者狗子。我知道狗子来干什么。果然,狗子重复了前几天夜里大模子的行动和遭遇。但事情的不同之处是,就在美的传播者将她所准备的药物射进狗子身体后而再无准备好的药物时,大模子带着蛮嘴、斜头和赵干一齐闯了进来。
美的传播者在那一瞬间脸色骤变,清白的油灯下,我看见她的脸比油灯还清白。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是来救你们的……”美的传播者急了,“我是医生,来治疗你们的病,这是我的研究课题……明白了吗?不明白?听我慢慢解释给你们好不好?听着,仔细听着,听不懂了问我,行不行?”她一边说着还用手一边比画着。
我的簇拥者们摇摇头。没有人愿意听。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也是人,是从外面来的人,不是坏人,听懂了吗?好人!给你们来治疗病的好人。你们有病,有病是不是?我是没病的人,就这样,你们也会像我一样……”
她的形象几乎像个幼稚的孩子,但她自以为她是在对着幼稚的孩子说话。我的簇拥者们训练有素,临阵不乱,从来也不会顾及考虑对方的意见。他们只听从安排,他们的思维不在我这里,就在我的女人黄叶儿那里。幼稚的美的传播者! 后来的事情我记得最真的一幕是:美的传播者森白的嘴角淌下一股鲜红的血液,青白的油灯在她的血液映衬下黯然无光,她惊讶而不明事理的眼睛瞪得又黑又大……
我曾经指使我的簇拥者,在美的传播者的身体尚还留有余热的成份时,你们谁愿意就给她最后一点快乐吧,反正我是不想再看见她。但我的簇拥者们都摇摇头,表示了委婉的回绝。我扫兴的下了命令:趁着黑夜,把她拉出去,埋掉!还有,不许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十、生命
祖先的新祠堂和我的新住所即将竣工的时候,白土地人突然实行了大罢工。 消息传来,我正在老祠堂的木板床上感受最后的几个梦境。
我看到罢工的白土地人时吃了一惊,因为不只是修建新祠堂的男人对我表示出极力的反抗,连所有的妇女和孩子们也都参加了反抗罢工队伍。这是白土地人对“希望”的第一次污辱,这是白土地历史上对统领的第一次挑战。我还能重新夺回我的威风来吗?我恨——
都是美的传播者惹得祸!
不!我必须夺回来!这个可恶的和我一样身体健康没病的坏女人,竟使我的生活由安静变得一塌糊涂,竟使安定祥和的白土地人躁动不安。她的降临,让一切打乱,她的到来,让一切波澜起伏。有人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就是同一族类,不也充满了血雨腥风,斗争不断吗?你看看,与我一样完美的人,她却把我的领地搞成了什么样子?她一出现就心怀鬼胎,嫉妒过剩,打算要我死亡嘛!这样的族类,不除她还不知会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呢。我感谢我的女人黄叶儿,临危不乱,当机立断,替我除掉了一心头大患。接下来呢,这点小事我就自己来摆平算啦。是的,龙年太子自任白土地统领以来,还没发过火呢。就发一次,烧它一场。谁不想活了?是哪一个,现在就请你来跳进火堆,看你身体能刚强到何种程度,看你忍耐性能持续多长时间,来吧来吧,待我点火,烧你! 我对着全白土地人,心里懊怒着那个美的传播者。我看到全白土地人雀雀跃动,似乎要反了的样子。我让谁去向下传达我的命令呢?我回转身子,却发现原来我身边空无一人。我的簇拥者呢?都到哪儿去了?我仔细搜寻,望见人群中突出的大模子低着头,好像不敢正视我的眼睛。我还望见狗子缩在人群某个边角,贼兮兮的,又像是害怕的样子。其他的呢?蛮嘴,赵干,斜头,一个个全都藏在人群中,都表现着与我要划清界线的意思。为什么?狗杂种!我对你们怎么了?我亏待你们了?你们这些狗王八,跟着我吃香喝辣,屁事不干,吆吆喝喝,耍尽威风,现在这么快就翻了脸啦?狐假虎威的那阵儿你们怎么不靠拢他们?你们这都是怎么啦?不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个女人吗,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值得你们要跟太子统领保持一定距离?王八蛋!趁人之危,不得好死!你们看着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