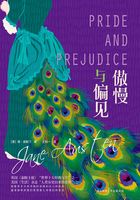就比如一次,读了十几年之乎者也的荃兴去他那儿预测将来的前途是否无量。胡老大就穿上长衫,拿起折扇,微闭双眼,盘膝坐在炕头上,慢腾腾地接过荃兴恭恭敬敬递上来的生辰八字。胡老大怎样看,荃兴不知道,因为这时荃兴勾着头,他深知那神圣一刻不是他凡人俗胎的荃兴可以看的,否则,他那双眼不瞎了才怪!所以,明智的荃兴只能虔诚耐心地等待着胡老大口吐真言。
胡老大坦坦然然地像是根本没把荃兴的命运当一回事儿,让人觉得他只是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打了一个盹。
荃兴就听到胡老大先“啊”地长叹了一声,又“哈”地狂笑起来,荃兴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胡先生,我……”荃兴问时仍勾着头,大脑里一片纷乱,想像中的神秘对胡老大来讲,那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或者就如一个随便的什么动作而已。
“你抬起头来!”
荃兴顺从地把头仰起来,他看到胡老大沟壑纵横的老脸上裹着的是一片高深莫测的严肃表情。就像后来荃兴跟我说,他举着棍子骂猪,“再不滚我就打你了!”猪依然冷冷地看他,不说话也不行动,视他不见一样。胡老大说:“咋说呢?你嘛,总的判断,命里无官运也,要么……天机不可泄露!当然,看在你是干孙子的份上,救你一下:认命!前世你是福身,子孙兴旺,命钱斤两不小,日进纹银十两有余。这一世嘛,就只怪你娘把你生的不是时候,你命里克木!哦,你说,你娘生你的时候是不是不在炕上?”
“在……”
“在木上!是不是啊?你尽管想凌云直上,却根子不稳实……”胡老大探头向荃兴靠了过来,嘴里呼出的恶臭之气险些把惊愕的荃兴熏得晕过去。荃兴向后仰了一下腰,即刻又把脸凑了过去。
“是……在柴草堆里。”荃兴低声说。又猛然抬头吃惊地盯着胡老大那张半是迷醉的脸。
“哈哈哈哈……”胡老大仰头大笑,又满口因无牙而露风地唱说:“干孙子!鬼孙子!胡×乱×的个狗孙子!你的事,我的事,没人不信那是大事!……尤其你娘!你娘哟……哈哈哈,打她生来,我就掌握了她的小命……”
“我娘早死了。”荃兴唉声哀调,眼圈儿红起来。胡老大猛然刹住口,一旁斜倒下去。
“神了!”荃兴后来又跟我说,“顺仔,要不你也去算一下。”
我摇摇头,说:“我不信。”
“甭犟了。”荃兴说,“咱们古店庄许多的事胡老大都算出来了,而且事出之前说的话全都应了验,分毫不差。本来嘛,我也想干点有文化的事,可后来……后来胡老大说你荃兴娃不行,就别违背注定的命运胡弄啦,小心完蛋了你!我才死了这心。要不,我早写文章去了,咱古店庄有东西可写哩!你知道吗?古店女老板她男人咋死的?这……胡老大早预说过的,真的就那样应验啦!”
我曾听说过荃兴很能写的一手好文章。现在,古店庄那些土里挖泥的娃儿们就唱着,他写的《古店女人记》中有这么一段:
十八女儿进刘门,羞羞答答
二十少妇更有姿,貌冠天下
廿二夫妻营古店,来客下马
廿四赤身迷商贾,金银斗大
廿六春风正得意,薄情如花
廿八忽遭漏屋雨,卷衣归家
……
但可惜的是,当我见到这篇已被流传到了下一代口中的佳作时,原稿已散失数页,且黄斑生就,成了遗憾。我建议他重写,荃兴笑一笑说:“胡老大说了,我得认命。”
我便去找胡老大,我想知道古店女老板的男人死的缘由。
二
回到家时,爹不在,问娘。娘说:“去熊家了。你不知道熊家出事了吗?”娘声音沉沉的。我说:“不知道。”娘说:“唉,真是遭了孽了,咱古店庄究竟咋了?一事接一事啊!”我淡淡地说:“有什么异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嘛。”娘说:“以前呀也有事,可有了事人的心里也没有啥,出事了就出事了,过得去,可现在呢,这要是有个啥事一出来,人心里就慌慌的。”我说:“那是心理在作怪,你倒说,熊家出啥事了?”娘又唉叹一声,眼睛里滚出两颗泪才说:“兰叶死了。”
兰叶是熊家熊田老汉的二儿子熊过的女人,才二十多岁,矮个儿,略胖,脸上特点是嘴唇厚,说话时速度慢得像从鼻孔里哼出来的,看起来一副邋遢样却实际不邋遢,干起农活来熟练利索地是她男人熊过的师傅哩!
“咋了?”
“说是把毒药喝了。”
“为啥?”
“都说是因为吃了两个梨的事。”
“吃两个梨又咋?家里多得是那东西!”
“他公婆不给吃呗,她却硬吃了,她公婆就和她吵,吵了一早上。出去放牲口时在包里塞着她男人的鞋底,预备要纳的,包就鼓着。她公公就追了来,夺过去拉开包一看里边没梨,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气极了,骂她公公一句:‘我到你们熊家来过的猪的日子!’你说说看她厉害不?咋来那么大的个性子?她公公就告诉了她男人。她男人就赶到了山里,打了一天的架,听说是兰叶被打得快要死了……回去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唉……也可怜,肚子里还怀着个娃儿呢!”
“她男人也不是好东西!”
“兰叶呢,也真是性子太硬了!女人,唉……要像个女人的样子……也不知这下咋埋人哩?她肚子里有个几个月的娃儿……你年轻不知道,一座坟里不埋两个人儿!她娘家人来了恐怕也不依哩……”
“不依又能咋?”
“也不知会咋?可那坟里是万万不可埋两个人的……你年轻,经的事太少,没见过一座坟里埋了两个人会出怪事哩……”
“啥怪事?”
“大前年,柳树庄就有过那么一件事,怀着娃儿的个女人死了,被埋在了同一个坟里。后来就作怪,连邻家都不得安宁。一次,那坟前经过了她的邻居一个也快要生孩子的姓蒋的女人,不想,怪事就发生了,姓蒋的女人生孩子的那天,总有一盏蓝幽幽地灯跟在她身旁,忽左忽右,前面一闪后面一闪,她害怕极了,总得要人一直陪着才敢走动。生孩子那夜,不像旁的女人生孩子那样痛苦——旁的女人生孩子都要疼得哭叫,姓蒋的女人却笑,笑着说,灯灯灯……又说,你们快看,那娃儿在半空中笑哩……尽胡乱说一些吓人的话,唬得接生婆子都跑了。后来,她男人请了阴阳先生来看,说是魂灵被坟里的那个女人叫走了,必须再从坟里的女人手里夺回来。看病时,一切都顺当着,可把姓蒋的女人魂灵夺回来往她身上送的时候,阴阳先生手里本来拿着两个鸡蛋,就是她的那个魂,托收在鸡蛋上嘛,眼看要进门了,却不想他们家那只猫突然跳上阴阳先生的肩头,你说怪不?还没等阴阳先生明白时,那猫伸出爪子一下就把一个鸡蛋打掉了,啪的摔在地上,碎了。阴阳先生直惊得变了脸色,连叫:啊呀呀,不行了……不行了……这时候,是万万不敢说这话的,要说好着哩好着哩……那阴阳先生昏了头却胡叫出来……”
“那以后怎样了!”
“死了。”
“我问姓蒋的那个女人。”
“不就是她死了么,还能有谁?”
“那熊家……”
“不知他们会咋办?这样死了的人性子更烈,让人总担心……”
我一出门就碰见了给刘家放羊的老光棍虎山。这本来是个极爱说笑的人,每次见了我总要把说话的口气变成外地人,就像南方骡子学北方驴叫唤哩——南腔北调的。不过,他总爱那调子,张口就是“侬你那拉才说哩……”
这次怪了,不知老光棍生着哪路子闷气,看见我头都没抬一下。
“有啥事了?”我问。
“你说这到底是咋了?他妈的,这古店庄……”
“我问你咋了?”我不耐烦地说。我怕见别人那种悲哀的音调和唉叹的样子。 “那个老妖婆子给气的!真不是好东西,东雨西下哩!他妈的,我没亏过他们一家子!”
我便知道他指的是古店女老板了,“你怎么敢骂她?小心她不认你这个边塞男人了。”我跟他开玩笑说。
“球!谁看上她?老青核桃皮似的,心底里更坏着哩,真是头顶里害疮脚底里淌脓哩。就说哩,大儿子丑银和媳妇闹不和,她不但不劝说好那个贼儿子,还倒数落儿媳妇的不是,挑事非让儿子把媳妇美美实实捶了一顿,你不见哪,身上脸上竟是血。可她不去给媳妇儿说一句安慰的话,还说,当年啊,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咱女人,命该如此。这是话吗?球!她当年才不是那样的,她呀,三天一顿两天一顿地收拾男人哩,有一次差点把男人的命根子给揪断了!”老光棍虎山气乎乎的,仿佛挨揍的是他。
“熊家的二媳妇兰叶喝了毒药死了,听说也挨了打。”我转变了个话题。
“听说了。还有人说,不是喝了毒药,是打死的。”老光棍虎山压低声音说。 我蓦然一阵惊怵,心里便发毛。不知该说什么话了。
老光棍虎山发一声唉叹说:“人哪,总有生死的……唉,老熊田就不是个好熊!再也说,咋死都一样,这在咱古店庄已不是新奇事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我惊异地问。
老光棍虎山却又不说话了,沉默了老大一会,扔了手里捏弄的柴棍儿,卷了个和大拇指一样粗的旱烟棒子疯抽了几口说:“你知道那个老妖婆子多妖吗?她一直爱给旁人耍小聪明,可总耍不过去,说话前面出谜儿后面又道破了,还自以为比别人能,可你一看她那个样,就知道她是个啥老不正经了。就说睡觉吧,她大儿子丑银跟媳妇儿睡的那只窑和她的紧挨,靠边呢还有一只,离丑银睡的那只远一些。我就说你还是睡边上那只吧,儿子儿媳妇的,孙子孙女都那么大了,不方便,出门进门啥响动都听得见,你睡那么近干啥?你老了,又是一个人,睡哪儿还不磨到死了。可那老妖婆却还对我贼眉贼眼的,像是我对她有啥野心了。他妈的!我这半辈子都独身过来了,年轻时都没对她有啥意图,老了还能瞅上她?真是他妈的假正经!要正经年轻时咋不正经哩?多少男人那东西她没见过?老了倒还……唉,人真是越变越不像个人了!她就从这儿给我记下了。昨早,就说,暖哟哟,你怕是再不能给我们家放这羊了!我问,咋的?就说,古店庄的人都说闲话哩。啥闲话?我又问,她就那么妖里妖气的一笑,说,还能有啥闲话?你没老婆,我早死了男人,人家就都胡说哩!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古店庄的这些人,啥话都能从嘴里丢出来,没牙的那嘴呀,横着竖着都能说哩。我当时就气愤了,也听明白了!就是,聋子才听不明白呢!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要赶我走了?你本是大名鼎鼎的古店女老板,我哪敢对你攀奢望呢?怕我坏了你纯洁的名份吗?我倒还没那样想呢!可她却话都说明了还怕落个把儿,硬胡解释说,哪儿是我赶你走呢?果真有闲言哩。胡老大都说过。我哼了一声。后来我就去问胡老大,胡老大说,啥球事?我管那么多干啥?我说那么多话干啥?谁又不掏钱给我!不过呢,你老光棍就耐得住?我才不信哩,猫儿不吃荤,病猫!我当时就想给胡老大一巴掌,他妈的!我老光棍已经是几十年的老光棍了,我再找谁也不会去找她个老妖婆子……就只是,她不要我放羊了,我去给谁放呢?我总要吃饭哩……”
老光棍虎山说着说着有了老泪,他是伤心他丢了饭碗了。
我就想提另一个话题,把他的思维转移到另一件事上,这样,他就不会过于悲伤了,说真的,我就怕人哭。尤其见老光棍虎山要哭,我就要跑了。
我便说:“前几天甲银在水涝池子旁骂骂咧咧的,不知道为啥?你在刘家总呆着,知道点吧?能不能把秘密掏给我点?”
“哼!刘家是前辈子做绝了坏事,后辈子在还账哩,甲银么,他媳妇走了!” “走了?咋走的?”
“甲银想学他哥丑银那样把媳妇儿揍扁捏在手掌里不要翻身,可媳妇不是那号软料,挣扎着要从她男人手里跳起来。如今的女人,都成了长膀膀的鸟精了,一般的男人,不英雄着就成狗熊了……”
“那古店女老板呢?她当年……”
老光棍虎山突然住了口,脸皮绷紧了,有惧怕的神色。我就四下里看,发现远远的,古店女老板的三儿子卯银走来了。
舅舅又来了,问我:“你到底要不要人家芙子?”
“我……”
“彩礼三千六百八十块,娶进门也得花个五六千儿,总要把咱古店庄的人都招呼一下,总不能偷偷地娶进门,那样,岂不让古店庄的人笑话了咱。就这,已是古店庄破了例的低价了。”
我偷眼看见爹娘眉头皱得紧紧的,我知道他们愁的原因是没有钱。我心里暗喜。
我说:“早哩早哩,催那么急干啥吗。”
舅说:“不行!就现在,人家芙子爹养活不起芙子了。你不看,芙子她爹老了,干不动活了吗?”舅又说,“娃,娶进门吧,那女娃儿是个实诚的,咱就咬紧牙争破头硬撑这一回吧。”
我说:“钱呢?你们有钱吗?”
娘说:“只要你们都同意了,把咱们的老牛卖了算了。”
爹哀声说:“这卖了牛,也还差得远呢……”
舅说:“不管咋样,要快!这事不能耽搁,刘家也差了媒人去了。夜长睡梦多嘛。”
“啊?”爹和娘同时惊得张大了嘴巴,又都一脸悚然。“那……咱跟人家不是对手……”
“所以要快!”舅不像了平日里显得老谋深算。“我看芙子爹虽老实,但也说话算话哩!况且芙子对顺仔也像是满意着……”舅说,脸上竟也有了痴呆的症状和慌乱的表情。
他们都是怕刘家那几只狼的!我清楚着。
我记起来了。狗日的卯银今早上来跟我说过几句话。早上,日头懒洋洋地无精打采的从东山里爬上来,四周的蒿草疯冒的茎杆儿要钻天屁股了。我依然璺璺走进我家的庄稼地里。密密的麦子绿油油发亮,大半已经抽穗了,麦芒银针似的一根一根朝天直立,密匝匝的针毡是个一望无际的绿色画面,绿潮漫漫泛泛,有些活泼的虫子在麦丛里鸣叫,仿佛在告诉别人它们活得很好。有一只山鸡扑地从草堆里钻腾起来,飘飘摇摇发着惊恐一样的翅膀呼扇声遁入山隅处。但愿它别碰上猎人冯华。我暗暗想。远处有着荒凉和寂寥的渺渺群山让我恐怖,因为那些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山就像芙子爹的秃下巴。
“顺仔,听说你相好媳妇了?”我的背后有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来搭讪。
我听得出来,是卯银。这个狼窝里的小狼崽,倒瘦狗鼻子尖。“有事吗?”我问。
“啥时娶过门呀?可要保住她的小羊羔,一大群光棍等着受活哩……你们何家怕要出丑了……嘿嘿嘿……”
“这天下没有共娶共妻的理儿!”我说,用憎恶的口气。
“嗬!”卯银嘲笑了一句,“这是官话吧?听不大懂。不过——可要小心哩,别被人半路截了先!”说完他走了。我看他那背影都是和丑银和甲银一样的狼形。 舅最后对爹和娘说:“要不,我明儿个再跑趟去,等麦子一收,就娶。你们要赶紧准备钱哩!”
爹和娘的脸上的表情复杂地清晰,乐的和忧的都各占着半,对舅说:“娃这大事,全要靠你……”
舅没再说话,只用眼睛斜扫了一下我。走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仿佛要说什么,可又什么也没有说。
我在看书的时候,那个猴样的却长得又俊俏的刘若银来了,大大咧咧地进了我们家,向正惊疑地望着她的我娘露一个笑脸,说“您老人家忙您的,我找顺仔。” 娘也就回个笑脸说:“他在窑里,做好梦着哩。”
若银就又旁若无人地进来了,出于礼貌我站起来让她坐。
若银却又走近了我,伸出手来就按住我的肩,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你坐你坐你坐——我嘛,自己人,一泉子里吃水,又不是客。”
我还从来没挨过女人这么近,除了那次芙子给我擦眼泪。不过那次我着实心里不畅快,也就没在意。可这次,我清醒地闻到了若银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从未闻过的味儿。
若银用尽了力按我,我却站着不动。
若银娇嗔着:“你呀你呀,使那么大力,要吃了我?”又向我靠近来,仰着脸,差点把脸贴在我的嘴上。“你吃吧!”她说。嘴里就喷出一股幽兰般的香气,让挑逗弥漫着我们的空间。而且,她还正用胸前突起的地方磨蹭着我。
我几乎晕倒了,我感到心跳加剧,体温也骤然升高,浑身焚烧地难以克制,两只手颤抖着猛地抓住了她的那两个眨眼睛调戏我的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