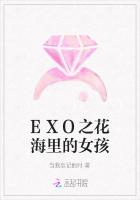回家的路走了好久,景寒月趴在齐杰的背上渐渐停止了抽泣,她乖乖地勾着齐杰的脖子,半个脸贴在他的肩头,聆听着他沉重的喘息声,像撞钟一下下敲进心里。
两人谁也不说话,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
大雨过后,坑洼的路面积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洼,一路走来齐杰湿了鞋,又浸泡了裤脚。街边偶尔跑过几只小狗,齐杰突然轻松地吹起了口哨,好老的曲子,《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景寒月再熟悉不过了,爸爸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只是她从来都不知道原来齐杰也会唱。她听着听着笑出了声,“没想到这么老的歌你都会唱。”
“你没想到的事多着呢。”齐杰得意地说。
是的,景寒月不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齐杰对她来说一直就像是个迷,一个潜在自己身边而永远无法解释的迷。他们是一家人,他是她的哥哥,是没有任何血缘的哥哥,她不曾见过他的样子,指尖却抹不去他的轮廓。
十年前的仲秋夜,一场煤气爆炸夺走了景寒月生母的命,她的眼睛也因那场意外瞎了。意外过后的好长时间,她绝望地把自己封闭在屋里,一待就是个把月。不说话,不思考,分不清黑夜白昼,整个世界只有黑暗陪伴,那些身边无法想象的形体和无法确定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刺激着她的神经。
为什么我不是耳聋而是眼瞎?那个时候景寒月每天抱着爸爸哭得昏天黑地,一遍遍问。可是,年幼的她殊不知耳聋和眼瞎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终身残疾,是此生都将终身背负的痛苦,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是的,她再也不是常人。
伤心欲绝的爸爸不忍年幼的景寒月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又已失去母爱,等于失去了人生大半个幸福。为了改变暂时的窘迫,两年后爸爸带着景寒月离开B城,经人介绍娶了一个叫郁秀的女人再婚。
这个新家里不仅有新妈妈,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只是这里并没有带给她预期的欢乐和幸福。为了不让爸爸担心,一切的不愉快她都默默忍下承受,尽管妹妹齐果对她始终如仇人般充满敌意,但至少身边还有一个替他说话的哥哥。
盲人的世界有时就是这样,卑微的连‘不’都不能轻易说,忍耐和承受是生活唯一的出口。
中学辍学后齐杰便早早离开了这个家,如今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淡漠的。
从有记忆起自己看到最多的就是亲生父母的打骂吵闹,一天都没停止过,而他就是他们最好的出气筒和沙包袋。
四岁那年夏天,从幼儿园回到家,母亲便告诉他父亲死了。吓坏的齐杰,哭喊着冲出去找父亲,却被母亲一把揪回来,一头磕在门框上,眼角像爆裂的泉眼,汩汩流出殷红的鲜血,顺着脸颊滑入脖子里。母亲吓坏了,大声惊呼,一激动,竟动了胎气,整个人顿时痛苦挣扎着躺倒在地,一个小时候,妹妹齐果出生了。
几天后,母亲收拾好仅有的几件衣服,一手拉着他,一手抱着妹妹离开了那个家,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齐杰没有告诉过母亲,小学三年级的暑假,他借学校组织课外科技行的机会回去过。那片街道已经打算拆迁了,一副破落潦倒的样子,他在那栋房子前站了好久,离开时居然有老邻居认出了他。
那天,他忘记了来时的路,一个人迷路在一片荒废的玉米地里,在那他像被人遗弃的孩子失声痛哭,不是害怕,是因为他从邻居嘴里得知当年是母亲用刀子捅了父亲。邻居还说,是亲眼看到父亲捂着肚子跑走的,血,流了一身。
对母亲,对父亲,对这个家,齐杰有着极大的怨恨,那天以后,他再也没有哭过。
景寒月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齐杰也还是个孩子,正直青春期的他性格倔强叛逆,沉闷失语,对外界的世界只有敌意和厌恶。
变故让年幼的齐杰和景寒月不得不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景寒月,整个世界在黑暗中轰然坍塌。大概是同命相连,景寒月的到来让齐杰内心多了一种安宁,他对她充满了无限好奇,充满了深深的怜爱,甚至还有一种要保护她的冲动。
和景寒月在家一起生活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总是时刻小心翼翼谨慎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他甚至清楚地记得她每次的跌倒和哭泣,他更喜欢她在身后像跟屁虫一样跟随他,轻轻叫他哥哥,哥哥。
这些都是写进童年往事的回忆录,轻写淡描,灰暗冰冷,没有任何的色彩,支离破碎大概是对这些最好的诠释。
“哥,爸妈又吵架了。”景寒月突然说,“这次他们吵得很凶,妈说要和爸离婚。”
齐杰停顿了半步,肩膀抽动瞬间冷漠地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和那种心狠手辣的女人在一起不离婚才怪。”
“你不要这样说妈妈。”
“你不要多管闲事!”
她不敢继续,又突然想起什么,“哥,齐果真的欠了麻子的钱?”
“这些都和你无关!”齐杰停下,双手用力把景寒月往上托了托,微微侧过头,“今晚的事,不许再提,别多嘴,记住!”
景寒月知道齐杰还在生气,不敢再多问,把脸埋在了臂弯里嘴里嘟囔,“还好爸妈今晚都不在家。”
爸爸在工地做活,和同事去拉货了。妈妈要在服装店加班赶做衣服,他们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显出超常的默契,谁也不管谁,各忙各的。
锅里留了晚饭,豆腐,凉拌土豆丝和汤面条,永远是这几样,几年下来几乎一成不变。
景寒月好像早就忘记红烧肉和糖醋鱼是什么味道了,妈妈说那些东西不但贵而且吃多了油就堆积在肠道里对身体还不好,所以家里偶尔才吃一次,而且每次齐果都会三下五除二把肉往嘴里碗里填满,自己一个人都能清盘。记得有一次吃糖醋鱼,她吃得太疯狂了,刺都没吐,硬是生生咽下去,结果卡在了喉咙里,一连三个月都不能正常吃饭。妈妈疯了,像祥林嫂一样每天拍着大腿念叨了大半年,“哎哟,真是浪费,真是可耻,二十多块买的鱼,花了五百多看嗓子,这钱哟……”
没有大鱼大肉,清汤寡水的日子,景寒月也从来不抱怨,有什么吃什么,像个没有要求的傻孩子。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她是知道的,妈妈每天不分白昼辛苦的在裁缝店给人家缝补剪裁衣裤,挣的钱也只够买油盐酱醋。而爸爸工地工作辛苦危险不说,工资总也涨不上去,N年如一日,妈妈每月拿着爸爸微薄的薪水不是皱眉就是仰天长叹。
齐杰看着一桌子凉饭问:“就吃这些?”
“是啊,每天都这样,闭着眼睛就知道晚饭是什么,不过,哥,你要不要尝尝,味道还是不错的。”景寒月咬着筷子说。
“怪不得你瘦,养鱼也没这样养的。”
“萝卜豆腐保平安,妈说的,何况我减肥。”
“再减肥你就可以当水稻苗往地里插秧了。”
说着他的目光不由落在景寒月身上,单薄的身体,纤细无力的四肢,像两枚小翅膀的锁骨突兀着,泛出荧荧的柔白。T恤的圆领已经松垮没型,磨出毛边,纤瘦的肩膀挂不太住,左肩不断往下滑,景寒月边吃边往上拽,不经意间露出白色的细细的内衣带子。她自己不知道,齐杰却看得一清二楚,盯着她的肩膀竟出了神。眼神又滑过那让所有男生都会嘲笑的平胸,脸居然红了。他感觉到燥热不适,强迫自己不再看不再想,这种克制让他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