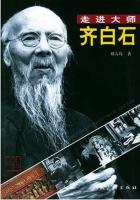观摩课
教务主任开完会回到学校,就急急忙忙推开校长室的门。
“不好了,不好了。”主任气喘嘘嘘对校长说。
“真抽到咱们学校了?”
“抽到了,上头要求必须是三十五岁以下青年教师献一节语文课,全市老师观摩。”
“你这臭手咋这么背呢?”校长也着急了。
学校仅有的一位三十五岁以下的语文教师寒假前刚辞职,可观摩课是放假前报到上级,据说是二十所学校抽十个,校长就没重视。
“要不从别的重点学校借一位。”主任用试探的口气,把心里想好的主意说了出来。
“那不行,那样传出去不让人瞧瘪了?”
最后两个人一商量,让教生物的小牛老师顶替。
“不就一节语文课吗,找一篇跟生物有联系的,让语文组的孔老师帮着写教案,找初中最好的初二二班,多排练几遍不就行了。”校长兴奋地说。
教务主任拍了拍脑门:“我去年听孔老师讲了一节《黔之驴》,这不有驴吗,不行就选这节课!”
“对,有了驴,小牛的专业不就用上了!不就省得露怯了!”
“咱们实验室还有个老虎标本呢,这篇课文正好是老虎把驴吃了,不行就安排在标本室上!”
“好!告诉有关人员,赶紧准备!”
主任告诉小牛时,小牛以为让她上生物观摩课,当即高兴地答应了。如果在市级观摩课上获奖,评中级职称时就多了最重的砝码。等主任说清是上语文课,小牛一下泄了气,连忙摇头。
“你得把这事当成政治任务,这不仅关系你个人,还关系到整个学校的荣誉,关系到明年的招生,关系到我们全体教工的福利……”
小牛只好答应了。
孔老师与电教组联系好了幻灯片,小牛也背熟了教案,孔老师试讲了一遍,小牛也都一一记下,与初二二班排练了四五次,第一个问题谁回答,第二个问题谁回答也都跟学生商量好了,校长、主任这才放了心。
一周后,三十多人的观摩团来了,黑压压地坐满了生物实验室。
小牛毕竟是有几年教龄了,并不怯阵,课讲得很顺利。来听课的老师见到讲台边的老虎标本也觉着新鲜。串讲完课文,该学生回答问题时,出了点小岔子。
应该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学生当天请了病假,班主任一忙活,把这事忽略了。小牛问题问完,故意扫视全班,然后叫出了该同学的名字,连叫了几遍,都没有反应,小牛没教过这个班,对学生本来不熟,心里有点着急。这时,她只好把第三个同学名字叫了出来。第三个同学正心里紧张地默念第三问题的答案,根本没听清老师问的是什么。站起来后,支吾了半天,小牛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这个学生才勉强回答了出来,答得并不准确。小牛只好问第三个问题,问题出口,还没等小牛叫第三个同学的名字,这个学生“忽”地站了起来,非常流利地说出了答案。在场的来宾像被疾风吹过的树木一样有了一阵响动,有人在窃窃私语。
小牛也发现了毛病,登时一个大红脸。结果离下课还有八分钟,课就讲完了。小牛灵机一动讲起了老虎、驴的生理知识。
语文课开头,生物课结尾。
中午就餐,校长嘱咐菜要上得“硬”一点,又临时采取补救办法:每个来宾一人一件高级羊毛衫。来宾都很满意。吃完饭,来宾与校领导在会议室议论这节课。校长、主任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等着批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不少优点,比如:老虎模型生动直观,关于驴的幻灯片创意新颖等等。校长长舒了一口气。
临送来宾上车,观摩团的团长把校长叫到一边,说:“校长,你们老师的课有个明显的问题。”校长一惊,连忙点头:“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团长说:“别的学校老师也准备了好几遍,可没让人看出来是准备过的,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你们这个毛病太明显了,评奖时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三等奖我可以担保,可二等奖……”
校长一下子蔫了。
团长笑了,拍了拍校长的肩膀:“今天就冲你们对我们的工作那么支持。”说着,团长晃了晃装着羊毛衫的手提袋,“我给你们争取争取!”
校长连忙说:“那我就拜托了,欢迎您再来。”
两个月后,小牛的获奖证书来了,果真是个二等奖。
后来教务主任到市里开会一打听,这次观摩课,一等奖空缺,三等奖空缺,十个学校全是二等奖。
又过了一个月,校长收到一封公函,说贵校已有资格参加省级公开课观摩,请教务主任去开会抽签,十选五。
在把公函交给主任时,校长虎着脸说:“你这臭手要是再抽上,你自己去讲!”
冯台长之死
那天一上班,冯台长意外去世的消息像一阵疾风,迅速吹遍了我们这个县级小广播电视台的角角落落。
冯台长去年刚刚退休,年龄并不大,身体也一直不错。虽然按照老林的说法,临退休前冯台长偷偷求人改了户口,多干了两年,毕竟也不算太老啊。说实话,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第一感觉是一丝轻松(这个感觉后来让我很惭愧),之后,才是一点点惋惜。我敢说,其他人也许还不如我呢。在集体去冯台长家吊唁前,好几个人都是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特别是已经是副台长的老林。
冯台长在一把手的位置待了近三十年,我呢正好赶上后十年。这也许是我的幸运,起码老同事们都这么说。
我记得报到那天,我心情忐忑地走进空无一人的台长办公室,从沙发上不知所措地坐下起来好几次,终于等来一个西装背头的干部模样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老林,当时是办公室主任)。
“新分配的大学生?”来人热情地和我寒暄。
我以为是台长了,就恭恭敬敬地点头。“本科毕业,来这里屈才了呀。”他说。这时,一个很矮的小老头拿着一摞报纸走进来,我还以为是传达室师傅来送报纸,刚才那个人殷勤地介绍:“大学生,这就是冯台长。”这就是我和台长的第一次见面。
工作不久,和大家熟悉了,台里的事情也知道了一些,传到我耳朵里最多的,是台长的秘密,这就是,台长几乎和每个人都吵过架,很多人挨过他的训斥。“你也做好思想准备吧。”老林不止一次地对我警告。
在我第一次和他“交锋”之前,我就听说了他的不少掌故。
冯台长是行伍出身,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他偏偏在文革中分配到了一家国内极其著名的电影厂。而且,他曾经和后来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男演员是对立面,两个人各自是两派的头头,斗争得如火如荼。只是可惜,冯台长没有文化,又很刚愎自用,结果,在刷大字报时,把当时一个中央领导的名字中的“彪”字少写了一笔。对手咬住不撒嘴,没奈何,冯台长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也就是我们这个县),很“委屈”地做起了小广播站的负责人。但对于这段历史,他从来是讳莫如深。后来,那个演员出名了,冯台长常常指着电视荧幕上的那个人对我们自豪地说:“嘿,知道吗,我们很熟的!”
他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年冬天的一天,大雪纷飞,在录一个文学广播节目时,他听到“鹅毛大雪”四个字,马上喊“停!”“什么鹅毛大雪?再大的雪花也没有那么大!改了改了!”大家都困惑地看着他,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看到他满脸严肃的表情,才知到他是认真的。播音员小惠一字一顿地说:“台长,那可是成语呀。”他一听,脸上的血管刹时肿成了蚯蚓:“我说改必须改!!”说着,他走到窗户前,看看外面的纷纷扬扬的雪花,回头说:
“改成——鸡——毛——大雪!”
在他的严密监视下,小惠不得不改读“鸡毛大雪”。他刚一走开,气头上的小惠顶牛又改了回来。但是,节目播出时,“鹅毛大雪”四个字还是被他听到了。据说,他立即摔了饭碗,冒着大雪,暴跳如雷地找到小惠家,把小惠批评得狗血喷头,后来,小惠整整写了一个月检查才算完。
第二个故事也没什么新意,就是他非让小惠把“瑞雪兆丰年”改成“皑雪兆丰年”,这次,小惠和他顶撞。他很满意。
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县里成立了电视台,还是广播站原来的班底,所以,冯还是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