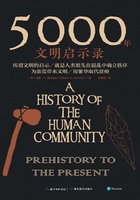且说刘三杀了二癞子和孔令仁夫妇,拿起桌上的笔墨,唰唰唰,写下一行大字,“杀人者,飞燕子刘三是也”。刘三写完后,把笔墨放在纸上压好,开始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寻找开了,不一会,金银细软堆了一大堆,从衣柜里找出一大块红绸子布,铺在地板上,把金银细软全都放在红绸子布上,想了想,见了两块碎银丢在地上,把红绸子布包好,沉甸甸的背在肩上,转身出了房门,又把门锁好,这才飘飘悠悠地来到院墙根下。
刘三瞅了瞅高高的院墙,又掂量了一掂量背上的包裹,太重,飞不上去,必须得用飞爪。想到这里,刘三从腰中掏出飞爪,轻轻一抛,只见飞爪稳稳地抓在了院墙上。
刘三双手一用力,两只脚往院墙上一蹬,嗖嗖两下上了院墙,到了上面,刘三把飞爪拴在包裹上,轻轻地系了下去。然后,刘三飞身下了院墙。
“排长,这么快就完事了?”一名队员小声问道。
“完了,该宰的宰了,该拿的拿了。”刘三笑呵呵地说。
“排长,这包裹里是什么?”另一个队员问道。
“瞧你傻乎乎的样,好东西,金子银子,咱们游击队发财了。走,快走。”刘三命令道。
一行六人离开县衙的院墙,静悄悄地消失在高密县城的茫茫夜色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行在大街小巷。
天光大亮,高密县衙的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味。一名厨子把四菜两汤端到了餐厅的餐桌上,依次摆好,眼睛来回扫了扫整个房间,心中纳闷,这个时候,县长和太太早已坐在餐厅里等着用餐了,今天怎么不见人影呢?
想到这里,厨子向后院走去。来到孔令仁的正房,隔着老远,厨子就喊上了,“县长、太太,该用早餐了。”喊了半天,无人回应。厨子定睛瞅了瞅,房门锁着,看来,县长和太太出门了。
正在这时,孔令仁的办公室传来叮铃铃的电话铃声,值班室的卫兵跑过去,拿起电话,连声“嗨嗨”,放下电话,向孔令仁的正房跑去。
卫兵刚跑过一个拐角,和厨子撞了个满怀,只撞得厨子倒退两步,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
“嗨,谁呀?一大早撞人,干嘛这么急?”厨子两眼冒金星,双手着地坐了起来。“奥,你小子,干嘛?跑啥?”
“唉,山田太君来了电话,找县长,我这不就跑欢得了吗。”卫兵说着,伸手拉起地上的厨子。
“别找了,我刚才去找县长吃饭,喊了半天没人答应,一看,房门锁着,看来县长和太太出门了。”
“不好了,不好了,副队长出事了,二癞子被人给杀了。”一个皇协军边跑边嚷着,慌里慌张地奔后院跑来。
“哎,小六子,你慌啥?卫兵问道。
“不、不好了,县、县长呢?二癞子副、副队长被人杀了。”小六子哆里哆嗦地说着。
“什么?副队长二癞子给人杀了?”卫兵问道。
“可不是吗,我叫副队长吃饭,他的房门锁着,我从窗户的玻璃缝里往里一瞧,我的妈呀,二癞子脖子上的血流了一片,把白床单和枕头都染红了。”小六子定了定神,不再那么害怕了。
“你是来找县长?”卫兵问道。
“啊,对呀,我的汇报呀。”小六子说道。
“糟了,快,小六子快把县长的门撬开,恐怕,嗨,你快点呀。”卫兵催促道。
小六子不敢怠慢,拿了把锤头咣咣两下就把孔令仁的房门砸开了。卫兵和小六子进到里面一看,我的娘,吓得回头就往外跑,边跑边喊,“不得了了,县长和太太被杀了,县长和太太被杀了。”
一时间,孔令仁的房前围了一大堆皇协军。卫兵一个电话打到了宪兵司令部,山田一撂电话,带着一队日本宪兵乘车赶到。
山田和黄二狗等人走进孔令仁的卧室,眼前的惨象惊得山田和黄二狗脊梁沟里直冒凉气。孔令仁和他的太太尸横床上,鲜血流了一大片,从床上都流到了地上,床头上的血点子喷得到处都是。
山田用带着雪白手套的手捂着鼻子,皱着眉头,站在地上发着愣。“大佐,你看,这里有字。”黄二狗指着桌子上的一副字条说道。
“杀人者,飞燕子刘三是也”几个大字映入山田的眼睛。“八格牙路,又是这个刘三,命令,全城戒严,全力捉拿飞贼刘三,挖地三尺,也要把刘三捉到,我要活刮了他。”山田气的脸色发青,皮靴子踹的地板嘭嘭作响。
一时间,高密县城鸡飞狗跳,日本鬼子和皇协军一队队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挨家挨户搜查着刘三的踪迹。
“该,活该,阎王叫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五更?叫你嚣张,叫你飞扬跋扈,啐。”卖肉的小二嘴里小声嘟囔着,瞅着过来的一队队鬼子和皇协军。
“哎,你认识这个人吗?”一个皇协军走了过来,拿着一张画影图形往小二脸前一递。
小二看了看那张画像,只见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嘴角左上方一颗小小的痦子。说道,“老总,俺是卖肉的,不认识。”
“******,不认识就不认识,还他娘的卖肉的,谁不知道你是卖肉的。记着点,看到这个人马上报告太君,听到了吗?”那名皇协军骂骂咧咧地说道。
大栏镇福生堂的前堂里,赵怀庆、司马亭、三姨太等人围拢着刘三一行六人,兴高采烈地听着刘三讲诉着锄奸的经过。
“同志们,刘三同志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既打击了山田的嚣张气焰,又没有暴露自己的目标,是一次定点清除的典型战例,希望大家认真地总结经验,好好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赵怀庆听完刘三的报告,借题发挥,表扬了刘三等人一番。
“还有,刘三同志这次秘密行动不但除了恶,还给咱们游击队带来一笔不小得财富,这些金银可以好好地武装一下咱们的游击大队,咱们的游击大队就是缺少枪支弹药啊。”司马亭悲伤地劲头稍微好了些,话也多了起来。
“嗯,司马亭同志,咱们大栏镇游击支队元气没上,还有一百多人,这可是咱们的根基啊,要想发展,必须注意保护自己,必须做到警惕性第一的原则,千万不要放松这根弦,否则,咱们就要吃大亏。”赵怀庆语重心长地说道。
“是啊,咱们大栏镇的灾难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刻骨铭心啊,你放心吧,赵政委,从今往后,就是不睡觉,也要把警戒线卡严了,否则,一旦被敌人得手,我们就会成为人民的罪人。”司马亭真正认识到了大栏镇的惨痛的教训,从认错的态度就可以看到司马亭豪爽的性格。
“这样吧,大栏镇就交给在座的诸位了。游击大队早已回去了,大队长李铁汉开会还没有回来,哪里少不了我呀,我必须走了。还有,玛洛亚同志正在养伤,需要人照料,我看,王丽怡同志随我一同回老河套,等玛洛亚同志的伤好了,你们一同回来,怎么样?”赵怀庆说完,看了一眼司马亭和三姨太。
“我正有此意,你不说我还想让你带上王丽怡同志呢,王丽怡同志,你就放心去吧,大栏镇就交给我了。”司马亭毫不掩饰地说。
“这,好,我听从组织的安排。”王丽怡看了一眼司马亭,又看了一眼赵怀庆,小声说道。
中午时分,一马一驴出了大栏镇,赵怀庆和王丽怡消失在大栏镇西南的一大片树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