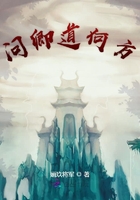高密人天生有一种倔强的性格,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高密的地好像也受的了感染,带着灵气,大灾过后的二十多天,又重新长出了绿叶,披上了绿装。除了折断茎杆的,其余的又齐刷刷地生长着,努力地伸长着茎干和叶子,好赶上秋的季节。人们的心里有了底气,不再像前几天的样子,垂头丧气的,重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拿起家中的农具,走在田间地头,除草的除草,保苗的保苗,一派繁忙景象。
“啪啪”老李头赶着羊群,鞭稍在空中打着旋,抽得山响,羊群里的一只只羊训练有素地走田间小路上低着头走着,没有一只羊东张西望,或者偷吃口庄稼的。
“喂,老李头,你可得管好羊群啊,新长出的叶子不容易,莫让羊吃了。”司马亭骑在青鬃马上“哒哒”地从老李头身边经过。
老李头忙答话,“镇长,你就放心吧,它敢,若是吃了一片庄稼叶子,回家我宰了它,炖了肉给你送去。”
司马亭在马屁股上猛抽一鞭,青鬃马“哕哕(huihui)地叫了两声,四只碗口大的黑蹄子猛地刨在地上,尘土飞扬,消失在镇南口的庄稼地里。
骑在青鬃马上的司马亭一路溜着弯,寻思着怎样赈济大栏镇老百姓的事,思来想去每个头绪,正想着呢,青鬃马窜出高粱地,上了官道。
“对,找县长去,或许他能帮上忙。”司马亭这样想着,一拨马头,青鬃马前蹄悬空,后蹄着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回旋,“啪”地一声鞭响,青鬃马箭一般地向高密县城飞奔而去。
走在去高密县城的路上,司马亭一边催马一边细细地思量着,“孔令仁县长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啊,再怎么样他也得帮这个忙,高密东北乡这么大的天灾,他能不管?不能呀,他是高密的县太爷啊,是高密的父母官啊,他不管谁管。”想到这里,司马亭心中更加有了底气,啪啪两声鞭响,青鬃马撒着欢地跑了起来。
一进高密县城,县城的繁华是大栏镇比不了的,虽说大栏镇是高密出了名的大镇,但同县城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街道又宽又直,街道两旁的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商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小商小贩沿街叫卖,吆喝声不断。
司马亭顾不了这些,扬鞭催马直奔县衙而去。到了县衙,门卫拦住了去路,司马亭勒住青鬃马,骗腿下来。
“干什么的,骑着马跑到县衙来干嘛?”卫兵斥问道。
司马亭扭了扭脖子,撇了撇嘴说道,“怎么,不认识我?我是大栏镇的司马亭,来找你们县长办事,孔县长在家吗?”
卫兵一听说是司马亭,我的个娘啊,名气太大了,高密有谁不知道司马亭啊,忙说道,“司马镇长,我们的县长在家,就在县衙的后院,我领你去?”
司马亭说,“不用了,把我的马拴好。”说着,把马的缰绳递给卫兵,径直向县衙后院走去。
一进后院,司马亭就看见孔令仁正在拿着把水壶浇花呢。孔令仁见司马亭来了,忙放下水壶,说道,“司马老兄,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快请进,到客厅说话。”
司马亭说,“闲来无事闷得慌,骑着马跑到县衙找县长聊聊天,解解闷,哈哈。”二人说着,打着趣话,走进了客厅。
县衙后院的客厅里,县长孔令仁和司马亭喝着酒,醉醺醺的孔令仁端起酒杯对司马亭说,“贤弟啊,你的三姨太还称心不?”
司马亭见他有些醉意,就说,“孔兄见笑了,托你的福,我的三姨太那是可人儿,既知书又达理,还挺贤惠。不说这些了,咱俩谈点正事。”
孔令仁“滋溜”一口把酒喝完,看了看司马亭,歪着脑袋,斜着眼问道:“正事,什么正事?”
司马亭说,“前一个半月,咱高密闹虫灾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孔令仁加了箸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嘴巴“吧嗒”了两下说,“听、听说了,你看这蝗虫闹得,哪儿来的这么多蝗虫?真是的,听说你的大栏镇最严重。”
司马亭听到孔令仁这些话,心想有门,忙说道,“既然县长大人我的孔兄都知道了,想必有很好的应对之策了?”
孔令仁听出了话里有音,慢条斯理地说,“我哪有什么应对之策,现在,国民政府催粮催捐逼得紧,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这些当官的朝不保夕,那管得了这些烂事,再说了,再过几天我就要调离高密,到别处上任了。”
司马亭心中凉了半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这也不能不管啊,一个大冬天,过了年还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季,老百姓还不全饿死?”
孔令仁瞅了瞅着急红眼的司马亭,大嘴咧了咧说,“天上下雨地上流,自己的事自己犯愁,我抬屁股走人,司马亭啊司马亭,又饿不死你,你着这么大急干嘛?真是的。”
司马亭见话说到这份上,气呼呼地说,“你是一县之长,一天不走,就是一天的父母官,这么严重的虫灾,政府总得发放粮食赈灾吧?”
孔令仁没好气地说,“你说得轻巧,上面不放粮,我拿什么给你们?得了,我家还有三袋大米、两袋白面,不嫌弃的话,你驮回去。”
司马亭说,“去你的,我还是管下任县长要吧。”吃完饭,司马亭告辞孔令仁,打马会大栏镇去了。
转眼间,秋收的季节来到了,大栏镇的人们都在风风火火地收庄稼。高粱一片一片地砍倒了,玉米叶一块一块地放倒了,大栏镇的人们手掂着高粱穗和玉米,只觉得像没拿东西一样,心里不是滋味,空落落的。
司马亭骑在青鬃马上,带着狗三、猫四在田间地头溜达着,察看着秋收的进展,秋粮的收获不由的使他紧锁双眉。
正走着,身后的玉米地里传来了声音,“司马镇长,这下完了,你看这棒槌,这么小,比起去年小了两倍,顶多有四成的收获。”
司马亭回头一看,原来是二愣子。下了马,走到二愣子身边,拿起玉米棒子在手心里掂了掂,叹了口气,“这都是蝗虫造的孽啊,可怜了这方老百姓了。”
二愣子说,“是啊,镇长,这可怎么办啊,到冬天我们这些老百姓还不饿死?”
周围的人看到司马亭和二愣子说着话,纷纷围拢过来,越围越多,七言八语的,“镇长,没法活了。”“还得交租子,可这交了租子,我们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大人们饿点就饿点,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挨肩的,可怎么办呢?”
司马亭用手挠着头皮,看着可怜的众乡亲,大声说:“老少爷们,父老乡亲,我司马亭也正在犯愁,犯愁归犯愁,办法总会有的,请大家放心好了,都回去忙活吧,散了散了。”
众人各自散去,司马亭叹了口气,骗腿上马,对狗三、猫四说,“你们先回去,我去县城一趟。”说着,打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