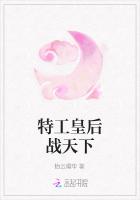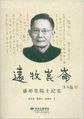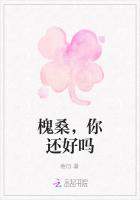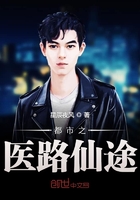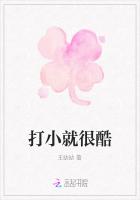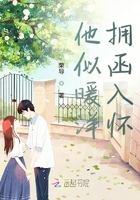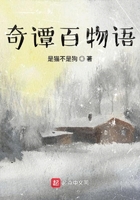活着的人,应该时刻都要想想活着的意义,因为谁都会有一天唤不起活着的回忆。
杜静红早就知道自己只能再活十五年或者十年,对于她来说,这就很满足了,到时候她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年月中,她摆脱了长期疾病给她带来的痛苦,愉快地利用生命的每一刻钟。年轻人是很不容易理解这种还可以活多久岁月的心情的,黎丽就很不明白杜静红为什么那样严格地每天写日记,即使在动了大手术以后,也要口述出来,让黎丽帮她记在日记本上。
“杜书记,我的文字可蹩脚,别人看了……会丢人的。”“自己的日记,还怕丢人?”“我当你要写一本大书,将来出版。”“大书?出本大书干什么?”
“那你天天写干什么?”
这天,她说话太多了,黎丽不让她再说了,她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天,她把随身带来的一本高中语文课本拿出来,这里有一首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她问黎丽:
“你读过吗?”
“读过。”
“你昨天问我的事情,这首诗有两句大致上可以回答,你找找看。”
黎丽找了很久,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可是猜不到杜静红说的就是“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花等闲度”这两句。
黎丽就是因为没有从这两句话中发掘出更深刻的意义,所以才不敢大胆地锻炼她的受伤的腿。可是刘海英——这个才十六岁的小姑娘,为什么居然想到“要活,不要安慰”呢?起初杜静红以为她得了一种很危急的病症,有生命的危险。后来医生说,小姑娘的生命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两条腿有可能残废。这么说,她是可以活下去的。残废了当然很可惜、很痛苦,但毕竟和不能活有根本的区别。“要活”,大概是小姑娘想和千千万万小姑娘那样快快乐乐地生活:也能去学习,也能去工作,也能去跳舞。“不要安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小姑娘知道自己残废了,用不着给她说安慰的话呢?
不对,不对,一个人的腿残废了还让人别去安慰她,这就不是“要活”的挣扎声和求援声。从小姑娘的举动和情绪看来,她这两句话也不像是因为残废而发出的绝望的呼喊声。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呢?这几天,她终日在书本里找寻,看来,决不是找寻排遣寂寞的故事或者沉迷在有趣的描写里,是在找寻……这很难说,也许是在找寻一生的答案。须知,她才十六岁。在她此后的一生还要走多么长远的路啊!可是她的腿不能走了。“这是一种需要别人给予帮助的声音”,杜静红这样想。
一个人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生旅程中,少不了要在逆旅上度过一些时刻,这不光指旅途中住客栈,还可以包括更加广泛一些。比方说,住医院就可以看成是病人的逆旅。人们在逆旅度过的时刻有长有短,但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白白度过,应该在这临时结成的集体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应该把逆旅看成是学校——医院难道不可以变成充实病人生命力量的学校吗?病人在医院里度过的是生命受威胁的时光,医院就是要给病人解决生命的问题,那么医院为什么不可以使病人更深刻地认识生命的意义呢?……杜静红这两天从小姑娘那句话想到这个问题,后来她觉得这种想法未免可笑,因为医学到底是一门自然科学,生命的意义却是另外一门学科解决的。虽然这样,她仍然不放弃找小姑娘好好谈一谈的打算。她不能让这样一个十六岁就半身瘫痪的小姑娘徘徊在人生歧路上,应该让她懂得此后怎样坚强地活下去。
遗憾的是杜静红始终没有机会和小姑娘谈什么。她是聋子,又成天捧着一本书面向墙壁躺着,沉思着。那么好吧,过两天再找这个机会吧。
病人的日子有时很短——当他在梦幻里昏昏沉沉地漫游的时候,一晃眼就是好几天;有时却很长——当他神智清醒之后静静休养,计算着阳光什么时候从东边出来,什么时候照到西窗,那个大钟的嗒嗒声,简直是令人非常苦恼的。在这样的时光里,要是有喧闹的笑声,激烈的争论,热情洋溢的歌唱,欢腾雀跃的聚会,那该多好啊!
有一天,病室的门大大敞开,院长领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军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年轻人,他们像乡下人过年串亲那样提着各种各样的礼物,喧喧嚷嚷地走进病室。值班护士虽然叫他们尽量小声一点,但是他们似乎再也抑制不住那种非常亲热的情绪,飞也似地跑到小姑娘的病床跟前……
“小海英,给,这是葡萄干。”
“小海英,给你两个伊犁大苹果。”
“林班长给你用钢管做了个小笛子。”
“小海英,团支部给你送这些书。”
“小海英,这是骑兵连给你的慰问信。”
“小海英,这是拖拉机队的……”
“小海英,赵大个子让我捎话问候你,他给你这个……”说话的人,抱着一个水瓮似的大西瓜。
“小海英、小海英”,满房子都是“小海英”的声音,满房子都充满了亲热和欢跃,连那永远不动的窗幔,也轻微地颤动着。病人们纷纷坐起来,高兴地看这热闹场面。
小海英早就搂着一个女同志的脖子,让人家帮她坐起来。她对着这么多农场来的好朋友,笑起来了。老太太大声地念了句“阿弥陀佛”,自己就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开心地笑着:“呀呀,原来会笑,会笑……呀呀,好孩子,笑喽……”“你看,她笑得多好看,就像脸上开了朵花。”“我敢担保,这一笑,病就更好治了。”
“那个老头儿,是她父亲吗?”
“不是,是场长。”
全病室的病人都为这种欢乐的聚会议论开了。但是没有多久,小姑娘突然伏在一个女同志的肩膀上放声大哭起来,好像把满腔衷情和所有要说的话全部倾泻出来那样。这是她到了医院以后的第一次哭声,不知道大家早料到会这样,还是认为她应该好好哭一哭,全病室的人都觉得痛痛快快哭一阵才更好。甚至她的哭声听起来也是爽朗的、清澈的,像小河里淙淙发响的水声。唉!这比她几天几夜一直捧着一本书沉思着的闷劲好受多了。
“大概她会轻松一些了。要知道,这是两条腿瘫啦,可不是拔了颗烂牙……”
“是呀,一辈子的事情,没有脑筋的人才不会哭。”
“如果是我……”黎丽也哭开了,“我摔折腿的时候,整整哭了两天。我不愿做个跛子,那怕只跛一条腿……”
“别这样……”杜静红在黎丽的耳边悄悄地说,“你会把人们搅乱的。现在她快哭完了,我们听听她说什么。”
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之后,天空不是一下子晴朗得了的。小海英擦干了眼泪,还在抽抽嗒嗒地大口吸着气。谁也没有说她什么,可是她好像是朝所有的人承认自己的错处:
“我不该哭,哭是懦弱的表现……”她后来的说话,才使杜静红明白她不是“要活,不要安慰”,而是有一桩叫人听了十分敬佩可也难免有点心酸的心事。她说:“我至少也得做个有用的人,我要那样活着,不要安慰。”好像安慰使她遭了多大的委屈,她泪汪汪地说,“我已经这么大啦,应该做个有用的人,所以我就去克服耳聋。我不明白,干吗耳聋还没有完全克服掉,跟着又瘫啦?这下,我变成更加没有用的人啦……我忍不住就哭起来啦……”
她这么一说,使好些人的喉头也有股不大好受的辣味呛上来。可是一个铜钟似的声音响起来了:“同志,你因为这个原因哭,那不算懦弱。是的,不算懦弱。”一直和院长站在一边的老军人,笑眯眯地说起话来了。谁都以为他会像老爷爷对待小孙女那样疼爱她、勉励她,劝她用不着哭,病是可以慢慢治好的。想不到他用“同志”这个称呼唤她,说起话来还明显地带着尊敬的口气。他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一种极其关切的心情便流露出来了:“你想过很多事情吗?”
“想过。”
“告诉我吧。”他说得很简单,但谁都相信那是一定会实现的。
小海英咬着指甲,慢吞吞地说:“我,想了……想了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杜静红想起了,小海英对着书本沉思正是三天三夜。那么说,她的确是一面读着书,一面就想着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这样厉害地折磨她呢?
“说吧,小海英。”
她的眼睛低垂下来,沉默了很久,好像并不想将心里的事情告诉这么多人。院长就向护士使着眼色——让邻室跑来的病人走开。正这么打算,她却非常流畅地说起来,她说话的声音简直和小孩子差不多,常常给唾沫噎着,并且谁也不看,似乎是她在一间空洞洞的屋子里自个儿跟自个儿说。
“我想过妈妈……多半在晚上,这盏大灯熄了,光剩下那两盏小灯还亮的时候,妈妈就好像在灯光里走出来……我的妈妈多么好,她一定很挂念我……”
她说到妈妈会想些什么事情,连杜静红也深深地叹了口气。可是她再说下去,人们就给她的思绪拉到另外一个方面了——她这三天三夜想得真多,想妈妈只是次要的一件。她说:“……人家都说,残废也不要紧,好多人残废了,仍然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要是哭鼻子,同志们会不会说我悲观失望,不学习人家的榜样呢?妈妈教我要找榜样,我不是找了吗……”她随手拿起一本书,好像落在书页上的泪水还没有干,她用手绢擦了又擦。“我知道保尔也是瘫啦,我看看他瘫了之后是怎样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好学习他……”
她翻开一页书,这页书用红铅笔划了很多线条。大概在第一次读它,划了一条;第二次读它,又划了一条;最后划得只见一片红色,连字迹都几乎辨认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