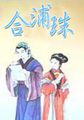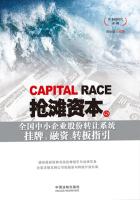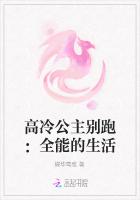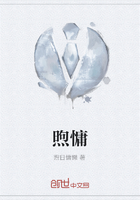挂在墙上的大时钟正好指在八点,阳光便非常准时地透过低垂的窗幔,在第五号外科女病室的地板上印出华丽的米黄色花纹。电炉子上的蒸煮器开始发出非常轻微的咝咝声,药房传来玻璃器皿低低的碰击声,医生办公室有人沙沙地走动和忙碌地翻着纸页,过道里也飘进来一股医院特有的、严肃的石炭酸气味……病房的一切活动都好像被一种浓缩的安静气氛小心翼翼地包围起来:穿着软鞋的护士轻轻地走过;安装了软胶轮的送药小推车,无声地从这张病床滑到那张病床;戴着大口罩的医生耳语般向病人提出问题;就连那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关进窗子里的蜜蜂,也是轻轻地撞击着玻璃……
病室的墙壁,就像覆盖着积雪的草原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那样洁白。被单和枕褥,床架和桌子,所有一切一切,除了那只长方形的大搪瓷盆漆了一圈深蓝色的边框以外,几乎都是白色的。从窗幔渗进来的那些米黄色亮光,委实已经使病室变得很明亮了,但是杜静红同志仍然觉得这里有一种幽暗的感觉,好像什么东西都蒙上一层寂静的白纱。最低限度,这里的空气是流动得很缓慢和很平静的,窗幔从来没有给风轻轻地掀动过,这当然是一点都不假。
四十多岁的区委副书记杜静红得了很久的十二指肠溃疡症,上星期医院给她动了手术,将溃疡部分切除了。她从迷迷沉沉的昏睡中清醒过来今天算是第三天了,她很想活动一下,可是觉得很软弱,连抬抬手的力气也没有,只能靠着倾斜的床架半卧在枕垫上。这也很好,她可以将眼睛自由地转动一下,看看别的病人是怎样活动的,听听她们谈些什么。她和这间病室的七个病人多半已经认识了,并且了解她们一些事情。
在她左边病床的,是一个很美丽的女青年。她有着一双没有人不羡慕的眼睛和很长的腿;腰肢很细,各部分都很匀称,这是一个演员特别需要的身段。她就是一个舞蹈演员,名叫黎丽。只可惜,她的左腿骨折了,用石膏绷带裹起来,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三个月。上月总算把石膏去掉了,医生送给她一副木头拐杖。
很难想像一个舞蹈演员怎样去和木头拐杖结伴,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她的生活中会出来一副拐杖。虽然医生事先就说明,这是暂时帮助她练习走路的东西,以后可以把它抛进炉子里。但是黎丽接到木头拐杖伤心得流下泪来,一直没有用它。有一天,她用指甲轻轻地弹着拐杖的木头,神志黯然地听了一会儿它那毫无生命的笃笃声,忧郁地问杜静红:
“一个工人离开了工厂,那会怎样?”
杜静红默然地帮她理着柔软的长发,停了很久才问她:
“你愿意把头发剪掉吗?”
“不。”
“为什么,图好看吗?”
“图好看?”黎丽有点不满意了,“为什么图好看,我的工作需要它。”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我是问,如果一个工人离开了工厂,他心里会……”
黎丽有点发窘了:“这和头发有什么关系?”
杜静红安静地对她笑着说:“你刚才问得很对。我们的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而且热爱它……”
杜静红对于黎丽的心情是了解的。有一天晚上,有人把一架留声机搬到病房里唱。放到一张荷花舞的唱片,她看见黎丽呆呆地坐在床上。吊在床沿的脚合着舞曲的节拍,轻轻柔柔地摆动,这说明她多么恋念自己的队伍啊!
“黎丽,你要回去,回到舞台上去。你干吗还要问我呢,舞台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和工厂对于工人是一样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黎丽悲伤地摆动了一下腿,“可是它……”又摆了一下拐杖,“还有,它……”她哽咽起来,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一个演员每次在舞台上的成功——哪怕有时她只在舞台上出来了一分钟,或者只跳了优美的几步,也是完全靠长期的刻苦锻炼得来的。黎丽从参加艺术活动起,始终没有间断过一种重复了千百遍的基本训练的动作——将右腿向后高高翘起,左腿支撑着全身重量,并使身体向前倾斜,就像一只仙鹤开始飞翔的姿势。她开始练习这种基本动作,只能保持二十秒钟的平衡,后来可以保持五分钟、一刻钟,甚至半小时。她的腿弹跳起来变得非常有力,却又丝毫不露出通常用力的紧张神色。每次演出以后,人们都称赞她的舞步轻盈得像只燕子。黎丽明白,观众虽然是在为舞台上的她鼓掌,实际上是为她在练功室的努力鼓掌。如果不是那种刻苦的基本训练,她在舞台上走起来,未必会比鸭子走得更好看一些。而现在哩,别说用左腿支撑全身的重量啦,就算让它稍为挨一挨地板,骨折的地方也仿佛要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就像两根折裂的木柴互相摩擦那样。医生说,她的腿骨完全接好了,愈合了。黎丽想,那不过是一种宽慰的话罢了。腿没有长在医生身上,而是长在她的身上,她还不知道一条健康的腿和一条骨折的腿有什么区别吗?医生让她扶着拐杖学走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有人说过,要是腿骨没有完全长结实便勉强学走路,将来会变成罗圈腿的。难道她能用罗圈腿跳给观众看吗?
黎丽旁边的病床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她患的是一种半身不遂的病症,几次三番要她的儿子赶快把她接回去,说是她的病是老人的病,已经到时候了,不必再花钱了。她越是这么说,精神反而越好,连已经麻痹了的左手也可以活动了。老太太是个心肠很软的人,最害怕看打针。她叮嘱儿媳妇,如果孙子有什么伤风感冒,一定要找老郎中把脉,千万不要往医院里送,“那么一只银花大针往肉里戳,吓死喽……”
靠近大门的那张病床,是胃溃疡患者张玉华,人家背地里叫她“花老鸦。”“花”字是很容易理解的,谁都穿医院发给的衣服,只有她在印着红十字的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像锦鸡毛那么鲜艳的花棉袄,走过的时候,人家都看她。至于为什么还叫“老鸦”,后来杜静红才捉摸到一点意思。原来,张玉华是病员里最活跃的一个,她的话可真多,谁也不知道的事情她都能打听出来,当然带着几分夸大和掺上大量的自我炫耀。不过说实在的,张玉华也有张玉华的好处,如果别人把她吹嘘的事情揭穿了,她也并不生气和非坚持自己的说法不可。她是个有趣的人,所以愿意跟她说话的人也很多。
医生上午查病房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病人一天最悠长的时间又开始了。张玉华照例活跃起来。一个人,除非他熟睡了,否则让他完全静止下来是不可能的。杜静红很了解自己也有这个特点。现在她既不能动,又打不起精神读书,甚至连睁开眼睛多看一看周围的东西都很疲倦,她就很想听听别人说话,这是她惟一的活动了。她非常用心地听着……
“……我在上海,还没有见过这种蹩脚医院……”这是张玉华的声音,大概她一定指手划脚,绘形绘声地说:“医生不会用药,光会用刀子,动不动就抬进手术室……”
“动手术比用药更难。”有人反驳说。“嘘嘘,你说的,吃药好受,还是动手术好受?”“当然是吃药好受。”另一个病人同意了。“你们看,我本来是胃溃疡,应该住内科,可是硬要我住外科。干嘛?我昨天打听出来了,他们是不打算用药,要给我开刀。喏,用刀子把肚皮破开……在这里……在这里用个钳子把胃夹住……在这里……在这里把胃拿出来……吱、吱、吱,用刀子切去一半……”
“哎呀,妈呀!”一个年轻的病人惊叫起来。“张玉华,别胡说吧。听说医生是给你做组织疗法,不过是切开点皮埋组织片。”“哼!就算是组织疗法,反正是……”张玉华不等人家反驳她,便神秘地说,“你们知道吗?杜书记,活不长了……”“嘘——”她听见黎丽压低了嗓子,恶狠狠地警告张玉华:“我不准你说她!……要说,就说你的。”“唷!看你这样儿,凶得像只老虎……”张玉华居然卖起关子来:“不说就不说,你当我又是胡说吗,我是亲自听院长说的……”“院长说什么呀?”
“张玉华,说呀,杜书记怎么样?”“杜书记睡着了,不要紧,说吧……”“嗯嗯,你们放心,我就说……”经过这样荣幸的三催四请,张玉华郑重其事地说开了,“她这病得了快十年,大肠烂了好大一截……”“不是大肠,是十二指肠;不叫烂,叫溃疡……”“就算十二指肠。你这人怎么啦,今天光盯我……医生说,给她割掉好长一截……这么说,她只能再活十年,最多十多年……”
较远的病床有人在呻吟,声音逐渐大,似乎是发着谵语:“……我的腿……同志,给我腿……”护士给她敷上冰袋,呻吟声逐渐低下去,后来又睡着了。
“她的腿怎么啦?”张玉华说:“她的腿得了坏疽病,昨天开了刀……割是割掉了,恐怕会变成跛子……”黎丽悲伤地叹息着:“怎么又是跛子呢,真是怪事。”“怪事?怪事多着哩。上星期送来一个被水淹死的小姑娘,怕只有十六岁吧,都说没救了,可是居然救活了……”张玉华的声音逐渐大起来:“救活了又怎么着?原来是个瘫子,不会走路;医生说给她治瘫,可她什么话也听不懂,原来又是个聋子;聋子就聋子吧,偏有个怪毛病,不让医生戴口罩,叫人家脱下来——医生还能不戴口罩吗?都说她有神经病,是个疯子;可疯子会看书吗?她偏偏会看很多书,床上、枕头边、小柜子里,不知道谁给她搬来这许多书,这么着,医院算是出了个孔夫子。”
“你说得不对。那个小姑娘虽说是个聋子,可是能用眼睛看出别人的嘴巴说什么话。医生给她看病,都得取口罩。”“能看出嘴巴说什么话?哈哈,你的神经别也是出毛病吧?”“真是这样。我昨天看见他们农场一个拖拉机手,是她的同学,她给我讲的。”
“听说,这个小姑娘来历可不简单,她抢救了很多棉花,扳了个什么闸,掉进水里给淹坏了。”
“她是个有功的人。张玉华,你少嚼舌头吧,什么疯子、聋子、孔夫子的,当心嚼烂了舌根!”
“我嚼舌头?你们看,她搬来我们外科病房住了。喏,可不是带着很多书吗……”
接着,移动床的轮子,在地板上辘辘滚动的声音由远而近。杜静红睁开眼睛,看见护士将一个几乎还像小女孩似的姑娘从移动床上抬下来,安置在她右边的病床上。随她一齐搬来的,还有一个帆布军用背囊,的确像张玉华说的装了很多书。病人们都走过来看这个小姑娘。杜静红连忙招呼黎丽:
“黎丽,你扶我坐高一点……再高一点。”
杜静红坐高了一点,便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这个小姑娘了。她的确只有十五六岁,十分消瘦,细细的眉毛却很黑,眼睛又圆又大,闪着莹莹的晶光;嘴角紧闭着,向上微微翘起,她那童稚的痕迹还没有从宽阔的额角上完全消褪;青春的特征也同时在她的双颊出现了。她凝然不动地坐在洁白的褥单上,就像一个少女石膏塑像被一圈白布缠绕着,多么洁净、多么纯真、多么美丽。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不光杜静红,几乎所有病人都不相信张玉华说的话是真的——要知—她怎么会是一个又聋又瘫的人呢?道,她还不大懂得世事啊!
看见这个小姑娘,杜静红不知为什么很想抚摸她一下,把她搂到自己的怀里,让她把心里的话讲给她听。难道她那微微翘起的嘴角不是表示要将自己的心事说一说吗?说吧,说吧,都说出来吧。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起初杜静红以为自己的声音太弱了,又提高了嗓子再说了几遍。后来她终于明白了,小姑娘的耳朵的确是聋了。
杜静红想起了,在她动手术前一天,同志们给她送来一盒小巧玲珑的点心和一罐蜜饯苹果。她让黎丽把东西拿出来,招待招待新来的客人。这当真起了点作用,小姑娘黑莹莹的眼睛朝她看了一看——多么聪明伶俐的眼睛啊!杜静红非常高兴地向她笑着,用手比划着,请她吃。但是小姑娘将点心推开,黯然很久,才用很低微的声音似乎对自己说:
“我要……活着……不要安慰……”
这句断断续续的说话,使杜静红全身震动了一下,她听到的是:“要活,不要安慰。”
此后,小姑娘再也不说话了。她倒卧在床上,脸朝墙壁,成天捧着一本书默默地读着、沉思着;读到某一页又急忙翻回来找寻,找不到又翻回去……
偶然听见她独个儿喃喃低语,好像是呓语,又似乎是对着墙壁中出现的一个人影诉说。
只有让她吃药的时候才转转身,吃完了药又翻回墙壁那面了……她这是干什么啊!难道是在书本里寻找遗失了的东西?也许是在那里找寻答案却没有找着。一个人知道自己瘫痪以后,按理说会悲切地哭泣起来的,她没有哭。但是这种沉思、追忆、渴求、找寻和找寻不到而茫然的神色,比哭泣更使人难受。
“我真是害怕,她应该好好哭一场才好。”黎丽恐惧地说,“可是她不哭,好像哭出声音怕有谁打她。这样下去,能把人憋死的!”
“她叫什么名字?”
“叫刘海英,今年才十六岁。”
“她得的是什么病?”
“不知道。医生光说,她瘫痪了。”“瘫痪?像老太太那样,半身不遂吗?”“不是那样。医生说,她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冷水里泡了半夜,两条腿瘫了,不能动了。”“嗳,真是可惜……”难怪大多数病人在住院的时候,护士都送来一双布制的软拖鞋,只有这个小姑娘没有。杜静红默默地记住了她头一句话:“我要……活着……不要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