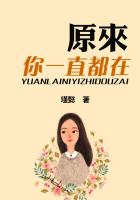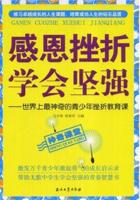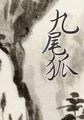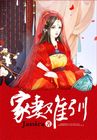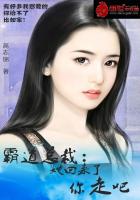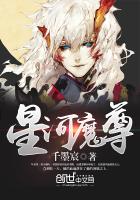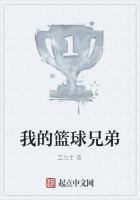“这里写着,他的两只眼睛瞎了;这里写,他全身瘫痪,动都不能动啦……”她多么同情保尔的不幸,同时又觉得自己的不幸比起保尔来简直微乎其微,几乎是抱歉地说:“我比他好得多,我只不过是耳聋,两腿瘫痪,但眼睛是好好的,一双手也是好好的,我干吗不能向他学习呢?可是……”
此后,她的说话变得非常高亢,非常急速,听着听着,叫人透不过气来:
“可是我能和保尔比吗?保尔是个英雄,他在没有病以前,参加过伟大的革命斗争、打过仗、杀死很多敌人;后来他虽然瞎了、瘫了,可是他躺在床上,能把他的一生写成一本书,全世界人民都看……他当然可以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可我哪,我什么也不会,我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只好当供养人员,让人民白白养活我……”她停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妈妈说,这样的人活着一天就是虚度一天;活一辈子虚度一辈子。我的确不愿碌碌无为,可我怎么能和保尔比哪!我怎么能……”
杜静红一边很认真地听着,一边很严肃地默默想着:在祖国的边疆——在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僻静角落里,有一个才十六岁的小姑娘。她的耳朵虽然聋了,但是她为了达到“至少也要做个有用的人”的目的,很快就找出一种方法,用眼睛看懂别人说话,克服了耳聋。后来,她因为抢救国家财产,掉进水里昏迷了,送进医院又变成一个两腿瘫痪的人。她不因今后怎样生活而伤心,却和保尔比了三天三夜,沉思了三天三夜。她想的是因为比不上保尔,比不上一个驰名世界的英雄!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姑娘啊!谁把她教育成这样,谁能把她教育成这样呢?
老军人用炯炯的目光看着小海英,这目光倾注了无限同情,倾注了更多的鼓励。海英说完了,他才用有力量的嗓音毅然决然地说:
“你想得有点不对。”所有人都惊讶,杜静红起初也不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老军人确切地说:
“是呀,是有点不对。你和保尔比,是比工作能力,你怎么能比过他呢?我好像跟你说过……”他思索着,敲着斑白的鬓角,想起来了:“种树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记得,你给我说过白求恩大夫。”“不止,还有怎样做一个……”“对啦,对啦。你说,我们的人,应该是高尚的人、真正的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活着的目的,要为人民工作;死了之后,要给人民留下好处。”“对喽,这不就行了吗?”“老场长,怎么就行啦?我现在活着,给人民做不了工作。
我……”老军人连连摇头,他说:“不对,不正确!你为什么不能工作?能!早就有人给你说过了,你忘了吗?”
“有人给我说过?”小海英感到万分奇怪,她瘫痪了之后,只有这次她才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啊。她着急了:“老场长,没有,你没有给我说过。”
“不是我,是一个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是谁?”
“毛主席。”
“呀!”海英的眼睛惊奇地圆睁着,她更加感到迷惑了:“没有呀……”老场长拿起那本写有“老共青团员赠”给小海英的书——一本纪念白求恩大夫的书,问她:“看过了吗?”
“看过啦。毛主席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学习白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可是瘫痪……”“是没有说过瘫痪。你是什么时候看的?”“去年呀,你不是去年送给我的吗?”“那么你这次病了,没有看吗?”小海英有点不好意思了,她说:“我……没有看这本。”“这就难怪你要哭鼻子喽。海英,毛主席的话你要常常记在心里,学一遍不够,要两遍、三遍……每学一遍就有一遍的好处。你来看,他在这篇文章里,不是早就给你说了吗?……”老场长在书里翻出一页,这里,有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志的文章:《纪念白求恩》,文章的最后一段写着: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小海英看完这段话,惊喜地抱着书,眼睛充满了希望,好像从一个黑洞洞的房子里看见外面多么美丽的阳光。
老场长读完这段话之后,解释说:“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当然要为人民工作,要尽自己的能力做。不过,人的工作能力是有大有小的,秤锤也有大有小……”他讲起她参军时说的“秤锤虽小压千斤”这件有趣的事情,使整个病室活跃起来。后来他通俗地解释这个道理:“无论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有多大,还是有多小,尽了能力才是衡量的标准。比方说,有个能力很大的人,他在工作中,尽了自己的能力;你,也尽了自己的能力,那么在‘尽能力’这把秤子上,他是一斤,你也就是十两,一样的。你不要以为不能做什么工作,给人讲个故事也可以算工作的。我就常常做这件工作。”
“原来是,给人讲讲故事也可以算工作吗?”小海英更加有希望了。
“对,讲个故事也算工作。我给你们讲过一些故事,让你们知道怎样做个高尚的人,这就算我做了工作……”
老场长继续说了很多。他的说话很简单,很明确,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他的意思。
小海英活跃起来——说真的,她已经是想笑了。“那么,我还是可以做工作的。”老场长笑眯眯地点着头:“这才是对的。你可以做很多工作,永远也做不完。”
小海英快乐极了,多少天来的忧愁一扫而光,完全流露出她在没有病以前的性格,拍着手笑哈哈说:“好哇,我原来三天三夜是白想啦,残废了也不怕……”
“不怕,不怕……”那个当了一辈子外科医生的老院长,一辈子也没有治过这样的小姑娘——明明瘫痪了,她还说“不怕”,那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人生态度啊!可是一个医生跟他的病人说“残废了也不怕”,那还像话吗?她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好姑娘,做医生的人更加不能给她说句话。他连忙改口说:“不怕,治病也要像你可以工作那样——充满希望。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残废残废的呢?还有我们这些穿白褂子的人嘛。嗳,哎哎……你也听我说两句,”他像对谁宣誓那样,将右手举得老高,慨然地说:“我们一定要治好你的腿,治好!懂吗?”
“能治好吗?”很多人一齐问道。
“能治,能治好,一定……能治好!”
这么一说,哗然地响起了欢呼,接着就一片噼哩啪啦的掌声。只有外科主任惶恐地看着院长,心里想,这老头儿今天别是太激动了吧?感情是感情,医学是医学。医学要是和感情搅在一块,就跟灰锰氧和甘油搅在一块那样。结果是……会吹破的。
回到医生办公室以后,外科主任抱怨起来了:“院长,你刚才是说些安慰她的话吧?”
院长在办公室里大步地踱来踱去,他确实为自己的诺言感到焦虑,说话变得很不连贯,“什么安慰……怎么,你认为不行吗?……也许,能行吧?……”
“能不能医好,得研究一下才行。这么多人,传出去可不是好玩的。”
院长虽然也有些信心不足,但是他毅然地说:“就是要设法医好她嘛!能力有大小,医术也有高有低,我们得尽力,尽力!”他劝告外科主任:“我们要求她对治病充满希望,我们对治人家的病也应该充满希望。往好处想!”
“当然……可是希望是一回事。”外科主任迟疑地说,“能不能医好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后来争论焦点,逐渐移到一个专门的问题上。院长说:“我认为,要趁她瘫痪不久——病变暂时控制住之后,就让她锻炼腿部,最好是扶着拐杖学走路。否则将来关节硬化,那就不好办了。”
“这当然对。可是,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她受得了吗?”外科主任知道,她的膝盖关节稍为触动一下都会引起剧痛,更不要说走路了,除非经过长时间的治疗以后,疼痛才会减轻。可是到那时候,谁能保证不会因为病变而使她的两条腿完全不会弯曲,变得僵硬起来呢。那就是说,完全残废了。
“是呀,是很痛苦的事情。”院长同意了。
“所以我认为没有把握。”
他们为这个问题苦苦思考着。这不能不深思熟虑,因为医生只能从病理上预先知道病人会有一些什么痛苦,但不能亲身体会到这种痛苦。而各种各样的病人,对于痛苦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忍受程度,即使最能克制的人,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因为剧痛而发生休克。何况他们的治疗对象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这是远不能和虎背熊腰的壮汉相比。因此院长的方步踱得越来越慢,最后停下来了。这就说,他也感到问题很棘手了。
“院长,我看给他们场长说明一下吧,刚才是安慰病人的话……”“等等,等等……”院长侧起耳朵,仔细听着,“你听,他们那个场长在说什么?”
病室里,老场长爽朗愉快的声音:“……你要记住,病嘛,对什么人都是个考验:对腰圆膀粗的赵大个子是考验,对瘦瘦小小的刘海英也是考验;对英雄保尔是考验,对你也是考验。你要经得起考验……”
“就是说,不要怕吗?”
“不要怕,对,对,不怕!”
“连死都不怕!”
“干什么要说死?要活,好好地活!喏,身体病了,思想不要病;身体痛苦,精神要快乐。医生说怎么治就听从怎么治,争取早日治好出院。”
“老场长,我明白啦,身上痛,精神要不痛!”
“不,不对,要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