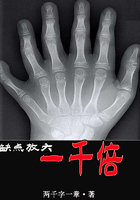1
一个忽然变得有意思也有某种意味的夜晚。不是因为厂庆。
这天是厂庆,二十五周年大庆。日子是假设的——25年不会错,他二十五岁那年办企业。前店后厂,楼上住人。开初男女共用一个马桶;夏天也没错,开业那天他站在门口,给来宾每人发一包烟一根冰棍。现在是几个亿的明星企业了,领导也说应该有个创业纪念日,到时候热闹热闹。江龙想,就选他的生日吧:8月15日。和生日一起,不会忘,也省事。
这天是他五十岁生日。
忙了半个月。他十分尽力,过了这一天,就是“年过半百”;二十五周年也是整数,不能不重视。无非为日后的发展铺垫,一个交情的契机,一个个部局宴请。他必须亲自出席,不然便是怠慢,骄傲,反而坏事。不会喝酒在宴席上唯有尴尬和乏味,掏钱还得不停地告饶,连连得罪。一晚一宴,夜夜呕吐。
终成正果。今天,方方面面的领导都来,虽然多的是副职也已给足面子。讲话都很得体,三言两语。酒席摆了一百桌,来宾和全体员工参加。餐后,工龄十五年以上的20位元老开赴雁荡山,“豪华休闲度假”三天。
故事发生在度假的第一个晚上。
当鸟笼打开,笼里的鸟总是要愣一愣,飞出去了也是绕着弯不知所去。天空太大了,太大的天空让鸟们心慌意乱。元老们也是,管束惯了,拿着钥匙一进房间,就打电话或敲门来问:“江董,晚上干什么呀?”
江龙只得把众人召集起来,说:“从今晚开始,到十八日下午五点大厅集合上车,这三天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高高兴兴玩去。包吃包喝,好玩的项目任选,全报销。对了,派出所开的罚单不能报。还有条纪律,不能偷偷溜回家,度假得有个度假的样子。”
大家反响不热烈。
四星级宾馆,一人一间房,不分经理、工人,一律平等。与国际接轨,倡导快乐企业。
回到房间,江龙疲惫不堪。深深吸口气,接着重重叹口气。闭眼坐在沙发上。
一切都圆满——圆满那么重要吗?他突然感到无聊,沮丧。
儿子从英国来电话。他精神了一下,儿子记得他生日。
“我谈了女朋友,纯种英国人。”儿子开门见山,透着自豪。
“你才多大呀?”儿子刚满二十岁。
“她眼睛是蓝的,个子比我还高。”
也许不是坏事。儿子在英国读了三年私人中学,他和阿芳去伯明翰看望他,逛商场还听不懂售货员在讲什么。整天和国内去的同学一起玩,会广东话了,会上海话了——去英国留的什么学!找个蓝眼睛,至少可以学学英语。
“她也学室内装潢?”
“不是。我们是在餐馆洗碗认识的。她家是工人阶级。”
儿子撒谎不打草稿。一年给他四十万,还有半年时间在国内(搞不清英国学校怎么假期这么长这么多),他什么时候打工了?还胡诌什么工人阶级,工党倒差不多!
“我和她同居了,要租房子。她会拿筷子吃饭。老爸,支持一下吧!”儿子直奔主题:要钱。
不该送他去英国。那时周围的朋友都送孩子出国留学,去英国德国体面,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掉价。他想让独生子接班,读工商管理,儿子却自作主张报室内装饰。好了,第一学期就有了蓝眼睛的室内装饰!
通话期间,手机短信提示,有沈阳客户来电:机器安装出问题。
“你们吹什么‘快乐顾客’,我们都成快死顾客了!”沈阳客户一点不讲情面。
“马上就去人——明天就去!”
这是大订单客户,得罪不起。明天放假,到哪里找人?
儿子毕业,说不定抱个中外合资的孙子回来。
儿子没有提起他的生日。儿女就是这么回事。
营销部王经理手机关机。他累糊涂了,王经理不正在身边度假吗?
305室,没人。307室,没人。309室敲开门了,生产部经理已躺在床上。江龙说,睡吧,好好休息。他知道,要是让他明天一早飞沈阳,他会立即打电话订机票。他觉得已休息够了。经过棋牌室,烟雾,人声牌声。两桌人,攻城掠地正凶。坐的站的十几人,见董事长来了,大声招呼,让座。
从棋牌室里出来,心里不是滋味。企业出钱,只不过让他们打麻将换个地方!
一个大包厢有人唱歌。难听,走调,又声嘶力竭。江龙轻轻推门,两位老员工,两位小姐。小姐在劝酒。喝酒她有提成,客人也乐意:“女人不喝醉,男人没机会。”江龙除了陪领导和大客户,从来不去KTV;这几年领导流行上体育馆、游泳池了,打高尔夫,桑拿按摩,他买单。他不打牌,年轻时喜欢运动,现在当买单角色倒了胃口。
“江董,来来来!”
在唱歌的元老看见他来了,热情不堪地跑过来,拽他的胳膊。似乎认识董事长在小姐面前很有面子。江龙不得不坐下来。
“江董,给你叫小姐?”
这位平日低眉顺眼的装卸工,十几年和他没有说过几句话,为年终困难补助,江龙给个红包便千恩万谢倒退着出门。他兴奋过度了。他握酒杯的手又黑又粗,青筋毕露,指甲缝发黑,身旁的小姐白白嫩嫩,很多情的样子。
“我还有事。我喝一口。”
幸好手机响了。
“你们玩,我先走。”
另一位在场的是财务部副经理,不说话,眼角瞄着江龙。小姐的手放在他的大腿上。
“我们董事长非常忙,市长见他都得约时间……”装配工向小姐煞有介事地说。
“你好啊,谁陪你度假呀?”小祝的声音又响又清晰。
“企业二十五周年大庆……”
“知道,知道。我找你,几号房间?”
“别来,大家都在……”
小祝手机关了。再打过去,关机。再打过去是告诉她几号房间,免得她满宾馆找:“我们约好的。”她不管不顾,想什么就干,温州人说的“单个脑”。这种性格过去可爱,现在可怖。
这时候,简直恐怖!
王经理笃定上街找小姐按摩了。刚才车子路过看到一长排按摩店,门口坐着穿超短裙的按摩女。江龙下楼告诉总台,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找他请她去301。服务员点点头没问什么。
小祝还是关机。她喜欢玩失踪,玩意外。也许她是闹着玩,吓唬吓唬他。等人时间最长,最烦。下楼问服务台有没有人找他——明知故问。在大厅坐了一会儿,注视大厅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的月光,慢慢移动。
厂庆热闹。生日冷清。
她不会来了。她是个急性子。
江龙出大门沿着小溪随意走走。空气清新,溪水潺潺。看到大山,看到山泉,觉得生活中除了厂庆,等人,还有这么大的天地。一个人很渺小,一个人的厌烦更渺小,微不足道。
山月在大厅里看和在山野看,也不一样。
江龙在柳树下的一块苍迹斑斑的花岗石上坐下。
五十年前、二十五年前的月亮和今天一样的吧?可是五十年前的今天他哇哇落地,浑然不觉;二十五年前手上是洗不净的油污,吃饭端过的碗指纹也洗不净。再过五十年,山月还会是这个样子,时圆时缺,出山落山,他在哪里呢?企业还在吗?
这时的他,迷惑中有恬淡,心慌慌的,却感到清净。
瞿瞿,瞿瞿。突然听到蟋蟀叫声。他吃一惊,久违了!
(也许,这些年他常常听见,只是忽略罢了。)
2
这一天没有结束。
坐在花岗岩石墩上,江龙非常想念(平日不大想)死去的哥哥。人死了,再也见不着了,连说声对不起都没有机会了。全是蟋蟀的叫声惹起的。生日,厂庆,蟋蟀。
童年,家住山根。捉蟋蟀,斗蟋蟀,是童年玩乐。几只萤火虫放在瓶子里,萤火虫的腹尖上有一点亮,幽幽的,泛着蓝,闪着绿。无烟无热,无躁无声,提着小灯笼似的漂游。一个小瓶子,几只萤火虫,便是一个照明的灯泡。逮萤火虫不难,草上飞的,捉蟋蟀不容易,石下藏的。不过,他和哥哥乐此不疲。
哥哥大他两岁。年岁相差太少的兄弟不和睦,谁也不服谁。打架,爸妈不必分是非就骂哥哥:“你大,你大就是你不对!”哥哥不服,便暗地里使坏,把江龙的书本弄脏了,把他的铅笔藏起来,让父母骂他。他知道是哥哥搞鬼,苦于没证据,便恨他。不过捉蟋蟀是两人的同好,吃晚饭时哥哥一个眼色,他点点头,什么都明白了。从后门溜出去,人手一个萤虫瓶,一起上山,在草丛,岩隙,石缝,坟坦,寻寻觅觅;有时也去废墟,断壁颓垣、残砖旧瓦堆里,蟋蟀虽小,颜色虽灰,但好抓。哥哥听蟋蟀叫声判断方位不如他准确,又赌气。
三十年前,兄弟俩合伙开店。做生意没有不争吵的,这时候爸妈总是怪罪他了:“你是弟弟,你要听哥哥的。”只得选择分开,分资产时两人差点动手了,只为区区几百元。二十五年前哥哥去了山西,办煤矿。不到5年便无音讯。矿难?绑架撕票?自杀被杀?他派人调查,自己也去过。活未见人,死未见尸。
这是江龙心中挥之不去的疼。念哥哥的好处了,哥哥在外面总护着他,哥哥帮他做作业,哥哥一句一句教他唱歌……那是清爽的童稚时光。当初就是让哥哥当董事长,又有什么?人生怎么不能从头再起?
群山见过太多的人间沧桑,默默无语。
他坐不住了。不能这样坐下去了。看手机,没有未接电话。小祝到底来不来?
瞿瞿,瞿瞿。蟋蟀一直在叫,在召唤他。
他站起来,循声寻去。四十年前的童真童趣的诱惑突兀出现:捉蟋蟀!
路灯明亮。在河岸下方。下河岸。
江龙发觉自己笨手笨脚。右脚下探,够不着石缝,换成左脚,转过身,肚子碍事,艰难地往下滑溜,踩空。河岸2米高。跳吧,河滩布满卵石。决定不冒险,匍匐着,上来了。这身意大利名牌杰尼亚西服上土迹草痕斑斑。
懒人挑重担,聪明人走远路。走十多米,从台阶下来安全轻松多了。弓着腰,屏声息气,蹑手蹑脚,这陌生了的感觉太美妙了。蟋蟀叫——前进,噤声——驻步。索性蹲下来,双手扶地。忽然发觉,瞿瞿声在河岸上方。一抬头,小祝正坐在他刚才坐过的花岗岩石墩上,裙子掖在两腿间,冲着他坏笑。
“手表丢了还是鞋丢了?”小祝故作关切,做鬼脸。
“丢人了。”江龙笑着回答。她终于来了。他一副狼狈相。
“差不多,够丢人的。你还以为不丢人哪!”
现在,敢这样跟他斗嘴逗趣的人还真难找。他也只允许她,她是“单个脑”。江龙上台阶。
手机响了。刘副市长号码。
“江董,你在雁荡山也不说一声。我陪上面来的人,听总台说才知道你在。去你房间了,没人。在哪里潇洒呀?”
“我正骂你呢!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我们小百姓请不动你了。”江龙说着对领导惯常的话,开玩笑表示亲热无间。刘副市长原先是镇党委书记,前些年企业招待客人,时不时拉上他,他有空准来。
“岂敢,岂敢。当官哪有你自在!不说别的,每年陪上面来人至少来雁荡三四十次,过年过节更来得勤,领导拖儿带女一大帮,名义是考察,节假日也不休息,其实,我们才是加班加点勤勤恳恳……怎么样,我去你房间?几时回来?”
“马上,马上。”江龙不假思索地说。他这样轻易放弃小祝,自己也奇怪。人到五十,对女人失去兴趣;对女人失去兴趣,人生逊色一半。小祝有点像刘副市长,有时需要,有时烦。
他望一眼身旁的小祝。
小祝回答他的目光说:“明白。”
小祝19岁来江龙企业。聪明乖巧,活泼可人。江龙把她从车间调到办公室,后来是生活秘书。一次到春城昆明参加订货会,不知道是真醉还是佯醉,是他醉还是她醉,反正有了一夜情。早晨醒来他很后悔;这种事后悔无用。她说:我愿意。回温州他给一笔钱让她自立开店,卖女人内衣内裤。不久有了第二次。第一次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是努力与害羞、害怕作斗争,耸肩弓腰,第二次像三级片里的小姐哇哇乱叫,分明作假他感到扫兴,从此不再有这种事。她也无所谓,爱打电话聊天,没事(基本上没事)也喜欢找他,如同任性娇惯的小妹妹,而他成了古板的老大哥。
“明白什么呀?明白我应该接待你,还是接待刘市长?”
“同时。最好介绍一下……”小祝的心态和他不同,“你别担心,我不缠你。别忘了,雁荡山是国有资源,全民所有。我回去了,再见!”
一甩手袋,摇摇手,小祝说走就走。
江龙厌烦和领导打交道,没话。没话找话最累人;领导恐怕更累,有时他很同情领导。
刘副市长坐了半小时。
江龙不由自主(都是休闲休出来的毛病),又给小祝电话。
“到哪里了?”
“上高速——早就上高速了。怎么,想我了?”
“关心一下。开车小心点。”
“谢谢,感动死了。要我回国有资源吗?”
“你不是想来就来吗?”
“雁荡山不想我,你想不想?”
“开车小心点。”他把手机关了。
感到神不守舍。良辰美景,坐在房间里有点冤。才十点半,平常不到十二点不上床。又踱步出去,门口站了站,深呼吸,伸懒腰,摇摇脑袋转转髋——这要不了几分钟。
去河岸吧,小祝来过的地方。她真的在身边,没什么;不在,倒有余香余韵,有点想她。思念比在身边有味道。思念没有负担,不必照应对方的感觉,完全是一个自己。
瞿瞿……
捉住这只让他出丑让他回不去童年的蟋蟀,成了他的心结。它竟敢向他挑衅!凭着执著,不达目标不罢休的这股气,才成就了他今天的企业;五十岁生日,二十五周年纪念日,这个好日子不能被一只蟋蟀欺侮。从前他一晚上能捉好几只!不就方圆十米的地方嘛!掘地三尺也不难。
蹲着太吃力了。双膝着地,一步一步往前挪。有动静蟋蟀就不叫,好一会儿感到安全了才出声。目标在左前方。他发觉自己在爬行。爬行就爬行。大腹便便、微秃、西装革履的人独自爬行。小心扒开草丛,挪动石块……
“啊!”小祝站在他身后,喊了一声。
意外地高兴。意外才高兴(本来依稀希望回去在大厅见到她)。站起来,拍拍手上、膝盖上的泥污。
“怎么又来了?”
“担心你的安全啊!干什么,练瑜伽?”
“捉蛐蛐。”
“蛐蛐,什么蛐蛐?”
“会叫会跳,还会咬。”
两人扒草丛挪石块瞎忙乎了一阵。蟋蟀经她一吓不做声了。一无所获。他发觉她随和,体贴,善解人意。
“这么晚了,还回去吗?”
“明白。”
明白什么呀?他给她暗示了吗?
小祝没有离开国有资源。第三夜表现得体,有兴奋有感觉,没有大叫大喊。
“一个人在生活中要不断总结经验。”在枕头上,江龙想起北大EMBA班上老师讲的一句话——十足废话。会心地笑了笑。
他得出的结论:不应该再与她同床共枕了。她至今未婚,大概也没有男朋友。这样不好,非常不好。他做得到。
(没有想到阿芳。两口子有默契,彼此不干涉,她玩她的麻将。以前互相干涉,二十多年的婚姻已足够让各自认清、习惯和接受现实。)
3
天刚亮,江龙就把她推醒。她裸着身体走向浴室。江龙看着她的背影很享受,比昨天夜里还享受。女人一生孩子,腰就粗了,背上的肉就起堆了。他想。
送她出来,在大厅门口遇见晨练的王经理。
“董事长早。”一身运动衣衫的王经理不带含义地问候。
“昨晚上没有找着你。沈阳那个厂安装有问题,今天要派人去。你安排一下。”江龙眼睛不看小祝,小祝径直去停车场。
“明白。”
江龙愣了愣。怎么也说明白。明白什么?
王经理无视小祝。其实他们认识。他们应该彼此打个招呼的。心里没鬼就应该打招呼——心里有鬼!
“这种型号,传送设计有问题。洛阳那边也出过事。”
“今天一定去人。”
“你放心。”
江龙看表,五点。这个王经理怎么五点就起来跑步!找一晚都不见人,偏偏在不该碰上的时候碰上了。(他有点羡慕王经理的健康生活方式。)
回到房间,睡不着了。
小祝打过电话。
“王经理走了吗?……你怎么向他解释?”
“你说呢?”
“不管,睡个回笼觉。昨天夜里你太累了。晚上我还来吗?……别怕,吓唬吓唬你,这样已经太感谢了。”
江龙又接不上话。不会再有第四次的——坚决!绝对!
他看过一本书(也许是文章),里面有句话(其他的话都忘了,题目也忘了):幸福男人的美满人生要有三个女人——妻子,传宗接代,操持家务;年轻漂亮的情人,享受性快乐。第三个是“红颜知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理解,支持。江龙想,红颜知己算了,那是文人、知识分子的事。生意场上不分男女,赚钱就是了,简单得很。多愁善感,自作多情,只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