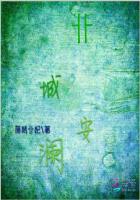我早已修炼成嫉恶无仇,对假话宽容,对虚伪麻木,这是时代需要的生存基本功。但我还是吃了一惊,装聋这么久,这么像,这么彻底,他怎么会做到?只为换工种,他怎么做得出来?
“要干大事,没有这个能耐还行!”
“对老婆孩子也这样?”丁三三问。
“这还用说。我老婆缺心眼,对她一句真话也不能讲。”
“你,你是怎么对他们解释自己是这个?”丁三三天真,她感到不可思议,指指耳朵。
“车上抓小偷,挨小偷一拳,打在耳朵上。从此,聋了。小偷也跑了。”
我觉得,他的“工人阶级”(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但那时混为一谈)形象,就在这一天彻底破灭的。公然作假,手段卑劣,恬不知耻,自鸣得意……无话可说了。造反,是听毛主席号令,听党的话,他承担不了责任,他的一些作为,狂妄无知,也可以从受教育程度差,缺乏教养,从个人性格和修养来解释,我可以喜欢或不喜欢,甚至他对李丹,李丹有女人魅力,我不是也曾心荡神漾吗?区别只是做了或差一点做了,也可谅解。这件事,却是做人基本原则,职业道德,没有人强迫他或指令他。
“医院你有熟人吗?”他问。
“没有。”我断然拒绝。
“不要紧,医院造反派有我认识的。”
那天傍晚,他又来了。递给我一张处方笺,上写检查结果:“传导性耳聋。”医生建议:“休息半个月。换工种。”盖着红印。
他做到了。
他很得意。我觉得他特地过来是向我证明,我依旧是保守派。
我唯一能做的:不留他吃饭。
14
诸葛春兰来过两封信。
第一封信我没有保留。我是避嫌,或者说是心虚。我暗恋着她。有一天李丹对我说,当诸葛春兰知道丁三三才是小学毕业,她“啊”的失声,泪水盈眶失态,整整一天不言不语呆坐。教师家庭出身,使她看重学历觉得不配我,哪怕在“读书无用”、有知识者卑贱的那个年代。她也是暗恋我的——席雄告诉李丹。我不能回信。
她在信中说,她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和睦的家庭。当初看上席雄是又会劳动又会写作,是我的学生和我器重的人,她才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结婚。可是现在他不劳动不写作,天天和一伙图谋不轨、居心不良的人一起,喝酒,吹牛,今天要打倒这个,明天要斗臭那个。她不能说话,一说话就是挨骂挨打。她让我劝劝他,她相信我的话他会听进去。这封信她让我不要告诉席雄。他扬言她要是向我告状,就打断她的腿。
春兰不明白,我是“臭老九”,他是领导阶级;我“跟不上”,他是“紧跟”。我只在为她难受,为她担心,为她祈福。
第二封信我至今留着。也许是一种预感。我全文抄录,权作缅怀吧!
叶老师:
你好吗?
前天席雄从你家里回来——我可以想象,你会有一个非常温馨温暖的家——他一进门就手舞足蹈,喊:“成功了!成功了!”孩子吓得躲在我身后,我也呆住了。一个多月,他听不见,不说话。我们都被他骗了,他骗了所有的人。我说了句“卑鄙”,他重重扇了我一个耳光,并且威胁我和孩子,说出去就杀了我们。孩子才5岁,他怎么能这样对孩子说话!
昨天他到厂里办了休病假手续,晚上便去北京。
他大概没有对你说,他写了个“京剧样板戏”,剧名《矿山尖兵》。剧本是我誊抄的。斗走资派和总工,一点也不合情理。错别字多,有些语句也不通。我才明白你过去为他花费多少心血。他“听得见”了,他要送剧本到北京交给江青同志,他说这是第9个样板戏。我别的不敢说,只是劝他先请你看一下,他说你看几千字的小作品行,这样大作品你思想水平和艺术功力都够不上。我没有办法。
他已不是从前你要培养的席雄了。剧本写得好不好不要紧,我早就不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现在是他的人品,而这次装聋作哑更是让人不齿。这样下去太可怕了。这个家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只希望你和来过我们家的李丹编辑,能拉他一把,让他清醒一下。
现在是夜里一点钟。席雄走了,孩子睡了,很安静。太安静了。白天听孩子的笑声,夜晚看孩子的安详睡态,这便是我的全部幸福。
这时刻,我特别想念你!我和你六年没见面了。我去过一封信,你没回信,我不怨你。趁着夜深人静赋予我的勇气——明天就不会有了——我要说,我一直盼着再见到你。我期待这一天。期盼这一天的到来,是我生活中的阳光。
你不要介意,我只是在说实话,在说梦话。说出来,我会轻松一些。
今生今世我是他的人,我不怀二心。我向你保证。来生来世,我会选择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啊,我终于说了!
我真想找你去。干校的田埂,大槐树下……
春兰
我没有回信。不能回信。想过要约她来的。只是想想。有太多的理由不能和她见面。
如果她来了呢?
哪怕让席雄知道,春兰心有所属,她不可能与邻居电工有私情,他会杀她吗?
15
李丹约我下班后在办公室等她。
她受席雄之托,借希特勒《我的奋斗》。席雄说是灰色封面的内部书。
我惊诧莫名。
“你们怎么还来往?”我以不习惯的口气质问。他奸污了她,她说过席雄毁了她一生。
让她借这本书,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那就算了。你别理他。”
她脸上有一丝尴尬,带几分苍老的可怜。她不能自圆其说。
她和席雄在小树林里的经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连暗示都没有。不过大概很多人都有风闻,本来这种事瞒不住人。她的美丽、孤芳自赏、骄矜和“政治进取心”使传闻更有附加价值和刺激。我怀疑是席雄自己散布的,“我把漂亮的女编辑都干了”,他会这样说。
那么,她怎么离不开他?是情,是欲?情是战友情,革命情;欲是男女之大欲,有过性经验的三十女人的生理欲求。抑或两样全有。
也许可以理解,谁都有可能。
“听说他写了个剧本?”
“江青同志没有回信。他怀疑是中南海门卫没有转上去。你别管他的事,狂妄,没有自知之明。”
那么,至少是欲要多一点,或者兼有旧情。
不久,一个二十世纪和平年代的大闹剧、大悲剧终于历时10年收场了。如此荒唐,如此可悲,文化的污点,民族的耻辱。
我们都沉醉在欢乐和兴奋之中。一切都还来不及思考和检点。
那年春节,可以凭票每人买一斤水果糖,半斤花生米,一斤猪肉,三两带鱼。春节不再“革命化”,我们第一回享受三天假期。
年饭吃过,我去报社,看一下春节的版面大样。11点要赶回家,和三三过除夕守岁。
在报社门口,看见李丹站在当年春兰站过的大槐树下。槐树枝桠光秃,在寒风和彩灯光影中尽情地摇晃。性急的人已经在零零星星地放鞭炮,憋了十多年了,有这一天了。
李丹迎我走来。
“你好。过年好!”她的语调带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过年好。你去哪里?”
“去报社看看。”她望我一眼,决定说实话,“我等你。我知道你在办公室。”
“有急事?”
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像是冻苹果,笑容发僵。白羊绒大围巾下的发梢结着霜花。
“我等你几个小时,站在树下。……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零下20多度的严寒,除夕夜在室外等几个小时。她轻松的口吻不合温度不合时宜。
“第一个问题……”我回应她的轻松,但立即感到残忍。我不能这样嘲弄般带着优越感说话。“我们去传达室吧?你很冷。”
“不,不冷。我在想,刚才一直在想,星星为什么是美丽的?”
“你怎么知道是美丽的?”我反问,拉她去传达室。她不走。“现在是寒星点点,第二个问题……”
她仰着脸,两只大眼睛望着我,眼里含着泪光。
“你说,我该怎么办?从前我听党的,现在,我听谁的?我还能听谁的?我怎么办?”
鞭炮声大作。焰火一时一时照亮天空。
这个问题太严肃,太沉重。但我又觉得,眼前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色彩,不就是答案吗?
“现在,听我的:到我家过年。三三会欢迎你的。”
在只有小孩快乐地三三两两跑来跑去的街道上,我握了握她戴着厚厚毛手套的手。
她点点头。跟着我走,她对我从来没有这样顺从过。我有点感动。
16
李丹调记者部了。她十分满意。
那天中午,她从矿区采访回来,气急败坏地跑到我家。我正在吃饭,她把我叫到门口。
“席雄杀人了!”
我吃了一惊:“杀谁了?怎么回事?”
“把春兰杀了。”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脑子一片空白。生命是什么?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春兰没有了,怎么天空、大地、眼前的一切依旧?
“不可能,不可能。谁告诉你?”
“他父亲,席雄父亲。昨天夜里的事。”
“他父亲人呢?”
“在我法院朋友家。”
三三端着饭碗出来,招呼李丹进来吃饭。
我们顾不上理会她。李丹只是向她点点头。
“我去见他。你带我去。马上去行吗?”
“当然。走吧!”
李丹把挎包放在我家。我们急忙向汽车站赶去。一路上我不说话。我不相信,但愿是梦,恶梦,恶梦有的时候像是真实的。恶梦会醒来的。坐上车,我依然感到是一场恶梦。恶梦到了山穷水尽不能解脱的时候,比如站在悬崖上下不来,鹰在脚下盘旋,上下左右全是绝壁,我会告诉自己:“不做了,不梦下去了,醒来吧!”我现在就这样对自己说。
李丹的法院朋友很真实的存在。我见过。十多年前,他来办公室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只得在电话机旁的位置上读席雄的《铁将军》和他的充满豪情和阶级感情的来信。……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他也和席雄有缘——他不会知道。
当年他英俊,一脸逢迎讨好,屁股很重不愿离开。当年李丹美丽的脸庞冷若冰霜,爱理不理。现在,他成熟了,举止得体,说过话后再补一个笑脸,而她却是亲热,活泼,套近乎。两个人的脸孔,都已写满沧桑。
我和李丹一进门,席雄的父亲就“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地喊,双膝扑通下跪。(我想起十多年席雄进编辑部办公室的情景。)
半个小时,惨案的经过勾勒出来了。
昨天晚上,席雄家的灯泡坏了。春兰在黑房间里等他回来吃饭。等到十点多,她没吃上饭,打着手电找邻居家。邻居是矿上的电工,平日家里的小事相互帮忙,席雄在家他间或端过茶杯过来下盘棋。电工爱开玩笑,规劝席雄:“晚上早点回家,有这么漂亮的妻子,你放心得下?”对这些打趣,她从来不搭理,她独自在家,电工也从来不串门。换灯泡,他站在椅子上够不着,椅子上又加个小凳,春兰打着手电扶着小凳。这时席雄推门进屋。春兰一慌神,手电熄了,而同时灯亮了。一黑一亮,眼见为实。春兰正扶着他的腿。席雄一言不发,电工觉得有点不对头,用玩笑来开释却非常不合时宜:“这好,让你抓个正着。”谁也没笑。他讪讪告辞。春兰急忙说:“吃了吗?快吃饭。”他还是坐着不说话,一股酒气。春兰说:“到床上躺一会儿吧!”他起身往伙房去,她知道少不了一顿毒打,以为他要去拿捅炉子的铁钎,拉住他哭着说:“你听我说……”席雄顺手抄起菜刀,举刀就砍,她肩上挨了一刀,又在她脖子上砍了两刀。春兰倒在血泊里了,他蹲在地上,揪住头发割下头颅。他一身是血,打开门,提着她的头站在门口。血往下滴,他喊:“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我把老婆杀了,你们报警去!我把老婆杀了,把头割下来了!”他一直站在门口,又喊又笑。警车来了,他对公安人员说:“怎么才来!我杀的,大丈夫今天才出了口恶气!”他提着头颅自己跳上车(卡车)。双手是血。春兰头发上的血已经凝固,一绺一绺的。眼睛半闭。
席雄的父亲的河南口音,像他儿子。
十多年前,在席雄滴水成冰的“书房”里,我见过他。他端来一大盘炒鸡蛋,没说话。
“春兰真的和那个人偷情?”李丹男朋友对这问题有兴趣。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他说。
“不可能。”李丹说。
李丹男朋友似乎不高兴我来,不用正眼看我。
他真的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胃里在翻腾,心里很堵,闻到春兰的血腥味,嘴里也是血腥味。我眼前是站在干校田埂上的她,红头巾在风中飘动。我只有一次握过她的手,手瘦小,温暖,柔和。我要吐了,我说了声“对不起”,跑到院子里扶着树呕吐。这是一棵槐树。
我头顶着槐树站了一会儿。
那么这是现实了!
他们大概在等我进房间。李丹男朋友看见我进来了,才说话:“第一,有自首情节。他站在门口喊着让人报警;第二,喝醉酒,酒后不能自制,有人证明的吧?第三,可能有精神病。患精神病,这最好!就是民间说的武疯子,疯子不能为他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席雄的父亲木讷地坐着,一个劲地点头,流泪,绞着粗壮的手指。“他不是有耳聋病史吗?”李丹男朋友问。
“装的。”李丹断然地说。
“装得像也不容易。送精神病院检查,经得起他们的测试,针刺,电击,一般人根本熬不过去也装不出来。是死是活,就看他的能耐了。”
李丹说:“他抗得住。”
前男朋友转过身问我:“你姓叶吧?李丹经常提起你。精神病院有熟人就好办,能走走路子吗?”
李丹替我回答:“叶编辑认识人多,他会想办法的。”
席雄父亲又要给我下跪。我扶着他。我想说找找看,又不想说,也不想找。
“你老人家保重身子。”我只能这样安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