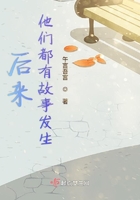3月11日的夜晚,有点春寒料峭,这个平淡的无法平淡的晚上,让我到另一个世界都不能忘记的晚上,开始演绎复杂的无法复杂的情感故事。
“你好!这是县医院的李涵穹。这位是南门小学的老师刘亦菲。”王楠介绍说。在安丘城关镇卫生院中医针灸室,王楠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以后结合在一起的她。“你们先自己聊吧,我还有事先出去趟。”
她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椅子上。拘谨的彼此没有话说。
我抬眼看了看她,这是我正式见面的第一个女人。个头中等,宽宽的肩膀,宽宽的脸盘,宽宽的嘴巴,高高的额骨,大大的眼睛,如果是一个男的,肯定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有点发白,细腻中带着粗糙,有点苍老。肩上披着一块编织而成的柔软漂亮的淡雅印花披肩。
那个人看了看我。瘦瘦的棱角分明的略长的脸盘,带着镇定与刚毅、精明与机灵,大大的眼睛神采飞扬,衣服虽破但很整洁,裤子一角卷起像冬天里躲在灶旁取暖被炉火烘烤带着点焦黄色的卷毛狗。
“喝水吗?”我站起来给她倒水。
“谢谢!”她莞尔一笑。
“你在学校里教什么课啊?”我倒水给她,打破了尴尬。
“我教数学、音乐、劳动课。你呢?王楠说你在医院,干什么工作?”她问。
“我是去年从山东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医务科干医院管理。你是哪里毕业的?”就像开闸的渠水,我们打开了话题。
“我是安丘师范学校历史专业的。”她说。
“历史专业的教数学啊?你哪一年毕业的?”我问。
“去年毕业的。”她说。
“师范学校怎么才去年毕业呢?”我禁不住问。我知道那是一所初中中专学校。
“我原来是代课老师。小学五年级毕业后就去当了代课老师,国家规定到了一定工龄后可以报考师范学校,我就在1989年考了安丘师范。”她款款地回答。
夜风微冷,大街上烧烤店仍然红火,影院正在火暴地播放着《秋菊打官司》,我送她回学校后,在大街上独自走着,一阵凉风灌来,我禁不住缩了缩脖子,耸了耸肩膀,头有点晕,稍微清醒了点。她给我什么感觉呢?没有什么太好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太好的感觉,倒是感觉还能在一起交流沟通。
单位正在忙着迎接“二级甲等”医院分级管理评审,我白天黑夜加班整理准备各种资料。半月后,我给她打电话请她到“午夜玫瑰”吃饭。幽暗的灯光下,一个青年身穿像是用剪刀有意剪了许多破口的褪了色的牛仔裤,上下左右起劲地摇晃着用萨克斯管吹着悠扬凄美的《回家》。我要了一瓶“张裕”葡萄酒,倒满高脚杯,优雅地翘着小指,轻轻地端起来,示意她也举杯,透过酽酽的淡红色的高脚杯,我模糊地看着第二次见面的这个人,轻轻地抿入一小口酒。她对我的举止显然有点局促,端起的杯子有点晃,微微倾斜,流出来滴到了大方的桌布上,我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巾,叠好,帮她擦拭,她脸色绯红,显得有些慌乱。
那一夜,我们聊了一个年龄的话题。
“我是1968年出生,属猴的。你呢?”我问。
“我……”她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停顿了老一会儿,“我是1967年出生的,但考师范时为了增加工龄,我把身份证年龄改成了1962年。”说着,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我看,我一看,果真是1962年出生,既然她那样说了,我也没多想。没想到,多年后,年龄这不解之谜竟成了我致命的打击之一。
同时,我也知道了她家庭的基本情况,三个弟弟,老大在北京当武警,老二高中毕业在村里当代课老师,老三在潍坊卫校上中专。同时,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告诉了她。
“我母亲当时前夫得肝炎死了,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实在无法生存,才改嫁给我父亲。然后有了我和弟弟。”我幽幽地说。
“那你母亲也真不容易啊。哎,对了,过两天我要回趟家,你和我一起回家见见我父母吧?我们谈一顿子,父母真要不同意,总是不好。”她说。
她父亲是那种典型的农民代表,古铜色的脸,早衰的身体,多年的劳累弯着腰,有气管炎也没耽误猛烈抽烟。我把当时济宁产的一种“心”酒放到地上,没等坐下就被呛得猛烈地咳嗽起来,一阵恶心。我从小对烟就过敏,烟味大了甚至都拉肚子。
“你能不能少吃点(烟)?你看把人家呛得。”她母亲说。
“好!好!不吃了。”她父亲说。
昏暗的灯光下,我坐在炕沿上。她母亲为了看清我,拖了个凳子,和我坐在对面,像审犯人一样看着我,聊着些再寻常不过的鸡毛蒜皮。
“小李,我父母对你印象还行,找时间咱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她说。
“好,那就清明节吧。正好我们老家山上花都开了,我们上山去玩。”我提议。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清明节如烟如梦,家家户户喜气洋洋踏青插柳。小孩子的柳笛吹彻着清新的大街,许多调皮的孩子到降媚山上采一种叫“马虎爪”的酸酸的肉层很厚的野花,回到家吊在天棚上,能存活一个多月,并且开出淡雅的白色的小花。
我和她骑自行车在满村人像观赏耍猴一样回到了故乡。老父亲看着我平生领回家的第一个女人,异常激动,里里外外,手忙脚乱。
“你看你,你怎么摘的韭菜,还带着草,你能不能摘干净点?”母亲对着在地上杀鸡的父亲说。
“我正摘着,你又让我杀鸡,我能摘干净吗?”父亲反驳说。
“你快杀,杀完了去小卖铺拿瓶子香槟,家里净些白酒,人家怎么喝?”母亲边摘着韭菜边吩咐父亲。
“知道了。他们俩上山回来还早,你着啥急?”父亲慢腾腾地用刀割开鸡胃,仔细地清洗着里面的沙子。他已经习惯了母亲的这种颐指气使的方式。
桃花几度夕阳红,又是一年春风绿。我和她漫步徜徉在妩媚多情烂漫的降媚山上,天性活泼的我手持老式“凤凰”牌机械相机,不断调节光圈、焦距、速度,从不同角度给她照相,她有些拘谨的连个姿势都摆起来不自然。只可惜,她宽肩粗腰,不苗条,出不来效果。我心里暗道。
“你站在那里别动,我和你一起照一张。”我把相机放到一个山坡上,摆好,定好时间,调到自拍,迅速跑到她身边。没等她明白过来,我已跑到她身边,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了降嵋山的春天和春天里的我和她。山上的各色野花已经开放,桃树大多未开,正含着羞答答的花骨朵,只有山谷向阳的那几棵像是春天的使者傲然宣布着春天的到来。苦菜、迎春、婆婆丁、野茄子、野棉花柴各自施展靓丽打扮得漂漂亮亮,槐树、杨树、椿树、松树、柳树也绽开黄黄的嫩叶,梨树高雅清洁如梧桐孤鸿寒枝拣尽,杏树媚态百生春心荡漾,风吹树摆,吹落万红无数,飘飘洒洒,似新娘花瓣落雨;山坡上沙土地里那种叫“咬咬狗”的土色小虫子,不停地向沙里扒着自己的圆形的小窝,越向里扒外面的沙子越向里落,慢慢地把自己身子藏住;一条土黄色的大蛇盘成一团,懒洋洋地沐浴着太阳,一切都以降媚山主人的姿态热情奔放地迎接着这两个客人。
我们像孩童时低身用手拔着松散的沙土里的苦菜,一会儿就一大把。
“我们回去吧,这么多苦菜,蘸点甜酱,足够美餐一顿。”我提议道。
“叔,你看怎么样?”吃饭后,趁着她出去,我偷偷地问父亲。
“行啊,你看她,说话很大方,大眼睛,四方脸,不难看,还是个正式户口,吃公家饭的,饭碗有保证。再说他家穷我们也穷,正好门当户对。”父亲说。
风乍起时,竟能吹皱一池春水。回忆过去,对她的感觉竟波澜不惊。苏子感叹“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情”,多年后回首才发现,和她并没有谈恋爱,而是在完成一项使命,一种到了年龄应该完成的使命,就像苦菜到了春天就要开花,你不想开,春天非要让你开,一种为了父亲能见到自己儿子结婚的使命。此时,父亲的胃癌像一块石头压在我胸口,憋得喘不上气来,我真搞不清他还能活几年。父亲为这个大家庭辛苦劳累了一辈子,把一个个抚养成人,结婚生子,而看不到自己的亲生儿子结婚,那是一种什么心情?我突然想到了徐世水的悲剧,那是一种畸形的对父母的孝顺,结果导致那样一场悲剧,留下一个孩子自己怎么成长?我为什么无意中不自觉地又走向了和徐世水同样的路,同样造成了一种与徐世水不同但结局都是悲剧的结果。
或者子灵老爷爷骨子里的东西在我身上流淌着,或者仕昌大爷的梦想和追求让我满怀壮烈,不甘于现状,或者我就是一匹雨中驰骋的奔马,只有奔跑才能获得一种心灵的快感;像一只雨中孤雁,折翅断戟伤痕累累仍艰难飞行。当我遇见她并和她平淡地再平淡不过正常交往的时候,我所在的卫生局的业务科有一个考上了山东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事情让我沉寂湮灭刚刚两年的火花突然如地下的岩浆迸发出来,让我去圆那个大学里未圆的梦。当时,我要报考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但诸多原因最后没考成,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校园。
“小李,听说卫生局的宋春磊考上研究生了,厉害!咱们医院的外科主任周祥德参加医疗队支援坦桑尼亚,英语那么好,考了两次都没考上。你也快准备考吧。年纪轻轻的在个县医院有什么混头。”我的业务科主任孟德云说。
“宋春磊考上研究生?”我真不敢相信,既然他能考上,我肯定也没问题。两年前的梦想使一颗浮躁的心不再沉寂。我的必修课是医学英语,为了考研,我除了学好那些无聊枯燥没有任何规律的医学单词外,还走马灯一样在几个教室来回串,利用业余时间自修大学英语。想一想自己付出的代价,没有风花雪月,没有闲情逸致,只有寂寞孤独,只有书中求玉,还遭受同学们书呆子的冷眼讥讽。大学奋斗几年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我都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然而,孤鸿既然决定了向前飞,它宁愿寂寞沙洲冷也不会像麻雀那样随便栖息。我下决心告别一切应酬,准备下一个目标的冲刺。
1994年5月1日,我正式捧起了英语、政治、卫生统计、流行病、社会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专业书,从中品味着一种寂寞,一种孤独,一种清苦,一种枯燥。
“我准备报考研究生了,你意见如何?”一天晚上,我值班的时候,她来了。白天上班忙,除了日常的医院管理,还要处理医疗纠纷,折腾得焦头烂额,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为了更好地利用晚上时间,我主动顶替别人的行政值班,反正晚上值班没有多少事情,倒是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值班室下面就是停尸房,经常半夜三更鬼哭狼嚎,狐鸣狗叫,却没有耽误我焚香捧书,作一叶之偏舟,沧海之一粟,于心驰神往之间,游离于现实之外。暂且忘却司马感叹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世喧闹,于闹中取静,向着自己心中的那个孤寂追求歪歪斜斜地奔跑着。
“你考吧。我支持你!”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沉思了老长一会儿。这一点,我真是自叹不如,她比我沉稳成熟老练,我则浪漫多情浮躁。
自此,除了上班,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甚至占用上班的时间。她则经常来值班室看我,我静静地看着书,她静静地打着毛衣陪伴我,随着幽幽书香,暂且抛开庸俗尘世的琐碎人生,悠悠于南山东篱之下,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梧桐细雨空阶,点点滴滴,憔悴愁苦,风鬟雾鬓。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
父亲的身体日渐见好,各种体力活亦如以前。按照田医生的建议,最好一年进行一次体检,看身体变化情况。
“叔,我准备和你去趟潍坊,检查检查身体康复情况。”农历七月十五日,我和她回家看父母说:“娘,我去南园摘个冬瓜,咱们和小刘一起包水饺吃。”每年的这一天,我养成了一种冬瓜水饺情节。那宽宽的青青的叶子下长长的藤上,结着大大的长长的滚圆形的冬瓜,上面挂着毛茸茸的白霜,切皮去瓤,味道特别清爽纯正。
“不用检查了,花那个钱干啥?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父亲说。
“你懂啥?总要检查一下恢复情况。下周一我们一起去吧,小刘也去,正好去看看我表哥。”我说。
“没事,恢复很好!不用担心!你看这钡透报告单,胃充盈也很好。”田医生看着红光满面散发着振奋精神的父亲说。
中午,表哥招待我们三人。表哥表嫂是第一次见她,格外客气热情。正在吃饭,表哥的对讲机响了。
“喂,是哪位?是老刘啊。你好!你好!吃饭?今天中午不行啊,我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我舅来了,我要陪他,咱们改天吧。放心!你要的那批石油我明天就给你开调拨单。哎呀,你客气啥!行!行!我找家人去传达室拿。”表哥放下电话,告诉他的大女儿,“玲玲,你和你表叔去传达室拿点东西,你那个伯伯放那的。”
“来,小刘,吃,多吃,吃这大虾!涵穹可是个上进的人,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肯定草(差)不了。”表嫂亲热地为她夹菜。
“来,小刘,我敬你!你喝橘子汁。”表哥端起“五粮液”。表哥此时是潍坊石油公司业务科科长,官不大,但权力很大,很实惠。
“来,舅,我敬你!你这操心大半辈子,眼看涵穹的婚姻大事就要解决了。”表哥端起酒杯敬父亲。
吃完饭,她在客厅看电视。
“涵穹,你过来趟。”表嫂一改刚才的客气。表嫂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表哥老张家是老大。表哥是出名的怕婆子,但怕的有道理,家里人多,二姑夫去世的早,大表兄生性慈忍软弱,自己是老大,把自己的几个兄弟当儿子,甚是溺爱。表嫂如同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性格豪爽,处理事情风风火火,精明干练,热心快肠,雷厉风行。表哥家里人口多,事情杂,就连宪林表爷爷在世的时候,很多棘手的事情处理不了,只要表嫂出面,就能息事宁人。二姑夫抗美援朝冰天雪地得了哮喘,复员后没几年去世了。二姑40多岁拉扯着五个孩子,沐风披雨,几乎没法生存,幸亏她公公宪林表爷爷的帮助,一直劳累到大表哥、二表哥工作结婚。二姑孤寡一人,长夜难眠,在村里王媒婆的撮合下,偷偷地见了一个丧妻多年的老头,那老头也没什么负担,二姑感到也很投机。纸总归包不住火,四邻街舍都知道了,如柳絮满街飞。二表哥知道了,领着弟兄四个到了那老头家里,那老头吓得都尿下了,再也不敢和二姑来往。
二姑趁着赶集去找了几次,那老头只是痛苦流泪。
“她妹子,我不是害怕啊,我是怕给你惹麻烦啊。我看啊,我和你结了婚,儿子们也就不认你了。”
大表哥知道了,屁都不敢放。憋了老长时间,没办法,找到了老父亲。
“二舅啊,你看怎么办啊?我娘想嫁人,他们弟兄几个气势汹汹阻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娘真是嫁了人,他们几个怕是不认这个娘了?”大表哥无可奈何哭丧着脸。
“唉!你让我这做舅的怎么说?那是我亲二姐啊!”父亲叹了一口气,也没拿出主意。但父亲想到了表嫂,把这事情偷偷告诉了她。
“你们这些混蛋?就你们知道搂着老婆孩子舒服?让你老婆先回娘家呆上半年,你们试试什么滋味?咱娘守寡10年了,大好的青春都为你们了,你们翅膀硬了,还不放自己娘寻找自己的幸福,你们这才是些不孝之子。”表嫂在家庭会上大骂一顿,弟兄们耷拉着头,老老实实地挨训。
“老二,是你领着他们四个去的?你再领着他们四个去,赔礼道歉把那老头请来,选个时间,我主持婚礼。不用说咱娘自己找,不然我还要帮着她找呢。”表嫂气势凌厉。
二姑的婚姻终于在表嫂的大力帮助下促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