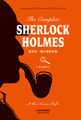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这位大哥,您就吃个火烧吧!”父亲重复地端着糊辣汤重复地卖着火烧。
快下集了,上店的人逐渐多起来。
老板姓张。他肩头上搭块油光光的毛巾,不断地招呼着客人。
“呀,老兄啊,敢情是发财了,不愿到我这小店里了。”
“哪说的,出了个远门,这不刚回来。”
“快坐!快坐!小李,快给李老板端碗糊辣汤暖暖身子。先吃个火烧垫垫饥,5块钱一个。”张老板说。5块钱在当时是指国民党币,钱很毛,5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
“好啊!”那李老板很痛快。父亲向店老板投去感谢的眼光。
火烧卖上了,张老板为了感谢父亲对他的帮忙,端给父亲一碗糊辣汤。
“小伙子,快喝吧!这么冷的天,也感谢你帮忙。”
“多谢大叔!我幸亏你帮忙!”父亲感激地说。
安丘南关大集的菜市场,爷爷则佝偻着身子,领着四叔,提着那个破篓子,一手拿着个破笤帚,一边小心地躲闪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扫着地上的花生皮,一边眼扫着那些卖白菜的,看有谁扒下点白菜帮来,爷爷跑去赶紧拣起来,放到一个破带子里,回去好洗一洗腌咸菜吃。
“啪啪啪啪,十里铺,十里长,临年过节发财旺;十里铺,十里长,求您一块白菜帮;天地冷,人心暖,求您烂菜好过年……啪啪啪”爷爷领着四叔,打着快板,沿摊讨要着。
“哎,老头,一边去,别耽误我生意!”有时爷爷还遭到白眼呵斥。
爷爷只好躲到到一边,等人家下集了再去拣丢在地上的那点带着烂叶的白菜帮。
卖完火烧,父亲再去粮食市场籴麦子,以备下一次打火烧。但粮食越来越贵,国民党钱越来越毛,表爷爷给的二斗麦子的本钱根本周转不动了。
爷爷连火烧都打不起了。
爷爷明显的老了,不到60岁的人,眼睛浑浊,步履迟缓,生活的困苦压抑使他麻木迟钝。奶奶没办法,仍和大娘出去讨饭。哪有的讨啊,经常空着碗回来。五叔则在家里照看姐姐。
即使表爷爷每隔5天来送一次柴火和干粮,可这是七口人啊!爷爷一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深夜,爷爷睡不着,迷迷糊糊地做梦。山川寂寥,万霜红染,淅沥萧飒,烟霏云敛,凄凄切切。苍茫凄凉的旷野,爷爷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了一个金光灿烂的地方。耀眼的光芒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走近后又像似曾相识。光华四射,熠熠生辉,分明是光的天空,光的大地,光的海洋。那些光芒似水若水般地波动着,光线一波一波地耀眼般的明亮,不时地随风摇动,金色的光芒时而骤起,时而伏下,时而奔涌,时而静息。倏忽间,那些光芒又变得很遥远,似乎退到天边的尽头,就像一枚太阳悬在那,远远地、悄然地向人间释放美丽的光芒。他在那些光芒涌来的时刻,忽然用手一抓,真抓住了一把,用手一攥,有着坚硬的质感。他细细一看,像碎金,又像谷粒。他翕动鼻子嗅了嗅,一种极熟悉的谷香沁入肺腑,好久没有闻到这种气味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捂在鼻子上,尽情地闻啊,闻啊,神情完全迷醉在光芒四射的谷香里。突然,他又发现了一片红彤彤的辣椒地,色彩斑斓郁郁葱葱,个个丰满,玲珑红脆欲滴,爷爷边摘边吃,越吃越香,火辣辣的,辣椒由嘴辣到嗓子辣到肠胃,翻江倒海,爷爷抱着肚子难受地蹲下。恰好父亲来了,看爷爷那么难受,问道:
“爷,你怎么了?”
“胃难受!吃辣椒吃的,想吐。”
“爷,咱回家吧!”
“哇!”爷爷吐出些绛红色的东西。他眼睛恍惚,就像潜水视物模糊,眼前老是那脑浆四飞的白加红的东西,堵得他胸口喘不过气来。
“不!不回去!我不想被乱石头砸死!”爷爷狂叫着。
“爷,你怎么了?做梦吧?”父亲拍了拍爷爷。
爷爷完全清醒了,他知道那是似梦非梦的饥饿状态的折磨。
“爷啊,不能再这样流浪了,眼看在这活不下去了,我们回去吧?”父亲凄凉叹气。
“不!老二啊,我何尝不想回去啊,但不能回去啊,回去也像小祖官那样被乱石砸死啊!”爷爷更是凄凉。
父亲无言。
腊月初三,父亲提着破篓子去南关大集打扫花生皮。“进入腊月步入年”,大集上已经隐隐约约透露着年味。散散落落的卖鞭炮的,用一根粗铁丝卡住一个大炮仗,点燃一根香,用燃烧的香头凑近炮芯,轻轻一吹,“哎!哎!小心喽!看俺的炮仗!”“咣”的一声,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个别富有的孩子忍不住掏出钱来买点解馋。这时候放整个一只鞭的还少。卖年画的拣些石头,把画的四角压住,任北风在吹着,自己蜷缩在墙角下,等着生意。一个老头在卖一种深黄色的地瓜糖,馋得父亲直流口水。邻村的李二狗自己用泥巴垛了个炉子在卖烤地瓜,手带一副破棉手套。“地瓜,地瓜,烤地瓜,滚瓜烂熟香甜的烤地瓜!”那味道飘到父亲鼻孔里,父亲禁不住吸吮了几口。
大集上的人明显的多了。父亲边打扫着散落的花生皮,边低头看那“年年有余”的扑灰年画。有人在后面戳了他一下。
“仕途啊,在这里啊!”父亲回头一看,是他老姑家里的近亲张锅炉子。“啊,是大叔啊!”
“仕途啊,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家(回)不去了!”张锅炉子说。
“怎么了?为什么?”父亲如晴天霹雳,惊问道。
“你们村里有个外号叫‘火炉子’的?”他问。
“是啊,是我的一个本家大爷爷,很近的大爷爷。”
“他前天晚上被国军打死了。听说你大哥也回去了。”
父亲一听,腿肚子哆嗦着提着破篓子就跑到南关找到了“鬼的好”高瑞云。他肯定知道信息。高瑞云正在卖火油,实际是国民党安排他在以卖火油名义打听刺探各方面信息。
“大叔,是前天晚上我‘火炉子’爷爷被国军打死了?”父亲怕周围有国民党便衣,偷偷地小声问鬼的好。
“是啊!”鬼的好说。
“咱村干国军的谁回去了?”父亲问。
“都回去了啊。”鬼的好说。
“俺大哥也回去了?”父亲问。
“回去了!”鬼的好说。
“俺哥哥住哪个地方?”父亲问。
“你大哥在西关一个很大的五间房子的大院里。”鬼的好说。
父亲拔腿去了西关。穿过几个曲曲弯弯的胡同,父亲好不容易找到大爷所在的部队驻地。
“站住!找谁?”站岗的问。
“我找李仕昌,就是跟着李竹明干会计文书的那个高个的。”父亲回答说。
“啊,仕昌啊!进去吧!往右拐,第一排房。”哨兵说。
父亲在大院里一站,看见一间比较气派的房子,里面是李竹明。当他向右看的时候,他透过玻璃看见大爷在房间里的同时,大爷也看见父亲了。大爷担心父亲来说啥,跑了出来。
“你来干什么?”大爷拉着个脸,脸色很难看。
“哥哥,咱大爷爷被打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
“你快家去吧!别管那么多!”大爷不容置疑。
“爷,坏了!完了!咱爷们完了!这回彻底完蛋了!咱回不去了。俺‘火炉子’大爷爷被打死了,俺哥哥也回去参加了。”父亲回家告诉爷爷。
“什么时候打死的?”爷爷问。
“腊月初一晚上。我去找俺哥哥了。”父亲说。
“你去找你哥哥回来。”爷爷说。
父亲只好又返回去找哥哥。
“我知道了,你先回家去吧!”大爷说。
大爷黄昏回到了三里庄。刚进门,碰到大娘挎着个“院子”出去要饭回来,要了一天的饭,“院子”里只装着半碗七长八短的地瓜秧子头。
大娘看见大爷,把“院子”一扔,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哭这命运,哭这生活,哭得肠断心碎。
“呜……呜……”一家人跟着都哭。
“瑜啊(大爷乳名叫瑜),你看着我和你娘死的展慢(太慢)了是咋?”爷爷呜呜地哭着和大爷说。
大爷没法说,也没的说,只顾哭。
天已昏黑,大爷看时候不早,泪戚戚地抱了抱姐姐,走了。
父亲说的“火炉子”爷爷就是李孟仲。李孟仲这名字我是太熟悉了。记得我小时候在村里上小学,每年给村里20多个烈士扫墓时,大队长王成才总是唾沫四射介绍我老爷爷李孟仲的事迹。可惜那时记忆不深,就听着玩,一直到多年后,我在父亲的采访中才彻底弄清楚了李孟仲老爷爷死因的前后。
俗话说:“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
1947年腊月初一,黄昏大约6点,大爷正在赶写一篇关于《安丘防御情况的报告》。种种迹象表明,昌潍大平原有一场规模巨大的血战,而安丘离潍县只有30公里,扼徐州、南京、临沂与潍县之要道,战略位置尤其重要。从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结束之后,共产党华东野战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根据形势的发展组成了外线兵团(亦称“西线兵团”)和内线兵团(亦称“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带领挺进鲁西南,进军豫鲁皖苏,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内线兵团由张界朋、谭震林指挥,留在山东境内,策应外线作战。国民党乘共产党主力外出之机,又拼凑了6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胶东解放区,山东兵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胶东保卫战,经过5个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的“九月攻势”,并乘势收复了除少数据点以外的大片地区,扭转了山东战局,迫使国民党转入了“点线防御”,被迫加强胶济线、津浦线的设防工事,强化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烟台等城市的防御体系,妄图以此阻挡共产党的攻势,维持残局。
“仕昌,整理行装,今晚有行动,准备出发!”李竹明安排道。
“去哪里啊?”大爷问道。
“管那么多干吗?是你问的吗?我也不清楚。”李竹明训斥道。
随着“嘟嘟”的哨声,100多人集合完毕,戎装“哐哐”出了南关,直奔西南而行。
队伍越走越近,大爷没想到是突袭秦戈庄。突袭的主要目的是抢粮。入冬以来,部队给养严重不足,上边供给不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俗话说:“金辉渠,银祖官,不如秦戈庄和土山。”我村水土肥满,较为富庶,一直是国共两党供粮的重要来源。
腊月初一正是朔月日,没有月亮的冬晚,更是一片黑漆漆。途经村庄除了几声犬吠,几乎不见灯光。静悄悄的夜晚,只有队伍行军刷刷的声音,偶尔传来几声低咳。
夜里十二点左右,队伍走到村东,这是进村唯一的必经之路,其他南北是山,西面为河。带队的张连长根据事先分工,四周放上流动哨,南山、北山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压阵,张连长安排大爷带领一排二排去包围民兵部,先解决民兵,其他村外待命。队伍事先保密很强,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民兵当晚转移了,只留下自卫团在民兵部。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是“鬼的好”高瑞云提前回村给民兵报的信,这使得鬼的好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赚了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躲过整顿和批斗,一直到我小时候记忆中那个老是背着手走路杨树杆子一样身材的老头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出去卖香油路上得了脑血栓最后躺在炕上平静地死去。多年以后也才知道那次偷袭民兵部是鬼的好提前告诉张连长说自卫团里有他近属,他不能出面,而让没有近属的大爷领着去,事实恰恰相反。他只不过不想让自己在乡亲们中受牵连。
清冷的夜晚,零下十五度,冬闲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为了省油,大部分村民都早早地脱衣睡了,甚至很多买不起火油的村民晚上是不点灯的。整个漆黑的村庄睡得烂熟烂熟,像李二狗南关大集卖的烤地瓜,平静而安详,就连狗都懒得叫,偶尔有老鼠从草垛里钻出来,嘴巴贴着地面,地撒欢寻爱找吃的。老槐树依然那么巍峨,高探的虬枝融化在漆黑的夜晚,像一副纯炭笔涂抹的墨画。
“咕咕!”队伍惊醒了不知名的夜鸟。偶尔有麻雀从草垛里飞出,消失在夜空里。
“排长,前面那排屋就是民兵部,我是本村的,乡里乡亲的就不便出面了。我在这里放哨。”到了老槐树下,大爷指了指黑暗中的民兵部。大爷这时突然改变注意,没跟着队伍包围民兵部,自己提着匣子枪站在了老槐树下。
“好!看好,上!”排长一挥手,训练有素的部队“哗”子弹上膛,打开保险,像狸猫一样“噌”一下散开,有的站在大门口,有的士兵在墙下一蹲,另一士兵脚踩其肩,那士兵“噌”一站,人借其劲,便翻墙进了院内,有的从后面,四面包围了民兵部。
民兵部里,老爷爷李孟仲和四个老头还没睡。老爷爷出去巡逻回来不久,要是晚一会儿就碰上队伍了。
“老宝大哥,今晚你和郑云值下班,这民兵拉出去了,更要多加小心!”老爷爷一边擦那膛线都快磨平的“汉阳造”,一边和一个老头说话。
“行,知道了。”那叫老宝的答应到。“那我们俩先躺一会儿了啊!”
老爷爷没有睡意,在昏暗的灯光下,边擦枪边低声唱他喜欢的那京剧《卧龙吊孝》。
一见灵位泪涟涟,捶胸顿足向谁言。我哭(哇)哭一声周都(哇)督,我叫叫一声公瑾先生(呐),啊……我的心(呐)痛酸(呐)。
见灵堂不由人(呐)珠泪满面。都督!公瑾!啊呀贤弟呀!叫(哇)一声公(呃)瑾弟细(呀)听根源,曹孟德领兵八十三万,擅敢夺东(呃)吴郡吞(呐)并江南。周都(哇)督虽年少颇具肝胆……
“死火炉子,你半夜三更唱什么哭丧啊,快睡!”老宝埋怨大爷。
“哎,这就躺下喽!这大冷天的俺火炉子要真搂着个火炉子睡觉那有多舒服。”李孟仲老爷爷答应着。“噗”一下,吹灭了煤油灯。
民兵部的后窗户冬天为了御寒,用“墼”堵死了。当老爷爷在唱《卧龙吊孝》的时候,一个士兵已用刺刀挖开了一个“墼”。
“哗啦!”土块掉到了屋内地上。
“什么人?有情况!”李孟仲刚躺下,一激灵,本能地抓起了“汉阳造”,一起身坐起来。就在他抓起“汉阳造”连子弹都没来得及上膛的时候,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从后窗射进来,紧跟着“哒哒”冲锋枪一个点射,一串子弹恰好平着全部射进了他的胸膛,李孟仲顿时全身像触电一样扭曲着,子弹从前胸进去又从后胸射出,几柱血流从枪眼飞溅而出,喷在炕上,喷在一边睡觉的老宝身上,老宝反应稍快一点,一骨碌滚到了炕下。
就在枪响的同时,房屋门“咣”的一声,几束手电筒光同时射进来,“不许动!不许动!”几声喝令,几个士兵全副武装,手端冲锋枪,冲了进来。
“他妈的,你们民兵呢?”进来的士兵一看是五个老头,老爷爷已成一个血人,倒在炕上,炕上满是喷出的血。那四个老头炕上炕下哆嗦着。
“天黑说有任务,转移出去了。”老宝回答到。“老总,我们只是村里值班打更的啊!”
枪声就是信号,张连长一挥手,队伍“哗”开进了村里。同时,降媚山和北山上两挺重机枪“哒哒哒哒”响起来,在这寂静的夜晚叫得更加凄厉。
平静的夜晚陡然打破。哭声、喊声、人叫声、马嘶声、牛哞声、狗吠声交织在一起,穿透村庄的各个角落,穿透寂静的深夜,穿透人们冰冷的心。
老槐树下火把通明,把斑驳脱落的树皮照成了古铜色。熟睡中被激烈枪声惊醒的人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个个的家门被枪托砸开,大人小孩被赶到了老槐树下。张连长把庄长王希提从人群里提溜出来。
“爷们,今夜出来,不想太难为乡亲,更不想让乡亲们流血。你村共150户,我们就要5000斤粮食,不多,你看着办吧。”张连长说。
大爷听到民兵部枪声后,就没脸露面了,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刽子手。当张连长带人进村抓人弄粮食的时候,他没有听清楚张连长以后说了些什么。他茫然地提枪进了民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