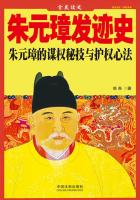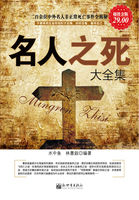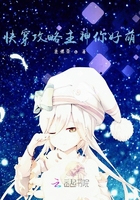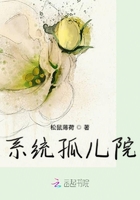徐悲鸿第一次出国留学,东渡扶桑,未及学成,几乎是无功而返。哈同赞助的学费花光了,徐悲鸿再也没有能力自费留学,他必须想办法考取官费。
为了继续自己的求学之路,徐悲鸿在上海拜见了康有为。
徐悲鸿怎么会认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的呢?在这个时候,康有为能为他的留法梦想助上一臂之力吗?
早在1917年,徐悲鸿去日本之前,他就画了一幅完全用西洋写实手法绘制的水彩画,名叫《康南海六十行乐图》。
“康南海”正是康有为。这位当时名震海内外的维新派领袖是广东南海人,因此别称康南海。画面取中国传统园林背景为衬托,描绘康有为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或许是为了刻意体现这一书香世家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徐悲鸿还在画中为前排的一个小男孩搭配了一身洋装。这身小洋装并非毫无缘由的点缀,徐悲鸿或许想到一向推崇西方先进思想,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说不定会理解他支持他出国留洋,去西方学习绘画艺术的梦想。
徐悲鸿是怎样结识康有为的,这还要从他在哈同花园做事的时候说起。当时圣仓明智大学常常邀请名流来校讲学,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从康有为的言谈中,徐悲鸿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画应当改良的观念。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的绘画已衰敝之极,墨守成规,缺乏创新,他主张应该学习西方的写实主义,融合中西画法的精华加以变通。康有为渊博的学识和改良中国绘画的精辟见解深深吸引了青年徐悲鸿。与此同时,徐悲鸿的绘画才能,尤其是他擅长写实的风格也深得康有为的赏识,他不但把自己丰富的书画收藏拿出来供徐悲鸿欣赏,还请他为自己全家画像。
一位清末维新变法的领头人物,他必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国体和国运。因此,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他认识、理解并关注像徐悲鸿这样一个有正义感、有上进心的艺术青年,或许不仅仅是上天赐予徐悲鸿的幸运,更是偶然中的必然。
与康有为之间亲如师生的关系,成为了徐悲鸿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契机。就这样,从日本归国后,一心向学却苦于求告无门,深感前路渺茫的徐悲鸿登门拜访了康有为。一个月后,带着康有为的举荐信,徐悲鸿去了北京。
在中国近代史上,1917年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虽然这里充满了争权夺利的政治动荡,但是,主张反对封建专制,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这里风起云涌。
这一年的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主张破除旧的文学规范,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面貌。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大学改制。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声援胡适。
1917年12月,就在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22岁的徐悲鸿来到了北京。当康有为的弟子、前总统府秘书、著名诗人罗瘿公读完康有为的举荐信并看到了徐悲鸿带来的作品时,大为惊喜,随即写信向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推荐了徐悲鸿。
傅增湘是当时手握留学官费发放权的关键人物。在面见了徐悲鸿之后,他也确认徐悲鸿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画家,并诚恳地表示,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平息,一定为徐悲鸿申请一笔官费,实现他前往欧洲留学的愿望。于是,徐悲鸿和蒋碧微安心地在北平住了下来。
应蔡元培和傅增湘的聘请,徐悲鸿担任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虽然年纪轻轻,但在艺术上的悟性和满怀的抱负让他在北平文化界崭露头角。徐悲鸿针对中国传统绘画走向泥古不化的局面,号召画坛有识之士奋起革新,并撰文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重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的主张。此时尚未走出国门的徐悲鸿就具备了如此见识,足见他对于自己留洋的目标早就了然于胸,他对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理想亦早已有了成熟的思考。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文化古都北平的时代氛围为年轻的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丰富的世界。在这里,他有机会到故宫观赏大量古代绘画稀世珍宝,还结交了罗瘿公、黄宾虹、金城、樊樊山、萧友梅、陈师曾、胡适、鲁迅等社会名流。他更在无意中爱上了京剧艺术,与京剧泰斗梅兰芳和程砚秋过从甚密,并为他们画像。
艺术都是相通的,舞台上的色彩、动感和精彩的念唱做打,给徐悲鸿带来无穷无尽的艺术灵感。年方24岁的徐悲鸿,在这样的熏陶下,很快便全方位地展现出了一位未来大艺术家的潜质和素养。良师益友、丰富多元的精神养料以及京城独有的文化氛围让等待留学官费而滞留北平的日子变得并不那么漫长。可是,对于徐悲鸿的新婚妻子蒋碧微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用度日如年来形容她的状况大概也不为过。一个没有自己事业的旧式女子,在陌生的城市,傅增湘没有丈夫的陪伴,怎敢独自出门。蒋碧微几乎终日独守空房,等待流连于各类文化活动中的丈夫回家。个中滋味对于这个在故乡被父母捧为掌上明珠的蒋家二小姐,简直是苦不堪言。蒋碧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初到北平,不但乡音未改,而且还听不懂那种地道的北平话,平时既没有谈话的对象,朋友中女性又少,因此觉得非常寂寞。往后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听朋友在说北平住家怎么理想,可是我就从来不曾想过要到北平去住。因为在我记忆里,我那一年的北平生活,只有苦闷和贫穷。”
而全身心投入北平文化生活的徐悲鸿,对此也无计可施,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安慰妻子,唯有盼着早日拿到官费,和蒋碧微双双前往法国。他心想也许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可是没想到,一波三折,当教育部再次公布向欧洲派遣留学生的名单时,却没有徐悲鸿的名字。年轻画家按捺不住自己的失望和气愤,写了一封措词十分尖锐的信,质问傅增湘。这让介绍人罗瘿公面子上有些难堪。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学习。蔡元培此时给傅增湘书信一封,问可否再给徐悲鸿一次留学的机会。这次,傅增湘没有食言,也不计前嫌,终于让徐悲鸿获得了宝贵的留学官费。这件事让年轻气盛的徐悲鸿感到有些局促和惭愧。当他前往傅增湘处向他面谢时,这位教育总长只轻描淡写地表示“不失信而已”,“神态举止也表现得恂恂然如常态不介意”。
这笔官费,真正启动了艺术大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航程,也撞开了属于他的命运之门。从背井离乡独闯上海,到自学法文考取震旦大学,再到欧战爆发转道日本游学,又因资金难继中途折返。几番起落,坚持如初,最后终于得以成行,徐悲鸿凭的是毅力、恒心,当然,更离不开他生命中遇到的贵人。
多年后,徐悲鸿曾这样回忆道:“余飘零十载,转走千里,求学之难,难至如此。吾于黄震之、傅增湘两先生,皆终身感戴其德而不忘者也。”
命运就是这样莫测,但似乎也暗含着某种必然。
那叶曾经风雨飘摇的扁舟,如今终于换成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船,扬起生命的风帆,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