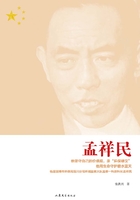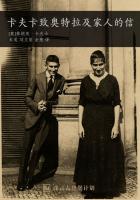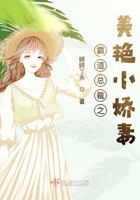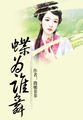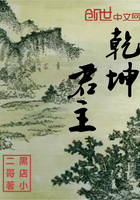引言中曾提到笔者的一位法国朋友家中收藏有一幅徐悲鸿的画,摄制组打算采访他。这一安排也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影集团领导的支持,他们认为观众过于熟悉徐悲鸿,恰恰是这样一类独家信息也许能从一个不同的视角给观众带来新鲜感。收藏徐悲鸿作品的华人很多,并不出奇,可是中国观众却还不知道一个法国收藏者眼中的徐悲鸿究竟是什么样的。
2011年10月,在巴黎老城区,我们的剧组见到了比尔纳特先生。他开了一家美容院,生意不错。收藏艺术品是他家祖上三代的嗜好。他告诉我们,他是在自己父亲的一堆收藏品中发现徐悲鸿这幅画的。一见到它,当即就被深深吸引,于是加以精心保存。
近年,随着徐悲鸿作品拍卖屡创新高,声震国际艺术品市场,比尔纳特先生在法国的报纸上看到关于徐悲鸿奔马作品拍卖会的消息,发现与自己收藏的画很像,回家仔细研究,才知道祖上收藏的正是徐悲鸿的作品,喜不自禁,更是爱护有加。当他将原作展示给我们看时,大家都很惊讶。那是一幅尺幅并不大的画作,可画中吃草的马儿却栩栩如生。此画画于1926年,正是徐悲鸿留学法国期间,画家的签名落款俱全,一看便是真迹。想必早年徐悲鸿还不像今天这样出名,要想在法国临摹他的画风笔迹,此事也多半不可能发生。不知经过怎样一番辗转,这幅二尺见方的小画才得以与比尔纳特先生一家结缘。
我们给画中那匹吃草的马儿拍下了好几个特写,在那一刻,徐悲鸿的画作再次将时空串联,让我们的遐思回到了将近一个世纪前大画家徐悲鸿留学法国的日子。
“世界艺术的中心”,博物馆林立,名家大师的作品真迹也琳琅满目。徐悲鸿一下船就忙于四处参观美术作品展,在众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之间流连忘返。这些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简直令他如痴如醉,他废寝忘食,终日浏览观赏、学习研究。与此同时,徐悲鸿进入了一家私立画院补习。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大致掌握西画的技巧,并参加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严格的入学考试。在报考之前,他还需要选择一个主攻方向。
在前往法国的路上,徐悲鸿夫妇曾途经英国,借下船短暂停留的机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当看到古代希腊巴维农古神庙的浮雕时,徐悲鸿叹息道:“唉,为什么不让我慢慢地见到它,而使我骤然站在它的面前,以致惊恐无比呢!”比起中国画的写意,西方古典绘画技法的写实让徐悲鸿大开眼界。
事实上,20世纪初的法国画坛正处于一个流派纷呈、激烈变革的新时代。继诞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印象派”之后,以凡?高、高更为代表的现代派绘画开始成为了西方画坛的主流。而徐悲鸿来到法国求学时,凡?高已经去世30年了。此时,画坛上最为流行的是表现主义绘画,在法国,就是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所以后来很多与徐悲鸿同一时期先后来到法国求学的艺术家都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现代主义的绘画道路,比如林风眠、潘玉良、赵无极和吕霞光等。
而徐悲鸿却偏偏把目光投向了一百多年前引领了西方画坛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写实绘画。
新古典主义的绘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推崇古典风格,推行古希腊、罗马的艺术语言、样式、题材、风格,是为其达到喻古讽今的目的。
由于与法国大革命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古典主义以新的内容,使得许多艺术家能够突破古典主义的程式束缚,创造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因而新古典主义又常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崇尚古风、理性和自然,其特征是选择严肃的题材、注重塑造性与完整性、强调理性而忽略感性、强调素描而忽视色彩。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路易。大卫、安格尔、德拉克洛瓦、杰里科等。
徐悲鸿将自己的主攻方向定位在写实主义绘画,也许正是因为他感觉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艺术也需要一场畅快淋漓的革命。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写实为它的基本表现形式,选择严肃的重大题材,包括古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在艺术形式上,强调理性而非感性,在构图上强调完整性,在造型上重视素描和轮廓,注重雕塑般的人物形象,对造型的准确性要求极为严格,非常强调素描的主导作用。而这一切,正是徐悲鸿所需要和向往的。
当时,在卢浮宫法国馆陈列的几幅新古典主义名作给徐悲鸿的内心以极大的震撼。这就是杰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和《荷马三兄弟的誓言》,以及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导人民》。
画面上那喷薄而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令他着迷,那种描绘人民为自由、为解放、为民族大义和推翻腐朽制度而奋争的史诗般的画面,深深触动了徐悲鸿,让他想起了自己正处于军阀混战、列强瓜分中的祖国。
这时的徐悲鸿已经做出了选择。可是,当时的法国已经没有一百多年前新古典主义辉煌时期那种大师云集的氛围,画这样的写实派巨幅画作的人早已越来越少,而且良师难觅。大型油画本来成本就很高,又难以找到买主,那些现代派的小幅画作在当时既流行又比巨幅油画更容易绘制,那么,徐悲鸿为什么还偏偏对已经在欧洲过了气儿的写实派绘画情有独钟呢?
徐悲鸿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世界艺术的没落与中国艺术的复兴》。这是他观察了世界的艺术之后为自己,也是为中国艺术界确定的一个目标。即便终于如愿来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徐悲鸿的内心也一刻没有停止对危难中的祖国的关注。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杨晓阳在接受剧组采访时说道:“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成为头等大事,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的时候,文艺是什么?文艺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应该说是文艺已经变成了一种武器,当成为武器的这种美术,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是写实画法,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于是,在欧洲渐渐少有人问津的写实主义成为了徐悲鸿的不二选择,而他对当时日渐盛行于欧洲艺术市场的唯美、小资的现代派绘画反倒是敬而远之。在我们采访的专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美术研究员郎绍君这样评价徐悲鸿:“他从来都不是在为艺术而艺术,徐悲鸿选择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就是为人生而艺术。”
怎么去理解徐悲鸿的“为人生而艺术”呢?那就让我们继续在大师的人生旅程中找寻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