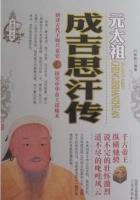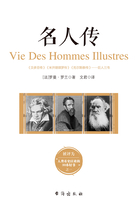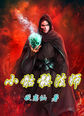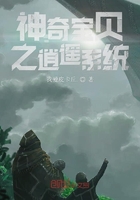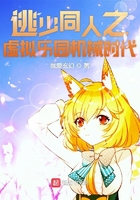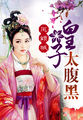1915年,就在徐悲鸿带着梦想远离家乡宜兴再赴上海时,宜兴一个大户人家蒋家,因为81岁的老太爷去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丧礼。而死者正是日后成为徐悲鸿妻子的蒋碧微女士的祖父。
比起徐悲鸿四处借贷为父亲奔丧,蒋家老太爷的丧礼极为奢华气派。在蒋碧微的书中曾这样描述那场丧礼:“宜兴人办丧事,繁文缛节,相当隆重。……殓棉是用做成套子的丝绵,将死者全身套起……然后再穿上衣服,衣服必须是单数,祖父穿的是前清的官服,从里到外,一共是九件。”
蒋家是宜兴的大户人家,祖上为官,世代书香,隆重的传统丧礼不足为奇。与1899年出生的蒋碧微相比,徐悲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他们虽然都是江苏宜兴人,但两人的出身和社会背景悬殊。
据说,徐悲鸿宜兴屺亭桥镇的祖屋是他的祖父在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流落宜兴做了十年苦工所建。
小悲鸿出生于甲午海战的次年1895年。当时清政府与列强侵略者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加重了百姓的苦难,大批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破产逃荒流落异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徐悲鸿画工出身的父亲徐达章根本无法仅靠在镇上卖画维持全家生活,他必须起早贪黑耕种七亩瓜田以应付必需的日常开销。幼年徐悲鸿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很小就下地帮父母干农活,照顾弟妹,自然比一般孩子更早熟。
当童年时代的蒋碧微在富有的大家庭中品尝各式点心、定制绸缎衣裳,度过一个又一个场面热闹的节日时,徐悲鸿却早已跟随父亲流浪江湖,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卖画生涯。
就是这样两个看似门不当户不对的青年男女最终却结为了夫妻。这缘分说起来与一座花园息息相关,那就是当时位于上海孤山路的一座私人别墅——哈同花园。
哈同花园曾在上海显赫一时,它的主人是犹太富商哈同和他中法混血的夫人罗迦陵。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此话不假。哈同这个曾经的流浪儿,悄悄登上一艘德国船只来到上海滩,以一个犹太人的聪明狡诈,勤奋打拼数年,终于开始飞黄腾达。当逐渐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夫妻俩开始热心于创办学校和扶持各类文化活动。
就在徐悲鸿1916年考上震旦大学后不久,他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的广告。或许哈同夫妇认为尊崇孔子还不够,还要大力宣扬汉文字的创始人仓颉。
仓颉是传说中“四目灵光”的圣人。徐悲鸿根据古籍记载,画了一个身披树叶,长发齐肩,满面须毛,眉下四目的巨人,寄出应征。那是一幅一米多高的水彩画,当时立刻征服了明智大学的教授们,也得到了哈同夫人罗迦陵的赏识。哈同花园的总管姬觉弥立即派车接来徐悲鸿,交谈之后,更为器重。于是诚邀他担任哈同花园的美术指导方面的工作。由此一来,正在震旦大学读书的徐悲鸿,不仅有了交学费的钱,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当他遇到蒋碧微之时,落魄的状况已大为改观。
借助这次机会,年轻的徐悲鸿暂时摆脱了相当一段时间内困扰着他的贫困窘境,而且还平生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窗明几净带阳台花园的画室。但他却并不留恋这一切。学好法语,留学法国的梦想仍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
那时,蒋碧微已随父母从宜兴迁到上海,他们的家离哈同花园不远。经同乡朱了洲的介绍,徐悲鸿认识了年长于自己的同乡蒋梅笙,并成了蒋家的座上宾。
蒋梅笙夫妇见徐悲鸿才华出众,十分喜欢。他们又得知徐悲鸿在家乡的原配妻子在他漂泊上海期间不幸亡故,更多了一份同情,茶余饭后,经常念叨着这位年轻人。可他们却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二女儿,当时年仅18岁的蒋碧微,在此期间已悄悄有了自己少女的心思。
这位此后与徐悲鸿维持了28年婚姻的蒋家二小姐,在她的自传体回忆录《我与悲鸿》中曾经这样写道:“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秘密的喜悦。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许多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这使我对他深深的爱慕和敬佩。”
蒋家是个传统保守的旧式家庭,生于斯长于斯的蒋家二小姐蒋碧微自然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敢越雷池半步。两个年轻人多次见面却从未私下交谈过一句话。即使偶然遇见也会尽量地避开。
渐渐地,一种微妙的情愫在蒋碧微心中生长,令她惶恐而不知所措。因为她13岁那年已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世交查家定亲,眼看着迎娶的日子慢慢逼近。一天,朱了洲来到蒋家,突如其来地问了蒋碧微一句:“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去外国,你去不去?”这个想带她一起去国外的人正是徐悲鸿。蒋碧微在《我与悲鸿》一书中这样描述那一刻自己的心理活动:“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它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制……”这不可遏制的青春暗潮裹挟着蒋碧微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奔向徐悲鸿,奔向自由。就这样,在那个年代,徐悲鸿与蒋碧微听从了内心的呼唤作出了抉择。
出走前夜,蒋碧微给父母留下一封信。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女孩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由的新生活,除了向包办婚姻说不,她别无选择,只能恳求父母的谅解。蒋碧微顾不上去想已定亲的查家一夜之间找不到即将过门的新娘,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如果他们前来质问父母,父母双亲又会是何等的难堪;她也不管未来的生活将充满怎样的动荡艰难,这个从小到大养尊处优惯了的蒋家二小姐此刻唯有义无反顾,因为在她心里,眼前这个有志青年就是她的希望,她的幸福寄托之所在。
而对于徐悲鸿而言,这也是他在那段失败的包办婚姻之后的第一次自由恋爱,他心向往之,非常珍惜。他为原名“棠珍”的爱人改名为“碧微”,并将这个名字早早地刻在了一枚水晶戒指上。在他们双双登上离家的大船时,徐悲鸿将这枚戒指赠给了蒋碧微。
可两人这一走,留给蒋碧微父母的,却是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
在今天,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是压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的大山。居然敢和包办婚姻叫板,甚至双双私奔,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世俗所不容。
私奔的消息渐渐传开,闹得满城风雨。好事者更是添油加醋地渲染,查家也听到了风声,十分气恼。为了顾全两家的颜面,蒋家只得谎称女儿到苏州探亲,突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为了让这个还说得过去的理由更站得住脚,蒋碧微的母亲又托人买了口棺材,里面放上石头,抬入一座寺庙。做到这个份儿上,才将此事摆平,蒋家人为此也心力交瘁。
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徐悲鸿与蒋碧微奔向自由的路却并不平坦。摆在面前的,首先是二人的感情是否经得住现实生活的考验。毕竟,两个年轻人交往时间尚短,彼此了解不深,那种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夫妻之情,还需假以时日,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培育与磨合。而求学的艰苦环境、条件、甚至不期而然出现的意外,往往令人猝不及防,考验着这对年轻的夫妇。
那日,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双双登上远洋的大船,然而那艘船却并不是开往法国的。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中断了。可二人私奔的计划已经定了下来,可谓弓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间紧迫,徐悲鸿决定行期不变,先带蒋碧微去日本。临行前,哈同赠送给徐悲鸿1600元现洋。夫妻二人在日本期间的全部开销就要依靠这笔钱了。
虽然是被迫改道,东渡扶桑,在日本的学习同样让22岁的徐悲鸿开了眼界。他欣喜地看到日本画家已渐渐脱去了拘泥于古人的成例,能仔细观察和描绘大自然,尤其以花鸟画最为出色。于是,徐悲鸿经常流连于那些书店或画店,遇到自己喜爱的书籍或美术复制品,不管多贵宁肯饿肚子也要买下来。
而从小衣食无忧的蒋碧微,突然间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没有朋友,生活上完全依靠一位眼中只有艺术的丈夫,还需处处省吃俭用,她何曾吃过这样的苦。眼前这位她曾一度那么爱慕的年轻画家,似乎爱艺术胜过爱身边的美娇娘,完全忽略了她的内心感受和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寞。日渐增多的不满与怨愤堆积在蒋碧微心头,不知不觉中销蚀掉了新婚燕尔的甜蜜。他们的共同生活开始悄然出现了阴影。而一心钻研绘画艺术,每日如饥似渴地观摩和学习日本绘画的徐悲鸿,在揣度女人心思方面却显得那样木讷、愚笨,对新婚妻子内心微妙的情绪浑然不知。
一晃,半年过去了。东京的物价很贵,尽管处处节衣缩食,这对新婚夫妇身上带的钱还是花光了,无奈之下,二人只得打道回府。这让蒋碧微极为难堪。当初毅然私奔,得罪了父母和亲友,本想着悲鸿能够在外干出一番事业,也好夫荣妻贵,荣归故里,向父母赔罪。如今却是这样的狼狈不堪,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又回到父母的身边,心中对徐悲鸿的不满便更多了几分。蒋碧微的父母虽然曾为孩子的私奔受尽委屈,一度气愤难平,但见爱女终于平安归来,还是原谅了他们。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一个情感丰富的画家带着心爱的姑娘私奔,一起求学,今天看来都极富戏剧性和浪漫色彩。这并非电影电视剧中的场景,而是真人真实的经历,而且是发生在伟大的艺术巨匠徐悲鸿身上的传奇爱情。我们的摄制组后来在采访徐悲鸿与蒋碧微的女儿徐静斐时,她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我妈妈跟我说过,她当年就是觉得我父亲帅,自己奋斗,有志向。”多么简单的爱,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也是人人能明白的一颗纯真少女心。然而,他们的爱情也像任何一个时代年轻不经事的初恋男女一样,充满不成熟的脆弱和对未来的不确定。
一位伟大的画坛巨匠也有着与普通人别无二致的喜与悲,也有着七情六欲,大师在我们眼中仿佛更亲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