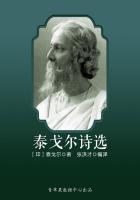在漳州度过大半生后,吴沙动身去了台湾。43岁,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收敛心性的年龄,但是对于吴沙,这似乎才是个开始。
这一年,是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4年。
早在吴沙入宜兰前,宜兰称作“噶玛兰”或“蛤仔难”。噶玛兰人在兰阳溪的出海口已经生活了上千年。他们以兰阳溪作腹地,驾着NO舺”(独木舟)在太平洋航行,与汉人互市。而西南山地的泰雅人长期与世隔绝,极其骁勇。
西方人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1632年。一艘西班牙船因为飓风漂到这里,船员50人悉数被戮,这引发了西班牙人的报复行动,7处部落被焚毁,几百个居民被杀死,然后西班牙人在这里修建了城堡。
然后是1877年的牡丹社事件,两艘琉球船又是因为飓风漂到这里。船员与牡丹社部落民发生冲突,结果,54人被杀死,其余12人在汉人的营救下逃生。出入在。
因为地理和民风之故,到乾隆年,当台南、台中、台北已经全面开发,这里依然是一片荒原。
一直到18世纪末,噶玛兰才真正进入大陆移民的视线。
先民开垦最初集中在平原下游,到道光年间,才扩散到兰阳溪两个支流-宜兰河和冬山河,最后扩张到泰雅人生活的西南山区。
这一切应该说是从吴沙开始。
吴沙到达台湾时,汉人大规模的拓垦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整个台湾平野人流涌动,田地、果园、水圳,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不断涌入的劳动大军和无法回家的异乡人的坟茔,时刻考验每一个人的身体和大脑的承受能力。不久发生的林爽文事件已经显示,一个跨越式成长的生机勃勃的新居住地正在因为生存压力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而充满风险。
吴沙最初的落脚点是淡水。然后,往淡水的边荒之地三绍社与平埔人贸易。当年,这种行当叫“番割”。吴沙把从汉族商人那里取得的草药、布匹、盐、糖和刀具卖给部落,换回山货,再转卖给汉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没多少人愿去的地方,从事这么一种有些危险的职业能够侥幸不死而且得到部落民的信任。到了五十几岁时,他不再是一个离开家乡的落魄的农夫,而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富裕的商人,因为“通番市有信”,又肯接济汉人,平民吴沙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追随者。
今天,在宜兰礁溪Y吴沙村中吴沙故厝所能见到的吴沙像,大抵是这个年龄的样子——沉默无言、长髯及胸、额头刻着岁月的印痕,眼神写满沧桑,不这是一个的者,是经的,是一个的知天命之年,身体不再壮美,步态不再娇健,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远行人者家,几地、一者他是,兰平地,地丰硕。掏一把兰阳溪水,水中带着甜意,一个出身贫困的富裕商人的人生恰如盛宴,身体正走向荒芜,但生命才现华美。
1787年,吴沙把投奔他的200多个漳泉人、潮惠人集合起来,一人一斗米,一人一把斧,在三貂社附近的贡寮,凿山、开河、伐木、修路、架桥、垦地。
一斗米,可以果腹一把斧头,可以搭寮。对于一无所有的新移民来说,这些最简单的生活资料与生产工具,便是新生活的开始。一些年后,如果侥幸不死,他们将成为一棵大树,他们的后裔,将成为大树伸出的无数枝桠,那些活跃在政界、商界或者寻常巷陌的,都将因为他们的袓辈而荣耀。
不久,投奔吴沙的人已达上千,漳州人因为乡亲的关系,占了九成。人迹罕见的荒野,出现大片良田和果园,道路和车马,打破山间的平静,部落民和汉人也算相安无事。
这一年,吴沙56岁,离汉人轻易不敢走进的噶玛兰已经近在咫尺。
随后,几个和他一起做“番割”的朋友一许天送、朱合、洪掌参加了进来,然后,又有淡水富户——柯有成、何缋、赵隆盛的财力支持,而淡防同知何茹莲的默认,使拓垦有了基本的条件。
1796年9月16日,大清帝国刚刚从乾隆年走入嘉庆年。
吴沙带着一千多个漳泉农民和三十几个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人,乘船抵达噶玛兰乌石港,合筑土围,开垦荒地,这是噶玛兰的头一个汉人村落,所以叫“头围”。
从此,头围有了妈祖的香火。
因为庆贺刚刚到来的嘉庆元年,或许,也为了祝福刚刚开始的拓垦,宜兰的第一座宫庙取名庆元宫。
这一年,吴沙已经65年,离贡寮试垦,中间又隔了9年。
9年,可以把热情冷却成冰,把生命挫成灰焊,而吴沙,则在专心做一件事,如果时间可以用来绣花,这时候已经花团锦簇。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由青壮年作骨干的大胆的冒险行动所体现出来的老年人的谨慎与睿智是多么重要。
吴沙在长时间的准备后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结首制”是他们的组织形式。垦丁数十人为一结,数十结,为一围,相互支援。小结首,晓事而资产多者担任大结首,以富强有力公正者担任。土地垦成,众4公分,结首倍之或数倍之。
五六万的垦丁就这样被组织成一支劳动大军。
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决策和筹资,在进入之前已经完成前进路线,已经悄悄借打柴进山绘好二百多个护卫,为推进的拓垦队伍设防.每前进一段,就设立隘寮,派隘丁把守山间的警讯,由这个隘寮传递到另一个隘寮,往往比袭击者还来得迅速。而五六十个乡勇在垦地穿梭巡防,经费由垦丁负担,每五甲(一甲11.5亩)为一张犁,每张犁,取银元一二十元。沟通是必须的,三十个“番语”翻译,可以用和平手段,把突发事件造成的危险降到最低。后勤补给,包括衣、食、住、农具、种子、车马,供应大体能做得有条不紊。
不过,冲突仍在预期中发生。结果,噶玛兰人失去了兄弟,汉人的首领吴沙也失去了兄弟,在一片悲伤中,吴沙回到三貂社。
今天,游人或者被那种民族融合后形成的多元文化趣味所倾倒,一些与那段历史有关的蛛丝马迹被发掘出来,作为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者作为卖点。但是,对于那个时候,那些拼命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人,对于那些努力扞卫自己生活区域的人,他们的经历都有刻骨铭心的伤痛。
有一个了大的。
据说嘉庆二年,噶玛兰人的村落发生了天花,在那时,这是要命的疾病,不过吴沙没有心情等待人家灭族,好发展他的事业。他的妻子,那个叫庄梳娘的乡村郎中的女儿,显然也是个信仰妈袓的人,按照漳州民间处方把草药熬制成汁送给番社。据说,有好几百人因此幸免于难。这种仁义感动了噶玛兰人,他们划出土地交给吴沙,双方依照噶玛兰人的习惯埋石为约,互不侵犯。人介彼此间的争端,因为善念终于化解。
这个故事有民间传说的美丽,我们因为感动而相信它的真实。
我介不知道,这样的感动是否迅速传遍所有的少数民族部落,让那些愤怒的脸从此有了兰阳溪水一样亲和的表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传统的猎区变成农田,传统只能变成追忆。
吴沙再度入垦头围是良好的开始。噶玛兰人信守诺言,不再骚扰。吴沙因此广招佃户,用漳州的农耕技术培育出垦区的丰登五谷。
头围成了汉人在噶玛兰建立的第一个村落,接下来,是“二围”,然后是“三围”……
那时的头围,因为农事,人员骤增,街市繁荣,成了台北、基隆商旅进入噶玛兰地区的中转。光阴轮转,又成了今天人们说的头城。
头城,宜兰平原的第一座城镇,因为临近兰阳地区唯一的商港一乌石港,而与大陆、台北贸易往来频繁,盛极一时。
建于嘉庆元年的庆元宫,见证过它的繁华,供奉妈祖的香火和吴沙的那个时代一样馨香浓郁。
那些阅尽风华的旧日的街,清代闽南样式融合了日据时期的繁复雕饰,成排的红砖店屋圆拱连绵,墙上依旧刻着昔日的商号标识。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吴沙而开始。
嘉庆三年十二月九日(1798),正是北风紧时,吴沙一噶玛兰垦荒者的老迈的首领生了一场病,去世了,三貂岭贡寮一他事业的起始地,成了他的墓园。
这一年,吴沙67岁。
他的侄子继续把土地开垦到整个兰阳溪北岸。
43岁赴台,56岁试垦贡寮,65岁入驻噶玛兰,67岁辞世,头尾垦地6万,天年,嘉庆十五年(1810),噶玛兰垦丁已有5万,其中,漳州人42000,泉州人2500,广东人140,归化的部落民38社,5500人。
嘉庆十七年(1812),朝廷设噶玛兰厅,垦地正式收入大清版图。
光绪元年(1875),噶玛兰厅改宜兰县。
今天的宜兰,棋格状的田野,嫩青水绿,鱼池散落其间,像一方方明镜。村舍参差,错落有序,宛如桃源。与它一山之隔的台北,却是繁华的都会。目光尽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在这儿收口。地势低平的沿海一带,公路两侧,一面,是起伏不定的山峦,白色的鸟影,时隐时现另一面,是无垠的太平洋。驱车奔驰,一路印象,山水宜兰。
吴沙辞世后的第63个年头,因缘际会,他的一个叫陈辉煌的漳浦同乡来到这里,因为身为泰雅人叭哩沙酋长的岳父的帮助,花了近30年的时间,又把兰阳溪南部全部开垦。
这个时候,距吴沙贡寮试垦,已有80个年头。
从此,宜兰,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昨天今天明天
有时!人们会觉得历史是一个奇妙的轮回,当五百年光阴一闪而过,隔着一道海峡,漳州的身影与台湾的身影,或者将再度融合在一起,并开始一个新的故事。
站在西海岸,眼前是一片无垠的大海,如此蔚蓝,蔚蓝得可以入梦。
在最近的5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片海域曾经承载过太多的梦,航海者的梦、商人的梦、政治家的梦、军人的梦、农夫的梦……贸易,战争,多国外交,历在这里从。
在逝去的岁月里,漳州河口驶出的商船,曾经引领着中国的风帆时代,并且使漳州的身影和台湾、欧洲的近代历史融合在一起。
今天,生活在这儿的人们大抵有这么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人们认为:这个城市不再偏居东南一隅。逶迤700公里的海岸线,造就二十几个天然深水港湾,133个万吨级码头,等待开发。福建6个深水港湾,漳州拥有2个。九龙江、漳江、鹿溪,那些曾经孕育过海洋商业文化的短促的河流,重新被赋予临港石化工业布局的历史使命。厦门港、东山港,它们的前方,是广阔的太平洋,在它们的后方,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腹地,浅滩、丘陵、山峦,绿色、宁静、富饶。全国第一家台资企业、全国第一大规模台资农业企业、全国第一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区、全国第一个两岸农业经贸合作平台、全国第一批台湾农民创业园、全国农业利用台资第一、水果之乡、花卉之都、水产基地有时,人们会用文学笔调来表达这么一层意思:这是被花神祝福过的大地,一年四季,繁花似锦春夏秋冬,灿若云霞。人们有时会做这样的随想:如果“南澳一号”重现的只是一段封存的时光,一阙久远的青花往事,“克拉克瓷”的故乡,依旧的涛声或许正在唤醒曾经的丝路花雨。
人们总是努力将自己更多地和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当生活需要一些变的时人们、公、海、海、码头……然后,把这里修成了国家级交通枢纽城市。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数个世纪以前在西方古航海图上屡屡出现的城市,一座被西方航海者视为财富与荣耀所在群起而至的城市,一座有着失落的英雄情节的城市,开始展示气质的另一面:冲动、吸金、魅力、潜力,并因此成为台商投资密集地。
一种常被人们拿来讨论的话题是:当两岸产业互相开放,迫切需要寻找发展空间的台湾石化、机械、纺织、农业、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等产业将改变什么?
有时,人们会觉得历史是一个奇妙的轮回,当五百年光阴一闪而过,隔着一道海峡,漳州的身影与台湾的身影,或者将再度融合在一起,并开始一个新的。
几百年前,人们穿越海峡,找到他们的岛,为的是寻找机会。
几百年后,人们穿越海峡,重登大陆,为的是寻找更多的机会。相逢一笑,我们知道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无论语言,无论体貌。但是,N了那么久,区别总是存在的,区别就是区别。
知道这一点,寻找到更多的相似点,或许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