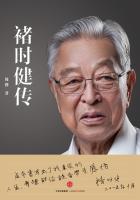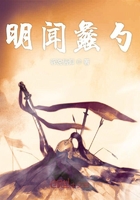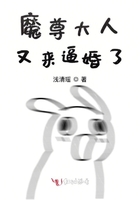《玛丽》的中心主题是回忆。这点在小说的题记中就昭然若揭。题记引用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两行诗:“回忆起阴险的往昔 / 回忆起甜蜜的初恋。”相比于可触摸的现实,幽暗的过去变得更真实、更有生机。这不是一个随意之举,而是一个强力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加宁克服了对家园和爱情的失落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恢复了自我意识。正如他即将坠入万念俱灰的深渊之时,回忆像洪水一样冲刷他的意识,完全抹除了任何当下世界的痕迹,导致时空突然神奇倒置,“栩栩如生的过去使得现在变成鬼影憧憧”。加宁说自己就像“一个神,重新创造了一个已经毁灭的世界”;这并非只是在暗示他偶尔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逃避。这一目的明确的创造行为,不只是简单“复活”过去,更重要的,是从一闪即逝的意象和遥远缥缈的记忆中,“复活”一个可以触摸的心爱姑娘。回忆有一种仪式般的功能,有潜能带回那些一度似乎永远消失在时间的镰刀之下的事物。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从加宁(《玛丽》)和乔布(《乔布归来》)到亨伯特(《洛丽塔》)和珀森(《透明》),这些人物都设法用这种方式操纵回忆之力,只不过他们往往被刻画成误入迷途的悲剧角色,徒劳地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粗看之下,加宁放弃与玛丽的重聚,这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以此方式,他是在承认,重聚与否,与他当前的困境本质上并无关系。纳博科夫传递这一点是通过视角的重要转变,从而启动了一个平行时空的逆转。在去见玛丽时,加宁惊讶于清晨中城市街道的气息,似乎与他的回忆一样晶莹灿烂。这一幻觉的效力,使这个朦胧缥缈的世界——他的柏林、那些流亡者和他们的公寓——连同俄罗斯和玛丽,立刻不可逆转地抛给了幽暗的过去。最终获得自由的加宁,将他的目光转移到新的迫切的现在和令人激动的未知未来。
加宁在小说结尾经历的转变,折射出纳博科夫“脱胎换骨”的必要性。更为复杂的是,加宁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可以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多余人”相提并论。漠然、疏离、厌倦、失意、孤僻、非道德、愤世嫉俗和理想幻灭,这些经典特性,放在一个勇敢浪漫的冒险行为被当下的惰性阉割的时代,让同时代的俄罗斯流亡读者一眼就能将加宁认出来,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主人公,如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或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有趣的是,纳博科夫第一部重要小说的主人公是典型的俄罗斯人,但他在下一部小说中却立刻大胆地换了一帮德国人登场。似乎他是故意将“多余人”那些特性都加于加宁一身,连同他生活世界中的“贫穷”、“乡愁”和“人性的湿度”,统统抛在身后。
对于纳博科夫来说,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不只是将其艺术从个人历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要切断俄罗斯人都有的那种令人窒息的乡愁重负。借助加宁,纳博科夫展现了看待世界的新的方法,回忆不再是否定性的熵力,相反,却意味着解放和启迪。在短篇小说《语词》中,纳博科夫的叙事者竭力想说出他的悲伤,充分描述他心爱的俄罗斯,表达他巨大的损失,以便脱离苦海,但当他说到“最紧要的事”,却终究说不出口。在《玛丽》中,纳博科夫暗示这“最紧要的事”不再重要,还有其他方式解脱悲伤,重获快乐,不是通过复活幸福的过去,而是如加宁所示,将目光重新放在客观的当下,意识到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细节中都蕴藏着快乐。
纳博科夫早期的作品中一再强调视角的转换。在短篇《一封永远不会抵达俄罗斯的信》中,叙事者说他的幸福是“一种挑战”,抵消了他的孤独,是一种永在的力量,蕴涵在所有给他带来欢乐的事物中,如“潮湿反射的街灯,伸进运河黑水中谨慎拐弯的石阶,一对夫妻跳舞时的微笑”。同样,在1924年的短篇《仁慈》中,叙事者从拂过电车顶上的潮湿枝头的敲击声中获得了奢侈的幸福:
拉动响铃,电车继续前行,湿玻璃窗上掠过街灯的零星光点,我满怀幸福之情,企盼再次听到那温柔而短促的敲击声。
同样,在1924年的戏剧《莫恩先生的悲剧》中,尽管一生命运多舛,莫恩依然保持着他的奇迹感,即便别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绝望,他依然能够重新发现真正的幸福。
这种惊讶于俗世之美的能力——“对琐事感到好奇”——是战胜失落之痛的关键,克服死亡那武断的、混乱的毁灭力量。1923年的短篇《诸神》回响着一种死亡之后释放出的生命力。仅仅一年前,在纳博科夫为纪念父亲而作的那首诗中就包含了这种观念。在那首诗中,他父亲的灵魂回荡在小溪的水波里;在这篇小说中,那个孩子的亡魂在任何地方任何事物中都能被感觉得到。父亲的叙事或如他所说的“故事”,是为去世的孩子而作,他相信儿子能够听到他的话,因为他也相信,“语词没有边界”。他不能也不会分担妻子的悲伤,因为他在身边大量的事物中都能感觉到孩子的在场。要不是他的眼光完全没有偏见,无论是地铁里小灯泡钨丝发出的光,还是一块堆满垃圾的“枯”草坪,他都一视同仁,否则有人可能认为他纯粹是沉溺于痛苦或固执地拒绝承认事实。身边随便什么事物的奇异之美,使他相信“根本不存在死亡”,“不可能有死亡”,相反,它们包含了一种永恒的、普世的、肯定生命的正能量。“你和我将有一个新的金童,”他说,“他是你的眼泪和我的故事创造出来的。今天,我理解了空中交叉电线的美,理解了工厂烟囱那模糊的马赛克,理解了这个锯齿状盖子外翻、半脱落的生锈罐子。”
因此,视角微妙的变换,能够带来态度的根本改变。视角转变得益于敏感地重组细节,就像诗人的“多重意识”带来一种自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性。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见于1925年的短篇《打架》中“贪婪而敏锐”的叙事。两个打架的男人面对面站在街头,纳博科夫的叙事者冷眼旁观,“着迷”于“他们扭曲面孔上反射的街灯,着迷于克劳斯裸露的脖子上那紧张的肌肉”。 当克劳斯将对手打倒在地上时,纳博科夫留下叙事者考虑后果。叙事者想知道,他是否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事件,是否该把焦点集中在人身上,集中在遭受的痛苦,是否该显示出更多的移情和同情。但是,最终,他捍卫了纳博科夫的视角:
重要的不是人的痛苦或快乐,而是光影在一个人身上的变换,在这特定的日子、在这特定的时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细节组合在一起的和谐。
这一立场明显回响着柏格森艺术眼光至上的主张(“人是通过熟悉和陈规的胶片来洞察现实,但恰恰熟悉和陈规模糊了现实” ),但它也汲取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通过打破习惯性的视觉模式,打破认知期待,艺术能够揭示日常事物的美学价值和超现实品质)。 纳博科夫强调“陌生化”,也暗示了“彼岸”世界或“先前现实”的在场,让人想起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冲动,致力于揭示一种超验的本质,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66 纳博科夫早期作品中对这些观念的糅合,形成了独特的描写风格。比如,在1926年的短篇《剃刀》中,日常的街景被转换成某种轻盈流动的东西,焦点不是过客而是他们留下的身影:
人们一闪而过;他们蓝色的身影打破了人行道的边缘,毫无畏惧地滑过闪亮的车轮之下;在被阳光烤得软软的柏油路上,车轮留下了带状的印迹。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借助对情节、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描写的高明操纵,纳博科夫致力于探讨记忆、死亡和想象力等重要主题,探讨一个极度客观的、变换后的视角所带来的后果。接下来十年中,他将在各式各样的场景中试验和推广这些写作技巧,以至于它们成了他艺术内核中必不可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