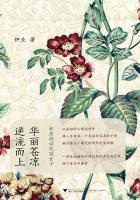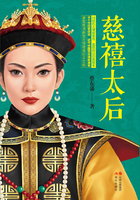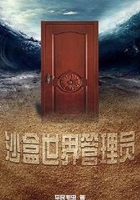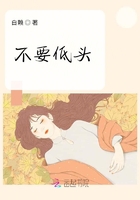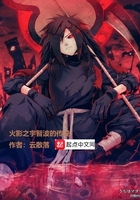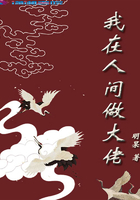纳博科夫家如天塌了下来。整个俄罗斯社群纷纷前来吊唁。复活节那一天,弗拉基米尔在《舵》上发表了一首新诗:“倘若所有的小溪把奇迹重唱……那么,你就在那歌声里,你就在那波光里,你就还活着。”回到剑桥完成他的最后一个学期时,弗拉基米尔写信给母亲,“有时太压抑了,我根本无法摆脱——但我必须隐藏起来。有许多事物和感情谁也无法发现”。
是年夏天一回到柏林,弗拉基米尔就向斯薇特兰娜·西沃特求婚。斯薇特兰娜觉得难以拒绝:他“看上去很可怜,很忧伤”。 她的父母同意了婚事,条件是弗拉基米尔要证明他有能力养活他们的女儿。他注定是要当作家,这点得到了验证:他开始了第一份工作,也是他最后一份工作,在银行上班,但只待了三个时辰,就草草结束。夏末,他得到一份委托,将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翻译成俄语,报酬是五美金。至今,他的译本仍然被认为是最佳译本。从1922年11月到1923年3月间,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他与父亲在1920年打赌的结果),出版了两部诗集(《天路》和《星团》)。但这不足以令斯薇特兰娜的父母满意。1923年1月,他们坚持要女儿解除婚约。对于刚刚丧父的纳博科夫来说,如此快就解除婚约,这份打击简直难以承受。他说,与斯薇特兰娜在一起,体验到的是“我曾有过或将有的最大幸福”。 为了疗治情伤,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从1923年1月起,他写了16首诗(其中包括一首850行的史诗),翻译英语和法语诗歌,创作了一个短篇《语词》和一出两幕剧《死亡》。他还在《舵》上发表了第一个棋题,在一部电影里跑了龙套。4月, 纳博科夫所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他在一个文学晚会上阅读了自己的作品,引起了三个姑娘的注意。他“面庞俊秀,才华横溢,魅力难以抗拒”。 好像特别有缘,他将很快与其中一个姑娘再次邂逅。
1923年5月,薇拉·斯洛尼姆在一场假面舞会上与纳博科夫相遇。两年多来,这个21岁的俄罗斯流亡犹太女孩一直在关注柏林文学舞台上最令人兴奋的一颗年轻星星的升起。当她在人群中认出他来时,就走到他身边,与他谈论他的诗歌,整个晚上一直神秘地不肯露出真容。三周后,纳博科夫在法国南部的一家农场打暑期工时,写了一首诗《邂逅》纪念这次见面。《邂逅》明显袭用了勃洛克1906年诗作《陌生人》的意象,并且从其《匿名者》中引了一行诗——“牵绊于这陌生的亲近”——作为题记。这期间,薇拉已给他写了好几封信。最终,纳博科夫回信说,“我不习惯别人的想法……你懂我的意思……在我们见面的开始几分钟,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玩笑,一个戴着面具的骗局”。
6月底,纳博科夫在《舵》上发表了《邂逅》(这是一次非常公开的示爱之举,薇拉正好也在为该刊撰稿和翻译):
渴望,神秘,快乐……
化装舞会上步态轻柔
仿佛从那浮动的黑暗中
你走上迷蒙的桥头……
我的心听到了什么
为何你如此让我心动?……
我向远方徘徊,仔细聆听
你我邂逅时星辰的运动
我想知道
要是你是我的命运又如何……
7月底,纳博科夫另一首诗作《歌声》与薇拉翻译的爱伦·坡短篇《沉默》并排刊登在《舵》上。这次,用一种明确的浪漫姿态,纳博科夫在诗歌的开头和结尾都用了俄语中“信仰”(Vera)一词。
这期间,除了创作出其他许多诗歌外,纳博科夫还完成了两部新剧(《祖父》和《极地》),游览了马赛(这次旅行给他写作短篇《海港》带来了灵感)。8月底,他回到柏林,揭开了薇拉的真面。他发现彼此已经见过多次。还是小姑娘时,她就经常路过他在摩斯卡娅大街的家,认识好几位纳博科夫在捷尼谢夫中学的朋友;少女时,她家在维拉附近租了一处乡间别墅度假;在柏林时,她还差点儿在父亲的奥尔比斯出版社的办公室撞见他,她在那里上班。立刻,他惊讶于他们有那么多相似之处,有身体的、感情的、智性的和想象力的亲密性可以分享,甚至薇拉也能看出“字母的颜色”48。 在他的诗歌里,她扮演着勃洛克早期诗歌中那个神秘莫测的“美丽女神”(纳博科夫和他的父亲对勃洛克的早期诗歌推崇备至)。他深信,他们是天作之合。1925年4月,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自1922年秋,德国开始遭受灾难性的通胀打击。许多流亡者纷纷离去。1923年10月,弗拉基米尔的母亲、两个妹妹和最小的弟弟移居布拉格。二弟谢尔盖去了巴黎。奥尔比斯出版社倒闭后,薇拉的父亲也破了产。纳博科夫被迫依靠教网球和拳击、做英语家教、接写作活谋生。他与朋友伊万·卢卡斯合作,为在柏林的流亡艺术团写小品,为芭蕾、歌剧和电影写场景和剧本。他甚至试镜当演员,一度认真考虑过要当影星。1924年1月,他完成了一出五幕诗剧《莫恩先生的悲剧》。在随后两年里,他又创作了15个短篇(此前,他已完成或发表了6个短篇)。到1925年11月,他正在最后修订他的第一部长篇《玛丽》。
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玛丽》的奇异之处在于,它明显包含了自传性的内容,如节选自五封瓦伦季娅·舒尔金情书的片段。四十多年后,当回顾这部作品时,纳博科夫对于当年“鲁莽”地暴露“个人真实”相当震惊。其中大段意味深长的回忆文字再次出现在他1967年的自传《说吧,回忆》中(描写塔玛拉的第12章)。尽管其间流逝的岁月并没有磨损他多少记忆,但在自传中纳博科夫还是漏掉了一些关键场景——“疗养,谷仓音乐会,泛舟”49。 纳博科夫最初定的标题是《幸福》,原作的一章曾经以短篇《一封永远不会抵达俄罗斯的信》的形式发表于1925年11月。两个月后,《玛丽》出版。这部小说得到盛赞。批评家尤里·艾亨瓦尔德赞扬纳博科夫是“屠格涅夫再世”, 认为《玛丽》“充满了生命、意义和精神”。纳博科夫后来说,写作《玛丽》,是为了“精心重构我那虚构但美丽而精致的俄罗斯”。将自身大量的过去岁月揉进主人公的历史,纳博科夫也将这部小说看成是“脱胎换骨、走向新生”的方式。
故事发生在柏林1924年4月的一周之内。在一家紧靠喧闹铁路干线的肮脏公寓里,一群身份各异的俄罗斯流亡者共同租住了几间狭小的房间,其中有列维·加宁(一个来历不明的文青)、安东·波特亚金(一个老诗人)和阿列克谢·阿尔费奥洛夫(一个中年商人)。他们共同的梦想是回到昔日的俄罗斯或进一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在压倒一切的漠然和令人窒息的绝望面前,他们的梦想日益枯萎。没日没夜呼啸而过的列车,永远提醒着他们已离开的那片大地,提醒着他们现在的这种中间状态,提醒着他们其他闪亮的但看来如此遥不可及的可能前景。波特亚金和加宁都迫切想离开德国。波特亚金梦想受阻,是因为他的各种证件还没有办好;加宁迟迟未能动身,是由于他的精神萎靡,消耗掉了一切激情。一天晚上,加宁偶然发现,阿尔费奥洛夫几天后就要赶来柏林的妻子,居然是他的初恋情人玛丽。这一发现勾起了他浓烈的乡愁和缠绵的回忆。在一个诱人但已失落的俄罗斯的背景下,他热烈狂喜地重温了他与玛丽的旧情。他决定在她到达柏林时半路拦截,于是在最后关头心生一计,阻止了阿尔费奥洛夫前去接站。然而,在他去见玛丽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主意,在另一个车站登上了一列前往法国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