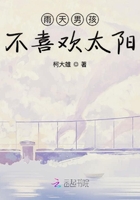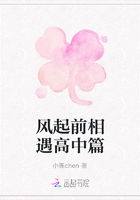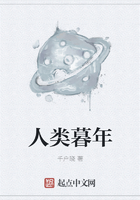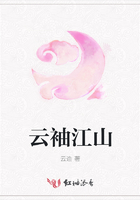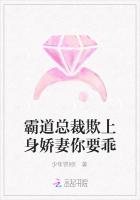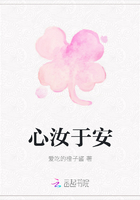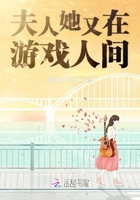一个作家传记的最好部分,不是他冒险的记录,而是他风格的故事。1
1926年秋,纳博科夫夫妇在帕索尔大街12号租下两间房,他们将在此住上两年。尽管他们在柏林期间多次搬家,但总是留在同一个区域,即新并入的夏洛滕堡区。该区以选帝候大街为中心,因大都会夜生活而著名。自世纪之交以来,柏林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又具堕落气息之都,吸引了一切创新和实验事物。慕名而至的有作家、艺术家(布莱希特、茨威格、格罗兹、迪克斯)、演员、歌手、舞蹈家、音乐家和作曲家(黛德丽、彼得·洛、林雅、贝克尔、库特·威尔、勋伯格),戏剧导演和电影导演(皮斯卡托、莱因哈特、茂瑙、维内、弗里兹·朗)。这个“新西区”成为柏林20世纪20年代文化浪潮的驱动力。其爆炸性能量进一步刺激并折射了一个压倒一切的、迫切的变革欲望。这种变革欲望表现于日渐动荡的社会和政治图景,先由毁灭性通胀点火,然后是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后金融风暴的火上浇油。一战之后紧随德国多年的政治动荡,如今再次出现。法西斯分子、共产主义者和警察在柏林街头暴力冲突不断。随着经济开始崩溃,失业人数火箭般上升。到了30年代初,德国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势力,几年前根本无任何政治影响力,如今真有可能掌握极权。
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俄罗斯流亡社群圈中的纳博科夫夫妇,远离了这些动荡。选帝候大街非常“俄罗斯化”,有俄罗斯人开的书店、咖啡馆、酒吧、餐厅和剧院(包括格罗茨街著名的蓝鸟艺术团,他们上演了纳博科夫和朋友伊万·卢卡斯写的小品)。来自俄罗斯文艺界的名人要么住在柏林,要么频繁光顾:如作家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高尔基、蒲宁、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舍斯托夫和什科洛夫斯基;戏剧导演和电影制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霍德、爱森斯坦;艺术家、歌手、舞蹈家和音乐家——夏加尔、康定斯基、查理亚平、帕芙洛娃、霍洛维茨和亚季戈尔斯基。1920年初,安德烈·别雷到访了夏洛滕堡后,说它是“昨日俄罗斯文化的温室”:
在柏林这一个区,你会见到多年没见的人,更别提经常碰到熟人;你见到莫斯科的人和圣彼得堡的人,见到巴黎来的俄罗斯人,见到布拉格、甚至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来的人;……如果碰巧听到有人讲德语,你会很困惑:怎么回事儿?德国人?他们在“我们”城市有何贵干?
纳博科夫在帕索尔大街租的房子下面就是一家俄罗斯餐馆,旁边的一道门是柏林最大百货商场(西方百货公司)的入口。顺着街再过几道门,就是西方图书大楼,里面有大量的俄文图书,经常可以发现纳博科夫在那里随意翻阅。3每隔一周,在不同的咖啡馆和公寓,他会参加文学圈子聚会。这些聚会是尤里·艾亨瓦尔德和赖萨·塔塔里诺夫发起的,阅读和讨论新作,包括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皮涅克、阿廖莎、格拉特考夫和左琴科的作品。纳博科夫也经常在俄罗斯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举办的读书会和慈善晚会上露面。尽管困居柏林,他甚至能间接地追求自己对鳞翅类昆虫学的爱好。1926年春,他开始造访达勒姆昆虫研究所的莫尔特雷奇。这位俄罗斯科学家“把蝴蝶知识讲得非常精彩、动人、浪漫”。这期间,纳博科夫在鳞翅类收集上的斩获却很少,只在夏洛滕堡火车站附近的树干上捕捉到一只十分珍稀的飞蛾。 他也有机会放纵另一大爱好,下国际象棋;在一次公开赛上,他先后与两个大师过招,其中一局对垒了四个多小时。是年秋,他接受了群众剧团的委托,创作一出新剧《苏联来客》,该剧在次年四月上演。他利用晚上写作,白天则为《舵》写诗评,做英语和法语家教,做网球教练。薇拉找了份翻译和打字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1926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然而,纳博科夫夫妇认为,柏林是“一个可怕的死胡同”。纳博科夫向薇拉抱怨,“听到德语就恶心”。 他们本打算在1932年底离开柏林,但在1933年,希特勒政权出台了第一个反犹法令,使薇拉成为潜在的迫害对象,他们依然没走。1934年,儿子德米特里出生。德国的局势让人“恶心”。与许多其他流亡者一样,纳博科夫“深信”,“十年内,我们都会回到一个好客的、充满悔悟的、各民族杂糅的俄罗斯”。
纳博科夫曾说,他“戴着太空头盔穿越生命”。他在自己的创作、个人生活和广阔的俄罗斯社群中找到了安全。有了这份安全,即便离更广阔的世界的忧愁只有一步之遥,他也能够生存。像他的流亡同胞一样,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幻”都市里,生活“在完全不重要的陌生人中间”,他们如同“剪下来的玻璃纸人物一样平面透明”。然而,这些平面透明的人物却能够带来“可怕的震惊”,赤裸裸地提示“谁是无形的俘虏,谁是真正的主人”。
尽管有那些“可怕的震惊”,但在一个“幽灵世界”的边缘生活,却非常适合纳博科夫。作为一个生活在异乡的异客,他体验到的被迫的疏离,对他来说无异于一份红利,因为“隔绝”意味着“自由和发现”。由于德国及其民众和文化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所以,没有对纳博科夫小心把守的自我构成威胁。他拒绝提高他“一知半解”的德语(那是他在1910年与谢尔盖一起待在柏林半年拣到的,或后来在学校学到的),拒绝阅读德语书报。同时,俄罗斯流亡社群也是自给自足,所以他也乐得不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瓜葛。
这种持久而净化的疏离感奇怪地与纳博科夫在其作品中已开始探索的对视角和身份之可变性的关注形成了互补。1926年的短篇《恐怖》标志着对这些主题处理的重大进展。以先于萨特存在主义危机的形式,它呈现了一幅完全卑贱而恐怖的场景,令人联想到托尔斯泰、舍斯托夫、帕斯卡尔、康德和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学或哲学作品。叙述者是一个年轻诗人,他描述了一系列亲身经历的事件。最初他体验到的是转瞬即逝的异化感,完全“不认识”自己了,接下来是那种夜晚对死亡的害怕,最后,是对另一个人近在咫尺的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惧。经历了四个不眠之夜后,叙述者的精神最终彻底崩溃:
失眠消失了,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我的头像是玻璃做的,腿肚子上一点点痉挛也有玻璃感觉……我与世界的交流线喀嚓一声断裂,我是我,世界是世界,世界没有任何感觉。
随着这种异化感的程度,真正的现实世界在他看来突然“以恐怖的赤裸和可怕的荒诞”出现——“我不再是一个人,我是一只裸眼,一个漫无目的的眼神,游荡在一个荒诞的世界”。就在即将堕入彻底疯狂之时,情人之死突然拯救了他。震惊和悲伤暂时抹去了一切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想法,但叙述者知道,他强烈的情感和对情人的记忆将褪色,他必将再次面对他“绝望而恐怖的存在”,到时“再也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
纳博科夫写作《恐怖》,原本是受巴黎一家流亡杂志《当代年鉴》所托。这个短篇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发表于1927年1月,它是纳博科夫第一部获得广大欧洲读者的作品。其二,它标志着纳博科夫创作中一次谨慎而重大的转折点,确立将成为其作品支点的主题和关注点。这些主题和关注点他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持续重访。
《恐怖》利用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处理了人类最敏感、最复杂的两个问题——疯狂与死亡。在1923年的诗剧《死亡》中,纳博科夫暗示,死亡带来的结果要么是“惊异”,要么“什么都不是”。 在1947年的小说《庶出的标志》中,亚当·克鲁格重复了这一观点。克鲁格说,死亡“要么立刻获得完美的认知”,要么是“绝对的虚无”。在《恐怖》中,纳博科夫的主人公说,
我们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没有我们就不存在,它存在只是由于我们存在,由于我们能够再现它;我们从这样的想法中获得了慰藉。死亡,太空,银河系,它们之所以恐怖,恰是因为它们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局限。
通过挑战“认知局限”,直面恐怖的事物,纳博科夫的主人公冒着疯狂的危险,但仍然没有希望解决困境。他被给予的唯一希望,是让他爱另一个人,然而,在毁灭面前,他的爱被证明是短暂的、脆弱的。不过,这个故事是“纳博科夫第一次在小说中努力阐明爱作为一个平衡点,对抗宇宙的恐怖,对抗这陌生化的世界”。 此外,它引入了一个纳博科夫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永远震荡动态,摇摆于死后两个可能的图景之间。一方面,“我们的生存”可能“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 另一方面,纳博科夫作品中对“彼岸世界”的描述削弱了生而有涯的观念。此外,这种理解力——“把我们的存在状态跟那些我们在少有的非理性感知时刻朦胧理解到的其他状态和方式联系起来”——是与创造性密不可分的。在1940年抵达美国之后最初的一次开讲中,纳博科夫阐明了这点:
在世的生命不过是灵魂序列的第一级;一个人的秘密并不随着尘世生命的解体而丢失,它变成了乐观猜想之外的东西,甚至不只是宗教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只有常识才将不朽排除在外。一个创造性作家……不由自主会感到,拒绝这个现实世界,站在非理性、非逻辑、难以解释和本质上是善的一边,他就是在以原始的方式表演某种东西,类似于人们期待灵魂可能的表演,只要时机来临,在一个更大的、更满意的层次上。
尽管伤悲挽救了《恐怖》中的叙述者陷入疯狂(哪怕只是暂时),但在别的地方,它却威胁着摧毁悲悼者。在早前的两个短篇《乔布归来》(1925)和《扑棱》(1923)里,两个主人公都是突遭丧妻之痛:乔布的妻子因偶然触电身亡,克恩的妻子是自杀。为了摆脱痛苦,两人都求助于极端方式:克恩决定开枪自杀,乔布试图重新体验他们短暂蜜月旅程的点点滴滴,建构一个“不朽的”意象来取代亡妻。然而,部分复活过去的过程最终证明是亦喜亦悲。乔布努力的结果是近似于将妻子的亡灵注入一个妓女的身体,他付费让她一起睡在洞房之夜的婚床上。反讽的是,他事与愿违。夜里醒来,他转向躺在身边的妓女,以为她就是亡妻复活。他开始“恐怖地、撕心裂肺地”尖叫,发出“阴森的长嚎”。震惊之下,他最终矫情地摆脱了痛苦的“煎熬”。
《扑棱》中的克恩在经历了“疯狂的七年之爱”后失去了妻子。妻子的死带来了一个永远虚无的“深渊”,“吞没了一切”。他们在一起的幸福压缩成了一块“碎片”,粘在“他用来屏蔽宇宙气流的一排摇晃的彩色玻璃”上;与别的碎片一样,“在外面的风中翻腾,逐一吹落”。这最后一块碎片的失落削弱了他“从那未知、从那旋转的天空逃脱”的能力。经过半年“迟钝的忧郁”,他冒险前往采尔马特的滑雪胜地,但那里“醉醺醺的”、“轻松”的气氛没有提供任何慰藉或转移他的注意力。尽管在那里遇见了英国姑娘伊萨贝拉,克恩还是犹豫地选择了自杀——“在他看来,死亡就像一场滑翔的梦,像羽毛一样降落。心如止水,没有慌张,没有疼痛”。 但是,在决定跳入那“深渊”时,他不经意间释放出超自然的力量,感觉到更贴近他世界中的那些脆弱的屏障,它们以一个堕落天使的面目出现。再次,有意行为的拟想结局证明很不可预测,因为那天使要找到的人不是克恩,而是伊萨贝拉。受到莱蒙托夫经典诗歌中的魔鬼所启发,纳博科夫笔下的天使勾引了伊萨贝拉;天使怀疑伊萨贝拉背叛了他,所以在克恩打算自杀的那天将她毁灭。
纳博科夫早期小说中对超自然的召唤同样表现于另一个写于1924年的短篇《娜塔莎》。在柏林一个狭窄的公寓里,赫列诺夫得了绝症,由年轻的女儿娜塔莎照顾。她是家中唯一在移民之后幸存的亲人。虽然筋疲力尽,但她毫不畏缩,依然悉心照料父亲,满足他的任何要求。她似乎在保守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防止她陷入悲伤。她告诉邻居,她有灵视,但又立马说那是幻觉。然而,在故事结尾,她的灵视得到证实:她在街上看见了父亲,并和他说了话,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死了。在产生这种灵视前,她感受到了光和热,让人想起纳博科夫小时候的神智失常:
娜塔莎像被风帆推动,她的疲惫像在支撑着她,给了她翅膀,使她轻飘飘地没有重量……她觉得自己变得很虚弱,那股默默的热浪在沿着脊背穿梭。
尽管娜塔莎将这种轻飘飘的、梦一样的感觉与疲惫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它暗示了一种存在状态,使她进入另一个空间——阴间,只不过这阴间不像克恩的深渊,是仁慈的,不让人觉得怕。赫列诺夫的幽灵面含微笑,温柔善良,和蔼可亲,完全有别于乔布亡妻复活的可怕场面。
从他早期作品中明显出现的鬼魂、魔鬼和亡灵复活,到他晚期作品中更谨慎但同样可感觉到的“彼岸世界”的存在,纳博科夫对超自然的处理,是他一生创作中表现死亡和来生主题的核心。事实上,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主题”。在为1979年纳博科夫去世之后出版的俄语诗集所作的序言中,薇拉确认了这一点。她说,彼岸世界“浸透了他写的一切”。 纳博科夫首次讨论这个术语是在1922年论鲁伯特·布鲁克的文章中,他写道,“从来没有诗人像布鲁克一样,用那样纠结而创造的眼光洞察彼岸世界的薄暮”。 这篇文章认为,布鲁克诗歌中的一些元素可视为强烈的表现符号。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利用它们(“轻柔、林荫、透明气流”)来象征“彼岸世界”的在场。布鲁克断言,死亡“只是一种惊奇,一个意外”,抢先说出了纳博科夫在1923年戏剧《死亡》中完全相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