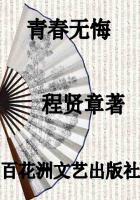三日之后,花山祭台,牯葬祭祀。
南越虽是蕞尔之地,可“祀与戎”亦备受推崇。望月教有“牯葬”一说,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杀生人及牯子牛供神飨。
祭台层层突起,中心是一四方台,高有万仞,直入云霄,一方长阶从花山坪顶延展,直没云端。
吕锦绣傲立祭台高处,红衣绽如火,眼角点上朱红泪痣,眼眶勾出红黑纹理,左右对称,直勾入眉,双眼亮如黑曜,身形魑魅。
一夕之间,她已不再是三日前灵动孩童。众白衣弟子围坐其左右,凝神聚气。几位着黄袍戴金圈的彪形大汉围坐外圈,身形魁梧,面露凶煞。
我立于红衣长老身侧,大风吹拂,身姿飘摇,足下为深渊归墟亦作“归虚”,出自《列子·汤问》,传说为海中无底之谷。祭台高处竖着两大支架,空空落落。在匈奴之时,我也曾被吊在祭台上头,万人垂涎,等待生祭。
支架上此时无人,祭祀神圣,不可暴露于外,当藏于暗处。支架上设有滚轮,祭时一到,祭台下方机关松动,牲人会从祭台暗格处升出,直至支架最高处,被紧紧锁死。
身着白衣的吕锦汐教主统领教众拾级而上,教中各派长老尾随其后,陈耳身形挺拔,在阵中格外凸显。
红衣长老仁厚,让我毫发无损,可这三日间,吕家姐妹对陈耳有何大动作,我不得而知。
待及近处,我看得清些。陈耳紧随吕锦汐身侧,青衣白衫飘拂缱绻,交缠错综。高处瞬息万象,陈耳却神色如常,我双手不由得轻握成拳,难以淡定。
他望了我一眼,目光逼人。
牯葬,以“牛牲”为始。几头牯子牛被拉至高处,惨叫不迭,祭台符箓之上猩红一片,大牛顷刻被放倒在地。
祭品落定,七法师分次列位,或摇编钟,或手持符咒,或催动五毒,各司其职,转而围着祭台轮转,口中念念有词。吕锦绣正襟危坐,主导整个祭祀大典。
鼓笙交响而起,苗家汉子不时发出呼喝,祭台上声音响彻,撼天动地。吕锦绣紧闭的双眼蓦地张开,双目炯炯,亮如豹睛。
祭台上浩歌四起,壮阔激烈,如临沙场,四面皆是楚歌,十面皆是埋伏。场下诸人齐刷刷仰头望去,大支架上已升腾起二人身影,衫布明晃,抖动招摇。
当那低垂的两个身影晃入我眼帘,我惊得跳起身子,步履不稳,险要跌倒。
“不!”我吼叫着冲出阵中,往祭台中心奔去。
“织艳,去病!”我疯狂喊叫,才冲出几步,便被人拦下,打横扔在地上。青衫一角恰好漂浮至我面上,本是柔软的帛布,却刺得我面颊生疼。
“陈耳!”我咬牙切齿,抓过他的衣袍,使力拉扯,声声控诉,“为何你要如此残忍,言而无信,背信弃义?”
他未有反应,倒听得他身侧吕锦汐呵斥道:“锦绣!”
“这可使不得,锦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红衣长老已至我面前,挥开阻挡我的苗人,对着吕锦绣义正词严道,“绣丫头,你这样做,可是死罪!霍织艳可是南越太子妃,去病更是婴齐太子独苗,你怎可……怎会将此二人用作生祭?”
我立直身子,陈耳伸手持住我的胳膊,逼我视他。我胳膊生疼,咬着牙瞪他,恨不得将自己肩上痛楚加倍奉还于他。
“你这无耻小人!”我甩手一巴掌,稳稳落在陈耳面具上,银鹰面具纹丝不动,我的手心却被划出一道不深不浅的口子。
“丹心!”他唤我,我愣神。思及织艳、去病,我硬生生抽回手,越过众人,翻身又上了祭台,来至祭台顶上。我晃动祭祀架子,四处摸索,想寻着机关,放他们母子下来。
又有人欲阻挠我,却被白衣教众制止。我正急切摸索,忽听得吕锦绣一句:“将他们放下!”
未等我回神,织艳与去病已从高处落下。我眼睛模糊,只看着两黑点凝成一团,迅疾坠落。我赶紧扑上前去,抢先接过去病,抱在怀中滚了一圈才稳住身子,而织艳则生生栽倒在地,伤了筋骨。
“阿姐,锦绣自八岁习蛊,十二年来,自觉南越再无敌手。”吕锦绣毫不退让,逼视姐姐,“你可信妹妹一次,妹妹要当着长老们的面,当着护法们的面,亲自布蛊,让你们看看这两人,究竟是何妖孽!”
“去病!”去病手足酥软,神志迷蒙,我搓着他的额头,极是担心。
“丹心!”我恍恍惚惚听到织艳喊我,转头见她挣着从地上坐起,一时百感交集,一手抱过去病,一手拉过她。
“去病!”织艳抚过去病脑袋,往额间一探,启声,“还烧着呢!”
去病眼睛睁不开。想起支架上漂浮的两点,我又怒又悲,心窝被刺得生疼,一时血脉贲张,望向吕锦汐身侧陈耳,努力压抑自己,方忍住要暴揍他的冲动。
正当此时,吕锦绣手下之人要夺落于平地的去病和织艳,我正恼羞成怒,冲着来人就是一拳。
“不要动去病!”去病被人按压,难受地咳出声来,我不顾来人多少,对着便狠打一通。
我显是敌不过,一头摔在地上,意识模糊。
吕锦绣向织艳走去,轻轻揉捏织艳腹部,我被压制,只能咬牙望着。
她又走向去病,大红衣袖中伸出一只套着黑网的手,摸向去病肚子,一只红色蜈蚣若隐若现。我心一凛,清醒大半,果真看着毒蜈蚣爬上去病肚脐眼。
我心提到嗓子眼,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去病受苦,去病身躯扭动,巴掌大的脸上眉头紧成一团,我痛心不已,恨极吕锦绣!
去病肚脐上出现一排青黑色蜈蚣爪印,他咬牙闭眼,虽是痛极,可并不呼喊。
吕锦绣取走蜈蚣,蜈蚣再经她的手,竟褪去紫红颜色,通体晶莹剔透。她将蜈蚣放入祭台正中玉盅中,玉盅中盛满清水,蜈蚣入了水,翻腾身子,宛如游鱼。
“盅中所注为皇陵之水。”吕锦绣望向吕锦汐,颇有讥讽,“当日父亲求而不得的续命之物,此时正在我手心,可又能改变些什么?晚了十二年,我早已长不大,姐姐命数也当定下,何苦改命!”
“锦绣!”吕锦汐喊着妹妹。
“各位长老想必已猜到,锦绣方才布的是鱼蛊!”她转眸轻笑,把握十足,“此蛊需母子配合才可施布。我取瓶山大蜈蚣引来这孩子骨血,再将蜈蚣放入皇陵水中,若皇陵水能葆清澈透亮,虫子如游鱼游弋自如,母亲腹间出现的是顺鳞,那他便是皇子正宗,锦绣便再无异议,自当尊之敬之。”
“若不是,那又如何?”黑衣护法切问。
去病是霍织艳与刘荣的孩子!我攥紧拳头,屏住呼吸,却见玉盅中水清无浊,蜈蚣触须灵动,实在不解。
“如此看来,当无异议!”红衣长老仔细查究玉盅,道。
“步尘长老还当查探霍织艳!”吕锦绣显是不甘。红衣长老顺着她指引走向霍织艳,蹲下身子往霍织艳腹间查探,安详面上脸色霎变。
“逆鳞!”红衣长老瞪着眼睛,拉过吕锦绣,“这自相矛盾……绣姑娘……这当如何评判?”
“子依于母,如尘归于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是该看霍织艳腹间蛊相!”吕锦绣此言一出,几位护法也上前察看,皆垂首懊丧,人群一阵骚动。
“当作牯葬!”四位护法脸色苍白,怒气冲天,武断决意。
“皇陵泉水所示本乃天命,可霍织艳腹间所布蛊纹,可人为之,若有人暗中诬蔑,霍织艳母子岂非枉死?”说这话的是陈耳,他不知何时已站在霍织艳面前,拦下欲动手的黑衣护法。听得他坚定言辞,我竟觉心安。
“霍织艳琴技卓然,声名远播,锦绣远在南越,也久闻其名,姐姐更是仰慕不已。霍织艳与大汉前皇太子刘荣斗琴之佳话,也是她告与锦绣的。姐姐,我可有记错?”吕锦绣极是狡黠,虽话音稚嫩,知晓却是甚多。
“确实有过。”吕锦汐并不否认。
“如此看来,那霍织艳与刘荣关系可是非同寻常了!”吕锦绣笑颜魅惑,我听得心口怦怦直跳,这个秘密怎可经由一苗疆外人和盘托出!
我挣扎着要冲上去,无奈被人死死按压,动弹不得。我喊着去病名字,他烧得极重,意识模糊,不能应答。
“之所以清水澄清,未现浑浊之象,那是因为此孩童……”吕锦绣直勾勾盯着霍织艳,山鬼扮相极是骇人,“承天子龙气,是皇家血脉,皇陵之水,合乎于他,并无稀奇!”
“教主及众长老们,如今两越交戈,大汉朝却派兵相助东越,如此打压我南越,又岂是仁义之道?”听她之言,吕锦汐亦说不出半句辩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