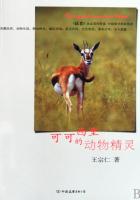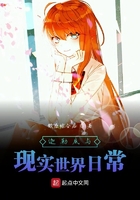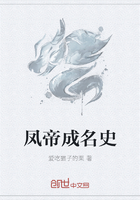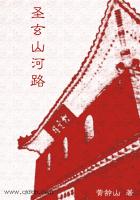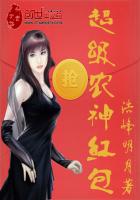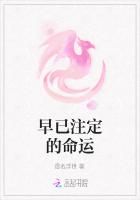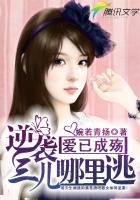为了和平,她们走向战争。女性是世界的一半。当女性投入战争的一方时,就意味着另一方已经离失败不远了。
——笔者手记
延安女子大学仅仅存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它的学员并无固定的学习期限,只要斗争需要,一声令下,这些热血女儿就打起背包,奔赴战火纷飞生死莫测的疆场。
生儿育女,是妇女的天职。母爱,是人类最动人最伟大的情感。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血缘联系,该是怎样的难以割舍呵!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紧张,既不具备生孩子所必需的相对安定的环境,孩子生下后也不具备最起码的抚育条件。因此,生养孩子就成为战时妇女最头疼的问题。为赴国难,为救危亡,许多延安女性毅然决然地挥泪与襁褓中的孩子告别了。
李昭——抗战胜利后,胡耀邦即将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李昭要求同往,可刚生下来的第二个孩子怎么办?夫妻俩决定把孩子交给陕北老乡刘世昌抚养。耀邦对老刘说,从现在起,老二就是老区人民和刘家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由你取。刘世昌沉思片刻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耀邦笑着说,那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还是湖泊的“湖”好。13年后。这个孩子才被接到北京。
汪涛——生有五个孩子。解放战争中,因要随大军南下,刚生下的第二个孩子送人了。建国初期,因丈夫无端受高岗事件牵连,由公安部门“监护”并停发工资,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刚生下几个月的女儿也被迫送人。后来两个孩子在养父母的精心抚育下读了大学,与生母联系上以后,听了自己的身世,不禁悲从中来,但也只能对母亲的做法表示理解了。
倪冰、程迈——这两位因全身心投入革命和工作,第一个孩子都因病死亡。程迈的孩子生在冬天,窑洞里太冷,她挣扎着起来到女大食堂拣煤核儿,回家后发现孩子已经冻死了。
刘沏——在北平读高中时结了婚,有一个孩子。后来她把孩子带到延安,交给老乡代养。在陕北那样穷苦的地方,老百姓尚且难活呢,不久孩子便因病死亡。
夏革非——生在延安的第一个孩子因营养不良,身体极弱。躺在土炕上时,嘴边黑糊糊落了一层苍蝇,一呼气便飞走,一吸气又飞回来。她总担心苍蝇会被孩子吸进嘴里,后来这孩子果真患急性痢疾死去。
张煜——女儿生下第3天,她就和丈夫苏民奔赴延安,把这个女婴托付给大哥家代养。建国后回去找,孩子已经丢了。自此,苏民每次乘火车,都要从第一节车厢走到车尾,仔细辨认每个女孩。他坚信自己能把女儿认出来,但一直到死也没找到。
黎莎——生下第一个女儿以后,她怕影响工作,咬着牙把这个女婴送了人。丈夫回来后问孩子呢?黎莎说送人了。送谁了?丈夫惊问。黎莎说送谁谁了。丈夫闷坐了一会儿,默默走出去,不大工夫,又把女儿抱回来。后来黎莎生的都是男孩。现在黎莎常夸自己的女儿怎样怎样好,女儿说,你还夸我呢,要不是当初我爸把我抱回来,我还不知道是谁家的呢!
陆红——她和徐以新结婚一年后怀了孕,因担心拖累个孩子影响工作,她从早到晚猛跳猛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但这孩子比她还坚强,不仅顽强地挺住了,而且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直茁壮成长到今天。
黎侠——她说,那时我们这些女性的革命热情太高了,已经到了不顾一切、不要一切的程度。在苏联学习时第一次怀孕,她想,国内正烽火连天地抗日,自己怎么能拖累个孩子呢!她不想要,于是走路连跑带跳,上下楼梯时也直蹦,但毫无效果。临产期到了,李立三派人护送她到医院。黎侠花言巧语把陪同的伙伴哄走,她一猫腰钻进厕所,锁上门,坐在抽水马桶上。她想,孩子生出来,如果是死胎就顺马桶冲走,如果是活的就偷偷送人。就在这时,她疼得昏倒了。
黎侠不知道,慌忙之中她进的是男厕所。外面几个男的急着解手,进不去门,觉得有些蹊跷,赶紧搬来一架梯子,才发现黎侠已经昏死在里面。
孔筱——1947年,在黑龙江省讷河县生下第一个孩子,十几天后就冒着风雪严寒,跑出去做妇女工作,到处讲课做报告,整个“月子”的营养只是吃了一斤鸡肝算是补补身体,而这个孩子竟然活下来了。1949年冬天,她在辽宁生下第2个孩子,接生的同志是临时拉来的,不懂,把婴儿往桌上一放,就手忙脚乱地照料孔筱。回头想起孩子时,孩子已经冻青了,但还是活了下来。接生人走后,孔筱又渴又饿,看到房角放着一箱冻苹果,便挣扎过去啃了一个。一会儿工夫肚子便痛得她通身冒汗,满炕打滚儿,从此她一生不再吃苹果,伤了。
董边——1944年生了第一个男孩,长得与丈夫田家英一模一样。那时延安很照顾妇女,生了孩子就可以当家属,不工作。可董边不肯当家属,决定把孩子送给同住一个医院的一户农民。那个农妇连生了3个孩子,都夭折了,见了这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儿,非常高兴,但一定要董边立个字据,以后不许来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母子之间也相互知道了消息,可董边为信守诺言,连孩子的面都不能见。
王紫菲——她说自己一生最怕生孩子,所以只生了一个。可投身革命的弟弟等亲友牺牲了,她义不容辞地把他们留下的孩子都揽到自己家里,结果一下养了五个。
张光——她有5个儿子,号称“五虎将”,乳名分别叫特虎、大虎、二虎、三虎和四虎。1995年我们去采访时,张光笑着对我们说,他妈的这辈子就想要个姑娘,结果生了这么多臭小子(其实这5个“臭小子”都很优秀,90年代时,特虎是海军青岛舰队政委,大虎是某部门服务公司总经理,二虎是云南省副省长,三虎和四虎也都勤勤恳恳从事着自己的专业)。我们对张光5个儿子的排列顺序有些迷惑不解,问她老大为什么叫“特虎”。张光说,1941年,她和第一个丈夫韩钧生了大儿子,为一心一意抗战,就把孩子送老乡了,建国前后又连生两个,分别叫大虎和二虎。韩钧逝世后,张光与第二个丈夫佟铣又生了两个儿子,取名三虎、四虎。过了许多年,大儿子被找回来,可顺序没法改了,只好把老大叫个“特虎”。
邓涛——1945年随军开往东北时,任务紧急艰巨,只好把儿子丢给延安老乡抚养,半个世纪没有消息。1995年春节,已是古稀之年的母亲和年逾半百的儿子才得以相认,母子相拥,悲喜交加之情难以言表。
采访中,这些延安女性回顾起自己做母亲的经历,无不内疚地说,她们对不起孩子,几十年来对孩子关心照顾的太少了。孩子们也都埋急她们“只管生不管养”,“妈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长大的”。可她们说,那时我们光顾闹革命了,哪有时间顾孩子啊!
李宁——著名革命家李克农的女儿,延安女大学生,建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公安厅长。她回忆说,在她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闹革命去了。家里生活十分贫寒,全靠母亲赵瑛含辛茹苦做小学教员才得以维系。母亲处事妥贴庄重,待人和蔼,连李宁的爷爷都尊敬地称她为“赵先生”。父亲离家11年以后,一天,已经18岁的李宁见门口来了一个男人,以为是收税要钱的。她赶紧回身去找爷爷。爷爷走过来,那男子咧嘴笑着说,爸爸,我是克农。
尽管历经11年的长离别,但父亲李克农这次回家只坐了1个小时,建国后,母亲因病去世,在追悼会上,父亲满怀敬意和歉疚之情,称妻子为“母仪典范”。
母亲,可以是坚强的战士。战士,很难做称职的母亲。延安女性就是一群无法尽职的母亲。
现在,我们来看看她们是怎样的战士吧。
谢雪萍:她只能以泪洗面
走,走,看女儿去!部队刚安顿下来,正在埋锅做饭,谢雪萍就催着丈夫张学思快走。天还下着绵绵细雨,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要能找到一块干燥地方,躺下就睡了,他们太累了。但谢雪萍看孩子心切,饭都顾不上吃了。时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中军区参谋处处长的张学恩向司令员吕正操告了假,夫妻俩骑上马,飞一般朝十多里以外的一个村落赶去。时值1942年初秋,冀中平原上的青纱帐无边无际,摇曳着海洋般的喧响。连续十几天的秋雨,大地几乎成了水乡泽国。两人渴盼早早见到女儿,心急如火,冒雨策马狂奔,马蹄溅起一路水花。
还是去年秋天,谢雪萍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两口子心爱得不行,给女儿起名叫德华。不久,敌人开始疯狂的大扫荡,部队天天转移,夜夜行军,有时一个晚上要换两三个地方宿营,两口子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照料孩子。而且部队常常要在敌人炮楼、据点的缝隙之间穿过,人不许出声,枪械不许相碰,马蹄要包上破布或稻草,孩子要是万一哭出声来,就会暴露整个部队的行动。商量再三,两口子决定把女儿委托给根据地一家姓张的老乡代养。历经一年多艰苦卓绝的转战,敌人的大扫荡被粉碎了,军区部队又回到原驻地。
想到女儿已经1岁多了,不知长成什么样子,谢雪萍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一路上,湿凉的军衣贴在身上,她似乎毫无感觉,一边策马疾驰,一边大声跟丈夫猜测着女儿长得像谁,女儿大概会挪着小脚丫走路,会扎撒开小手朝爸妈怀里扑,会呀呀学语地叫爸爸妈妈了!
前几个月,部队一举拿下石佛镇,全歼从伪“满洲国”调来的一个“皇协团”,他们都是东北人,但穿的是日本军服,不少人镶金牙说日语,祸害老百姓与日本鬼子一样凶残,老百姓恨得他们牙直痒痒。谢雪萍随部队进了镇子,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买了一块花布。
那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已经遥遥可见了,张学思马快,最先冲进村子里。浑身透湿的谢雪萍刚驰进村口,就见张学思突然调转马头,拦住妻子说,走吧走吧,别看了!他的脸部痛苦得扭歪了,眼睛充满血丝,声音都颤抖了。
谢雪萍心里一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突变,不顾一切拍马冲过去。面对眼前的惨状,她猛地勒紧缰绳,马的前蹄腾空而起。村子北头那几十间民房已经成了黑鸦鸦的废墟,残垣断壁,满地瓦砾,杳无人迹。一声长长的哀哭,从谢雪萍的心底发出,泪水和雨水淋漓在脸上,混成一片。张学思赶紧拍马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妻子。他的嘴唇咬出了血。
1943年秋,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启明又降生在日军残酷的大扫荡之中。这次大扫荡,丧心病狂的日伪军调集了10万兵力,在八千多个村庄和六百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密布了一千五百个据点,修筑了一万多里网状公路,出动了七百余辆军车,冈村宁次亲自乘飞机往返指挥,对我根据地“划片分区”,反复“清剿”,妄图将我冀中主力一举歼灭。情势如此严峻,战事异常残酷,张学恩要谢雪萍留在野战医院,不要再跟着主力部队南征北战了。
冀中大平原狼烟四起,吕正操率领冀中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在敌军的“清剿”中迂回穿插,玩起了“捉迷藏”。国民党高级军校毕业的张学思本来就有深厚的军事素养,又经多年实战,已经成为司令员吕正操足智多谋的作战高参。那是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天刚蒙蒙亮,大部队猛插进距威县15公里的掌史村,悄悄隐蔽下来。饭刚刚做熟,村口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稍顷,侦察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方才来了30多个敌人,被我们的前哨报销了一半。
吕正操火了:乱弹琴,怎么能随便暴露目标!
张学思沉思片刻说,从敌军只出动30多人看,他们还不摸我们的底细,尚可补救。军区首长们经仔细分析,认为敌人只是与我偶然遭遇,还不知道这里隐蔽着我大部队和军区机关,现在天已大亮,转移会完全暴露,不如坚持到天黑再设法突围。
张学思所率参谋处对即将面临的战斗提出预测:离此地最近的敌伪一线兵力不过七八百人,打到中午,敌二线兵力可增至上千人,打到天黑前,敌军最多能集中三四千人。而且敌军由于全力进行“全面扫荡”,各据点之敌只有守备力量而无机动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对付。
战斗果然按照参谋处的预测展开了。敌人完全不知道这个村子竟然隐蔽着我数千人马,一开始只纠集了二三百人前来报复。这帮家伙当然是“小菜一碟”,一阵猛打便抱头鼠窜了。于是敌军不断从附近据点调集兵力,五百,八百,一千七……
我方故意逗弄敌人,先是“零打碎敲”,等敌军走近了再狠揍。仗打了大半天,敌人始终没有出动飞机,也没有高级指挥官统一指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夜里10时,我大部队的重武器一起怒吼了,弹雨飘泼般泻向敌阵,随着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数千战士犹如自天而降,冲杀出来。敌人惊呆了,他们作梦也没想到这个只有二三百户人家的村庄,竟会藏着这么多八路!此战,我军共歼敌五百余人,我仅伤亡46人,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1943年的大扫荡依然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军拔除敌军200余处堡垒,平毁上百公里的封锁沟,炸毁敌人12列火车和500多辆汽车,毙敌1万余人。1945年3月,已升任晋察冀军区十一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张学思满怀胜利的喜悦心情,兴冲冲回到根据地的家。一进门,他发现妻子满面泪痕,默然不语。转眼一看,女儿小启明不见了。
孩子呢?他惊问。
谢雪萍猛地扑进丈夫怀里,放声大哭。张学思这才得知,半个月前,小启明突患急性肺炎,因无药医治而夭折。
战争接连夺走他们两个孩子的生命,年轻的母亲回天无力,只能以泪洗面。大丈夫有泪不轻弹,这次,张学思也泪如雨下了。
杨汉秀:杀回“杨氏泽庐”
飞机穿过浓重的雨云,一直升高到云层上面的万里晴空。一位身穿湖绿色旗袍和白色绒线外套的清秀女子依在舷窗旁,沉浸在纷纭的思绪里。坐在前座、同机赴重庆的周恩来正同军调处的美方代表谈论着什么。
离阔别多年的家乡愈来愈近了,杨汉秀的心境也如同机翼下波翻滚的云海,久久不能平静。
自到延安以后,她先在女大学习,后又考入鲁艺学习美术。不想在“抢救运动”中,因出身于大军阀杨森之家,遭到无端怀疑,先关押,后是“控制使用”,直到朱德从前线回来,为她的事发了脾气骂了娘,汉秀才解脱出来。但被列入“怀疑对象”的阴影,依然像一条尾巴似地紧紧跟着她,并长期被排斥在党组织的门外。作为战士她渴望信任,做为母亲她深深思念着孩子。她的心情压抑极了,她要求去前线,只有在那里捧出带血的心,才能证明她的忠诚。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宣传,演戏,唱歌,当美工,在灼热的焦土和硝烟中抢救伤员。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她和战士们一样,把军帽高高地抛向空中欢呼雀跃,漫山遍野一片欢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