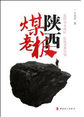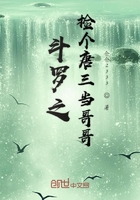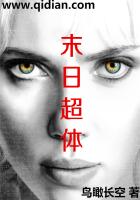1950年9月,甘露再次强忍悲痛,同意与萧三离婚。中央给了萧三口头警告的处分。1987年5月24日,甘露在北京溘然长逝。她的生前友好、著名画家黄苗子题写了这样的挽联:“声播蚕桑女,名扬花木兰。”
在延安的人生风景线上,发生了一些像严昭与S、吕璜与陈泊、萧三与甘露等等这样一些婚外恋情,并不奇怪。人生和人世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曲折和意外。这毕竟是那一代仁人志士当中,极少数个人命运发生的曲折和波澜。采访之后,我们细细想过,那种风云激荡的喋血时代、生离死别的人生,那种时时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煎熬,那种独往独来的孤寂,使得这些志士的生命张力和心弦常常处于绷得极紧的状态。任何一点小小的拨动,都可能使那颗心发出强烈的震颤和回响。天各一方、生死难测的离别与偶遇,漫漫烽火路上的一见钟情,随时准备战死沙场、渴望获得一点温慰的情缘,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希冀获得一点柔情的事情,很难完全避免。
他们和她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和杰出的革命家,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就让他们和她们有血有肉地活在我们的记忆中罢。这无损于延安的光辉和那一代革命者的伟大,同时也透出延安女性的美丽与坚忍。
对于面对死亡的战士,我们什么都能理解。
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0世纪30年代,陈嘉庚已成为南洋著名华侨领袖。
1940年,二战正酣,希特勒的军团在欧洲大陆上长驱直入,各国防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连崩溃,中国半壁河山已经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抗战打得十分艰苦。爱好和平的人类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侨界都忧心如焚。
在世界的东方,反法西斯的正义之战结局如何,主要看中国了。
就在这时,中国却不断传出国共两党发生“摩擦”的消息。蒋介石政府还向海内外散发了一份关于陕甘宁边区“摩擦”情况的报告。民族命运危在旦夕,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类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还是屡屡发生。
祸起萧墙,海外侨界深感震动,各地筹赈分会纷纷提请南洋华侨总会派代表回国考察,实地看看,究竟是谁的责任。此事非同小可,一般人物肯定难以胜此大任。此时陈嘉庚先生已届67岁高龄,腰病又很重。但为着国家之前途,他慨然说,还是我去吧,我要亲眼看看国共两党究竟是什么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团结抗日?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先生率慰问团飞抵重庆。
国民党政府深知陈先生在海内外的影响和威望。他数十年来侨居南洋,依靠自己的惨淡经营,成为名扬中外的华人实业家和爱国教育家。辛亥革命时,他帮助孙中山先生呼号奔波,积极募捐,致力于民族民主运动,后来独资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中学、小学,为普及家乡教育做出杰出的贡献。抗战爆发后,陈先生倡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为国内抗战争取了巨额捐献。据统计,抗战期间,华侨捐献的义款达70亿元国币,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救护车1500辆,大米1万包及大量药品等。陈嘉庚在海外一呼百应的威望,是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
这样的“大财神爷”和有重大影响的华侨领袖人物到了,国民党政府当然不会放过宣传自己的机会。蒋介石专批了8万元专款接待费,政府要员倾巢出动。接见,参观,游览,一日数宴,关怀倍至,并大力宣扬他们如何“廉洁奉公”、“团结抗日”,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实行封建割据”,特务头子戴笠还派出大批人马,严密监视慰劳团的活动,竭力阻止中共方面接近陈嘉庚,企图让陈先生看看“陪都”情况就打道回府。
但陈嘉庚老先生犯了倔,一定要去延安看看。那天晚上,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问陈先生还想去何处,陈答:“晋城、灌县。”
蒋介石又问:“还欲何往?”
你不明问,陈嘉庚也不明说:“兰州、西安。”
蒋介石刨根问底:“尚有别处否?”
陈嘉庚只好坦言:“如延安通车,也要去看看。”
蒋介石脸上顿露不快之色:“陈先生旅途劳顿,还望多加保重。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不日可到重庆,看此来有何结局吧。”言下有劝阻之意。
陈嘉庚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不得不亲往,以尽责任,回洋以后亦有事实可报告侨界。”
蒋介石只好说:“到什么地方看看都无妨,但要防止有人做欺骗宣传,以免上当。”
5月31日下午5时许,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随即出席了有五千多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先生在会上讲了话,谈了他回国慰劳考察的目的和经过,并讲到南洋华侨如何关心祖国的命运,如何支持祖国的抗战,募捐巨款、抵制日货等等。廖冰等华侨青年听到这样的报告非常兴奋,回想起当年在南洋的生活和斗争,想到那里的亲友、同志和广大的侨胞,人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6月1日上午,陈嘉庚一行来到女大,校领导王明、柯庆施等人迎了出来。由于陈嘉庚只会说闽南话而不会国语,女大特意安排会说闽南话的廖冰和福建籍学生邓寿雨等给他介绍学校情况,并在必要的时候作口头翻译。陈先生手拄文明棍抬头望去,一排排窑洞层层围绕在半山腰上,一阵军号响起,学员们身着灰蓝色军装,像条条溪流顺坡而下,集结在操场上列队跑步。有的班正上课,每人坐着一只小木凳或者几块砖头,整整齐齐排列山腰平台上,听老师讲课。
这景象对陈嘉庚来说,着实很新鲜。他转身问廖冰、邓寿雨:“你们成年累月就是过着这样的大兵生活吗?”
邓寿雨把陈先生的话翻译给大家,同学们高声回答:“是的。”
先生感慨万分地说:“太艰苦太紧张了。”
廖冰笑笑说:“不这样训练,我们将来怎么上前线啊!”
先生高兴地点点头说:“我是担心你们,过惯了南洋小姐的生活,在这黄土高原、荒山野岭吃不消啊。”
陈嘉庚爬上山坡进了窑洞,看同学们睡的是大通铺,铺的是草垫子。又参观了食堂,学校自办的缝纫组、纺织组等,详细询问了冬天如何取暖、每人每天吃多少粮等,老人感动得频频点头。他的秘书李铁民边走边对陈老说:“这才叫‘艰苦奋斗’啊,上了前线还要加上‘英勇牺牲’4个字。”
李铁民也是爱国华侨,正巧,他的女儿李芳娇是廖冰在新加坡南洋中学的同班好友。廖冰曾去过李家,并见过李铁民的夫人,中学毕业时,同学们互赠照片留念,廖冰一直把照片带在身边。当廖冰拿出当年的照片,说起那些往事时,李先生高兴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延安能碰上女儿的同学,这本身就证明了延安的感召力。
李铁民把廖冰拉到陈嘉庚身边,热情地做了介绍。陈嘉庚像见到久别的儿女一样,握着廖冰的手,问了她好多好多事情。廖冰的心情很不平静,她告诉陈嘉庚,她们这些从南洋回来的学生很多都已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已经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却用华侨捐赠的巨款购买枪炮来对付自己的同胞,蒋介石还命令胡宗南率几十万部队把陕甘宁边区重重包围,想困死、饿死、冻死八路军……
陈嘉庚深深地叹了口气。
参观结束,陈嘉庚一行人本打算乘车返回,但李铁民在上汽车时,不小心头部碰在车门顶上,流血不止。学校领导十分着急,赶紧找医生送李先生去中央医院。陈嘉庚本来打算只在延安待三四天,结果李铁民一住院,走不了了。这个小小的偶然事件,给陈嘉庚提供了更多了解延安的机会。
此后,廖冰、邓寿雨等一些华侨青年和福建籍学生,常去看望陈嘉庚和李铁民。都是自家人,陈老先生又做了些私下调查,有些事情问得很坦率:“共产党真的打日本,不打内战?”“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共妻?”“陕北老百姓真心拥护毛泽东共产党吗?”“凡是不听共产党的,是不是都要砍脑壳儿?”
廖冰她们哈哈大笑,一一做了解释,恨不能一下子把什么都讲给老人家听。看着这些纯真学子,陈先生也非常激动。聊到深夜,廖冰她们起身告辞。陈先生不放心,说:“这么黑的天,不要出什么危险,是不是派人送一送?”
廖冰、邓寿雨笑了。她们说:“延安现在是全中国治安最好的地方,一个人走都没有问题,更不用说几个人了。”
陈嘉庚以手加额,惊异地说:“看来我听那边的宣传还是太多了,没想到共产党治理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出意料!”
还有一次,他和廖冰几个华侨学生谈起边区的民主选举,他不相信地问:“老百姓多不识字,不会写被选人的名字,怎么民主呢?”
廖冰兴致勃勃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被选举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人身后放一个碗。老百姓走上台,相中谁,就往谁身后的碗里放一粒豆子。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这就是边区的无记名投票。”
陈老禁不住哈哈大笑,风趣地称这种办法为“豆子选举”。
数天接触,看到这些华侨儿女一个个精神昂扬,又黑又红,真的成了抗日先锋、民族斗士,老人欣慰地笑了。
陈嘉庚还与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做了长谈。
在一次欢迎慰劳团的联欢晚会上,冼星海指挥百人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那气势雄伟、激越澎湃的歌声,有如大河怒涛,深深打动了陈嘉庚老人的心。歌声一落,他便站起来摘下帽子,向合唱团深深鞠了一躬。高原上的劲风吹拂着先生如雪的白发。他用几乎哽咽的声音说:“在这里,我听到了中华民族的心声!你们唱的不是歌,而是中华民族的怒吼!”
来之前,陈嘉庚基本上是个“拥蒋派”,认为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还得服从蒋介石一个领袖的指挥。
离去时,经过对国统区和边区的比较考察,先生的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6月8日早晨,朝霞洒满苍茫广袤的黄土高原,远山如涛,石崖陡立,初夏的风已给山野铺上片片嫩绿。金色的苦菜花,紫色的马兰花,红艳的野百合,星星点点开遍河边岩畔。阎锡山派来接陈先生一行的车子已经等待许久了,可陈嘉庚依然依依不舍地同每位前来送行的同志话别。廖冰走上前,向陈老和李铁民先生敬了一个英武的军礼,陈老握着她的手连连说:“姑娘,延安是个培养人的好地方,在这儿好好学杀敌本领吧,胜利时我们再见!”
他深情地最后望了一眼雄伟辽阔的大西北说:“不虚此行!”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个信念在陈嘉庚心目中深深扎根了。
蒋委员长对陈嘉庚的这个结论当然是不高兴的,一年后免去了他的参议员身份,后来又派特务屡加骚扰,逼得先生在爪哇岛隐名埋姓了整整10年。
仅仅8天的延安之行,决定了这位老人——一代华侨领袖的余生。1949年,陈嘉庚来到北京,走进群贤毕至、满堂生辉的全国第一届政协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