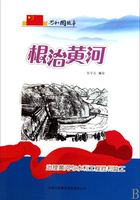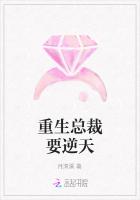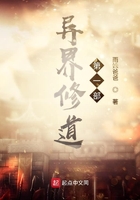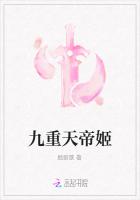在这么僻远的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大学已够诧异;而其中的妇女还在兵荒马乱中来自中国所有的各省,那就显得格外惊人了。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后来世界知道了,这天的中国大上海发生了一件秘事。
黑夜,黑巷,黑影,黑衣。十几个男人,零零散散地,东张西望,脚步轻移,悄悄潜入一条寂静的里弄,进入一家乌瓦粉墙的旧宅院,不知暗中搞了些什么名堂,一两天后像是被什么人发觉和惊动了,又迅速先后溜走。
整个世界根本没感觉,整个中国也照旧过自己懒洋洋的日子。
两天后,这伙人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脚前脚后现身在绿荫如海、碧水轻荡的嘉兴南湖。他们像是生意场上相遇的一群旧雨新知,嘻嘻哈哈相互作着揖,嘴里说些“恭喜发财”的好听话,还有人去租了一条乌篷船,说“我们要谈些小生意,有朋友会摇船,就不必劳驾船娘了。”然后,他们相互承让着,上了颤巍巍的踏板。那是平平常常的1921年7月,平平常常的一天。船上,13个布衣,有的摇纸扇,有的摇蒲扇,舱中的竹几上,一壶茶,几张纸,讲话的人或者低声宏论,或者只言片语,或者相互争论几句。
看起来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其实也够普通的。大都是从深山沟或小地方走出来的,不过读过一些书,吃过一些苦,东南西北走过一些地方。但是没人知道,有些书,让这些曾经很普通的男人内心悄悄起了变化:一种刚在世界上兴起、又传入中国的主义让他们眼光雄阔起来,让他们的心境激昂起来,让他们的胸怀深远起来,让他们的思想喷薄起来。这13个男人当时代表的不过几十人,在当时的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不过沧海一粟。而且,他们手无寸铁,口袋里大约只有一点点买烧饼的铜板,一副寒酸的样子。
但是在船上,他们居然在谈论一个极其宏大的主题:救中国!
也许,他们谈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坚船利炮的西方列强把中国打得一塌糊涂,那以后中国如大厦将倾,一败涂地。也许,他们谈到了两年前的五四运动,那是一星火种,而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也许,他们谈到了孙中山,那是一个伟大、善良、有教养的爱国者,领导一批精英打倒了皇帝,把根深蒂固的两千年封建王朝踏翻在地,功莫大焉。但他斗不过狡狯凶险的军阀,抱憾离世之际,他悲愤地留下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面对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灵魂,我们能从这遗言里读出他的痛楚和眼泪。
总之,先是在上海,后来在嘉兴南湖的乌篷船上,13个布衣断断续续谈了几日,几张纸上记下一些条条,很简略,很概括。上海的密探和警察肯定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可疑,汇报上去,正在给老婆或情妇打电话的长官挥挥手说,十几个男人鬼鬼祟祟凑在一起干什么?抓起来问问,去吧!
13个男人从上海迅速转移到嘉兴,就是因为意识到有危险了。
7月的上海,正是炎天流火的日子,那儿的警察和密探肯定有点儿懒,有点儿怕热,有点儿官僚主义或兵僚主义,有点儿蛮不在乎。偌大的中国,几大列强坐镇,几大军阀争雄,手中几百万军队呼来唤去,指哪儿打哪儿,十几个书生草民穷光蛋能翻什么浪!
警察和密探为应付官差,抹着腥热汗,很不耐烦地到那条里弄走了一趟,没见什么人影,拉倒了,回局子里搓麻或者睡午觉去了。
历史那个瞬间就这么平平常常过去了。
后来人们知道了,这13个书生一边喝茶,一边秘密决定了两件震动中国也震撼世界的事情,一是成立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二是实行一个主义,叫马列主义。然后他们揣着这几张纸,装出一副良民的样子各自分头走了。他们是那样普通,以至走进茫茫人海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那些大军阀,包括后来崛起的蒋委员长,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13个人的决定给他们搞了那么多“麻烦”……
对于人类的创造力,历史的想象力是永远不够的。
漫漫长夜中,许多看似偶然的电光石火不断闪射,其实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因果关系。一旦点燃导火索,大喷突大爆发便不可避免地到来。1921年7月,引爆中国的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狂飚运动的余音和果实。五四运动是天崩地裂的一声春雷,沉睡的东方古国惊醒了,由此天下大乱,思想大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和大膨胀时期的血腥,引起全人类的仇视和愤怒,为受难者呐喊和探寻出路的马克思主义便必然地风行整个世界,“天下靡而从之”。目睹中国贫弱到了极点,落后到了极点,愚钝到了极点,李大钊、陈独秀们悲愤地拍案而起,中国知识界的先知先觉者开始著书,办报,演讲,写文章。思想的闪电掣动在万里夜空,他们的笔像犁刀深深插进中国板结已久的土地,所到之处土崩瓦解,黑浪翻滚,创世纪的新鲜气息冲天而起。此后数十年间,无数的萌芽出土,开花,结果,撒种,接着又有更多的萌芽绽放……
这萌芽便是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自愿结合的秘密读书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无数精英,乃至整个现代中国,都是在读书会的幽暗烛光中悄悄生长起来的。
读书会造就了伟大的启蒙。我们所采访的延安知识女性,几乎所有人都深情地记着,那些昏黄的油灯,那些秘密的或不被人注意的教室、茅屋、板棚、破庙、城郊的湖畔或林中,那些被无数只手传递过、翻阅过的脏损的书籍和报刊,有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他们读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邹韬奋、艾思奇、蒋光慈、萧红,读《共产党宣言》、《西行漫记》、《大众哲学》、《萍踪寄语》、《母亲》、《娜拉出走》……
愤怒、憧憬和解放的渴望从字里行间激射而出!
对那一代热血青年而言,还有另一种伟大的启蒙,那就是歌声,响彻中国城乡大地的救亡歌声。艺术家在晓月昏星下含着泪写,学生们走上街头含着泪唱,更多的人学会之后再散布到四面八方去唱。那歌声如烈火怒潮、飓风狂涛,排山倒海,激动和震撼着每颗不甘做亡国奴的心。
那是觉醒了的中国的呼吼。
听吧——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听吧——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听吧——
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你这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听吧——
黄河在咆哮;到敌人后方去;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都是神枪手;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打回老家去;新的女性……
歌声是历史的琴弦,民族的心声,时代的交响,风潮的前奏。所有这些歌曲几乎一夜之间风靡整个中国,抗敌救亡的决绝意志在这旋律中昂然崛起。在那个黑暗年代,除了少数精英分子,千百万识字和不识字的青年男女很难接触到系统的革命理论,但如山的民族仇、亡国恨压在心头,一首歌就足以让他们和她们热血沸腾了!
革命的思想,抗战的意志,乘着歌声的翅膀,在城镇乡村、学校工厂、深闺绣阁的上空飞翔,千百万热血儿女听到了召唤。
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千万首救亡歌曲中的最强音。二战胜利之日,美国国务院曾将《义勇军进行曲》、德国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法国的《马赛曲》、苏联的《联合国歌》、英国《哈里路亚合唱》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定为向全世界广播的庆祝节目。
采访中,许多延安的老战士对我们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因为我爱唱救亡歌曲,是歌声领我们走进了抗战,走进了延安!
这里记述的,是许多女战士在奔向延安之前的悲壮人生……
她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一位顶天立地的奇女子。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上千名死去的或活着的女性中,她是我们要写的第一座雕像。
宽额方脸,俊眉朗目,举止干练,英武不凡,这就是张琴秋。
战争年代,张琴秋曾对一位战友说,一个革命者牺牲在敌人屠刀下是光荣的,可千万别屈死在自己人手里。这句话不幸被她言中。战争年代多少次出生入死,长征中两次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她都大难不死,“文革”中却不堪造反派的羞辱,从纺织部三层楼的窗口跳下去自杀身亡。
那是个阴云密布的有风的夜晚,她假称要写“反省材料”,一直坐在桌前,等看守她的人员挺不住,睡了。张琴秋悄然走向黑黝黝的窗口,登上窗台,拉开窗扇,纵身而下,一位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就这样悄然倒在纺织工业部大楼西侧墙根下的水泥地上,与世长辞。我们说不清那一刻她是怎么想的,我们只知道那是她一生中唯有的一次软弱,而这软弱又表现得如此悲怆和决绝。
战火中,她把自己的生命铸为一块基石,这块基石又成了她生命的祭坛。
1、战地分娩
蛮荒而苍凉的大西北,风雪狂啸之夜,嘶杀声枪炮声马蹄声响彻山野,敌军的马队和士兵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疯狂追逐着被他们冲垮打散的红军部队。红军战士们已经弹尽粮绝,无还手之力了,只能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仓皇奔逃。时任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张琴秋满面尘灰,骑在马上,挺着大肚子,跟随部队突围,破碎的灰军装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中央军委决定派出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二万余名西路军将士,向西北进发,企图打通与苏联联系的“国际通道”。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西北一片荒凉,人烟稀少,根本不适合步军作战。红军在这里既无群众基础,又无根据地可以据守,而且因为长线作战,军需物质无处筹措,西路明显处于敌强我弱又缺少回旋余地的困境。果然,在甘肃河西走廊,西路军遭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的疯狂围剿,几乎全军覆没。
那是1937年1月,秦基伟指挥西路军部分残部从临泽城突围出来。原野上朔风怒号,夜色如漆,枪声大作,“马家军”又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情势万分紧急,张琴秋突然觉得腹中一阵剧痛,汩汩血水浸湿了跨下权充马鞍的麻袋片。她满头大汗,浑身痉挛,一头从马背上栽下来。战士们以为她中弹了,赶紧围过来要抬她走。张琴秋痛楚地说,我临产了,你们快走,不要管我了!
四周枪声炒豆般响,甚至听得见敌人马队的嘶鸣声。一个小战士慌忙跑去喊来随队医生,另外几个人仿佛没听见她的极力阻拦,迅即打开背包,用双手举起被子,将她围拢在里面。
寒风被挡住了,张琴秋躺在战友的被子上,眼里溢满泪水。随队军医打开手电筒,急急为她接了生。荒野寒冬,弹飞如蝗,几米之外的地方,就有战士不断中弹倒下。浑身血水的婴儿落生后,一声没哭,几分钟后,软绵绵的小身子便没了热气。军医让人就近挖了个小坑,匆匆把死婴埋掉。张琴秋连婴儿是男是女都来不及问,就被战士扶上马背,边还击边突围。
自此,张琴秋患了严重的妇科病,再无生育能力。
西路军残部逃到倪家营子,又遭遇一场惨烈的战斗,只剩下千把人,被围困在孤零零的石窝山上。3月13日傍晚,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剩下的人马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自行突围,他和徐总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当天深夜,陈昌浩没同妻子张琴秋说一句话,便悄悄离开了自己的部队。
群龙无首的西路军散了,张琴秋跟随干部支队,在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下,绕着风雪弥漫的祈连山转开了圈子。这里气候恶劣,荒无人烟,无衣无粮无弹药,连游击战也没法打。队伍愈打愈少,最后彻底地溃散了。那天在半山腰,又遇上一股敌军,大家四散奔逃。等敌人过去,满脸尘垢、衣衫破碎的张琴秋环顾左右,竟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瞅瞅山上山下,敌军正大呼小叫,蝗虫般漫山遍野地到处搜寻红军残余人员。产后的张琴秋再也无力奔逃,她疲惫地靠在一块岩石后面,伤心极了,泪珠成串地落下。刹那间,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潮水般在眼前涌过。
江南水乡,大运河畔,在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那老树古宅、墙皮斑驳、已经透出哀败气息的地主家院,细雨霏霏的青石板小巷,也许还记得一个圆脸大眼睛的女孩,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摇曳在身后。那小镇的日月星辰、私塾里的朗朗书声,温馨过她有欢乐也有忧愁的童年。
暗无天日的长夜,五四运动的风暴,悄悄传递的书报,引发了她痛楚而警醒的思考,女孩朦胧觉得这世道不行了,该换一种活法儿了。
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时带头造反,率先剪掉发辫……在上海爱国女校,通过茅盾先生结识了他的胞弟、共产党员沈泽民。两人在油灯下促膝长谈,在外滩、公园相携漫步,沈泽民以他锋锐的思想光芒,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两人最终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考入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的上海大学后,在著名女革命家向警予的教诲和带动下,张琴秋英勇地投入大革命浪潮。她脱下白衫黑裙,换上蓝色工装,深入工友群众,创办平民学校,参与组织工人大罢工,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全党只有党员九百余人……
1925年,21岁的张琴秋奉组织之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大批20世纪的中国精英人物同时在这里就读,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张琴秋的丈夫沈泽民稍后也来了,还有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子女,如蒋经国、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
1931年,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把呀呀学语的女儿留在莫斯科,回到风起云涌、灾难深重的祖国。两年后,沈泽民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苏区。琴秋身穿灰军装,头戴红星八角帽,扬鞭策马,征战不息,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根据地,她的英名渐渐传扬开来。敌人宣传她是“青面红牙一身毛”、“一天吃一个小孩”的“女妖头”。一次遭遇战中,她沉着镇静地指挥数百女兵(另有三百名伤病员)抢占山头,向四川军阀的一个团发起猛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在山谷里乱成一团。张琴秋乘乱发起政治攻势,令女战士们齐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听到一阵阵清脆的喊声,看到山头上钻出来的都是头缠红布标记的女人。白军官兵全愣了。当官的下令反击,当兵的本来就怕和红军打仗,又不想卖命,便吵吵嚷嚷说,“好男不跟女斗”,“把这些婆娘打败了,也算不上英雄好汉”,谁也不肯放枪。末了,当官的和当兵的相互对骂起来,长枪和短枪也对上了。张琴秋一声大喊“冲啊”,身先士卒跃出战壕发起冲锋,一举抓获敌团长和几个营长,武器装备也全部也被我缉获。事后,四川报界纷纷报道,“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枪械,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
英勇而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因张国焘的错误导向,张琴秋跟着红四方面军,竟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其间多少次在枪林弹雨的缝隙中,侥幸躲过死神魔爪。1936年7月,长征途中,张琴秋与并肩战斗多年的战友、小她两岁的陈昌浩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