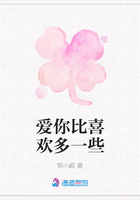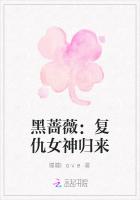我们是妇女先锋,
我们是妇女榜样,
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
在女大亲爱的欢聚一堂。
女大是我们的母亲,比母亲更慈祥,
女大是我们的太阳,比太阳更光亮。
要努力学习革命方法,学习理论武装,
学习职业技能,学习道德修养。
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
我们要英勇的走上战场,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
——一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歌
(王明词,冼星海曲)
中国有这样一个奇迹。
延安——在大西北的腹地,风沙蔽日,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生活艰苦,四周的环境又是那样险恶,面对的是充满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法西斯和后来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那样的强敌。我们相信,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但我们也知道,这胜利注定要以血流成河和千百万人的牺牲死亡为代价。
奇迹是:竟然有那样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精英,面对无比的艰难困苦,面对无数的流血牺牲,他们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汇集到延安的旗帜下。
巨人毛泽东在那里成熟为中国的领袖。连敌人也不得不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见到朱德,就被他敦厚的形象、钢铁般的意志和沉稳的力量所震撼。
许多女大同学向我们说,去延安之前以为那里都是些没文化的“土包子”,到了才知道,那时的延安真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他们具有超常的特质;他们目光远大,思想深邃,意志坚定,才华横溢,充满殉道者般忘我的牺牲精神。他们能够迅速把握时代的脉动,倾听民众的心声。他们的生命因此生机勃勃并且蕴含着巨大的张力,能够带动人民,推动历史。
而这些从乡村、城镇汇集到延安的花季女孩又是怎样的“战士”呢?抗大一位老战士回忆起她们最初接受的军事训练,向我们作了这样的描述:
最有趣的活动,莫过于夜行军。这种训练事先并不通知,仅仅在队长室的小黑板上写上:“今晚口令:老虎。”这也很平常,有人看了,有人没看,有人听说一声就扔在脑后了。当我们睡得正酣时,忽然一声军号,紧急集合!窑洞里没有灯光,在黑暗中,大家一坐而起,有的找帽子,有的找皮带……土炕上成了瞎摸乱抢“捉迷藏”的舞台,下了炕,大家又乱穿鞋子。队长哨声一落,整支队伍就出发了,一路上大家悄声你怪我我怨你,谁知队伍走到半道,大土堆后面会突然冒出一个哨兵,大叫一声:“口令!”
答对了的,哨兵就放行了,有的不知所措,瞎说一气:“酒壶!”“尿壶!”把当了没几天兵的哨兵也逗得直笑。天亮了,好不容易熬到目的地,队长说:“解散!”大家互相一打量,顿时笑开了锅。穿错鞋的,戴错帽子的,什么怪样子都有。最好笑的是一位同学竟把两腿穿在大衣袖子里,再把大衣翻上来,拦腰系一条皮带,难怪她总是落在队伍后面,这样的穿法怎么迈得开步子啊!大家围着她笑得人翻马仰,有人直喊“哎哟!”回校途中,这位女同学走路总是一步一扭,像拉不开步子的样子。回到窑洞,大家问她:“你是不是受伤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我自己觉得太好笑,笑得尿湿了裤子。”大家听了,更加笑得满炕打滚儿……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花季女孩转为战士的第一步。
这样的女孩难道能打仗能胜利能赢得整个中国吗?
历史已经证明:住过延安窑洞的人一定会创造、并且能够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
中国的二十世纪是这代人的世纪。
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斯诺在延安流连了四个月之后,激动地向全世界宣告,他在这里发现了“东方的魅力”。
毛泽东的名言
在气势磅礴的黄土群山中,在蜿蜒清丽的延水河旁,1939年7月20日下午3时,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开始了。
这一天,校容焕然一新,在河滩地上平整出来的学校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校门扎起了彩色牌楼,油绿的彩门衬托着两边围墙上20个醒目的红色大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那20个字即女大校训:“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校门正上方,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及国内外妇女领袖蔡特金、克鲁普斯卡娅、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画像。广场上搭起了一座舞台,是为会后的联欢会准备的。
下午3时,身穿蓝灰色军服的同学们已坐满会场,各班之间互相拉歌,歌潮一浪高过一浪,会场一片欢腾。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朱德、刚刚摔伤手臂的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新四军代表张鼎丞,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安德华等走上主席台。毛泽东身材瘦削,目光炯炯,浓密的黑发很长并且向后掠去,这样的发型在延安是很独特的,显示出毛泽东不拘一格的非凡风度。
开学典礼定在下午3时开始,大概是为了适应毛泽东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的工作习惯。毛泽东的灰布裤子上缀着深色补丁,旧上衣显得很宽大,口袋里塞了些书报什么的。他迈着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微笑着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
那时的延安真是“胸怀全球”,光是会议的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名单就有一长串,包括中共领袖、苏共领袖、各国党的领袖、中央妇委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等。会议首先由鲁艺乐队伴奏,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和《女大校歌》。然后由校长王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作了报告。他介绍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陈云、邓颖超等带头将他们担任重庆国民参议会参政员的薪水捐献给女大以购置图书,林伯渠捐献了一批油灯,秦邦宪捐献了大礼堂的幕布,邓小平捐赠了一些战马,会场因此一次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毛泽东讲了话。女大是他提议创办的,看到这个提议顺利实施了,他很高兴。他站起身,把烟头揿灭,然后操着带有浓重湖南腔的国语说: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毛泽东发出他那广为人知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在校园的土台上,举行了盛大的歌舞晚会。不少老乡也围拢来看热闹,那些新奇的节目教他们大开眼界,乐得手舞足蹈。他们没见过口琴,一个同学表演口琴独奏时,老乡纷纷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
女大的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大约百余孔。这是1939年春动员数百民工,用一个半月时间开山凿洞挖成的。清晨4时半,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和口哨声,学员们起床后,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有棱有角(许多被子是带补丁的),然后沿着羊肠小道下山到延河边练操、跑步和洗漱。远远望去,衬着黄土高坡,女战士们就像一条条蓝灰色的小溪,弯弯曲曲顺坡而下,同时伴随着此伏彼起的歌声。据说这成了延安一大景观,而且是对岸男士最爱看的景观。夜晚,一层层、一孔孔窑洞里点燃油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口,在高原寂静的夜空中闪烁,这时从对面山坡或延河边望去,女大校舍又像一座巍峨而宽阔的不夜城。
女大同学来延安之前大都没见过窑洞:来自天津的徐克立(原驻外使馆参赞)对我们说,未到延安时,她还以为窑洞很矮,进出得爬行呢。没想到窑洞如此宽敞,而且冬暖夏凉,还可以防敌机的轰炸。
女大的窑洞每孔约10几到20平方米。8至10人睡一条长长的通铺,是木板搭成的(这是女大特有的待遇,以防女同志睡潮湿的土炕患病),每人只有大约1尺半宽的床位。夜里起来上厕所,回来后睡觉的地方常常就没了,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睡回原位。全组共用一张木桌、一盏小油灯做晚自习,对笔记,看书,写墙报,写心得。冬天共用一小盆木炭火取暖。食堂在山脚下,每日3餐,蓝灰色军服的溪流要上下山6次。遇有雨雪天,各班就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乐事。
女大原来没有像样的厕所,女孩们要方便了,都是跑到山坡上找个避人耳目的僻静地方蹲下就来。王明校长是从苏联回来的,比较讲究文明卫生,他到各窑洞巡查时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给女同学挖了厕所,还用席子围起来,这才比较像样了。不过说来好笑,女孩们不怕日本鬼子,却害怕老百姓传说中的各种“鬼”,天一黑就不敢上山解手,就近找个草木繁茂的隐蔽处,方便后赶紧往回跑。一天夜里,一个女孩出来解手,她刚蹲下去,猛地从对面草丛中站起一个不像人样的黑影,那个同学吓得差点儿昏过去,没命地喊“有鬼!有鬼!”然后扑上去拼命与那个“鬼”撕打起来。大家闻声出来一看,那个黑影原来是另外一个窑洞的同学,因为怕冷,从头到脚裹了一条毯子。大家笑得人仰马翻,肚子都疼了。
中国西北是一片神奇的皇天后土。回首绵延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半部历史在西北。自秦始皇到强大兴盛、万国来朝的唐代,十几个皇帝在那里君临天下,号令全国,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自宋以降,首都南迁,中国也就逐渐走了下坡路。随着长达许多世纪的森林砍伐、风雨侵蚀,裸露的地表斑驳了。巨大的尘暴遮天蔽日,在这片土地上横冲直撞的黄河巨涛又把泥土裹挟而去,使得这里渐渐成了荒凉少雨的不毛之地,每10年平均就有大小3次饥荒。据史料记载,发生在1929年的大饥荒,有250万人被饿死。1936年,那里的婴儿死亡率在60%以上,有文化的人只占人口的1%。
毛泽东最终把根据地定在这里时,昔日繁华早已被历史的风沙湮没殆尽,只剩下空旷而雄奇的黄土高原在岁月深处沉寂着,偶尔会听到一曲悲怆的信天游或悠长的驼铃划空而过,打破这沉重的寂静,仿佛是历史绵长的哀叹。
贫瘠,空阔,封闭,愚昧,这就是历史留给三十年代的陕西的遗产。
据说,那时代陕西的贫苦百姓从生到死只洗3次澡,落生一次,结婚一次,死后一次。一家人轮着穿一条裤子,一年里有大半年靠吃糠咽菜过活是常见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李素,中农家庭的章岩(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父亲曾做过安阳县长的李逸云(原对外文委干部)回忆起那时的见闻,笑着承认那时做工作队员,深入群众真是可怕,你简直没法儿看。进了陇东老百姓的窑洞,男的大都裸着上身,下体只围了一块破布。女的缩在炕里,脚上缠着厚厚的裹脚布,身上却没穿的,几乎一丝不挂。一家男女睡一铺大炕,爬得满身满头都是虱子。老乡见你吃饭没筷子,顺手折一根树枝,用嘴一吸溜,然后递给你,你说你用不用?吃饭的粗瓷碗本来就很黑,盛饭前用脏兮兮的手或袖口一抹。吃完了也不洗碗,用嘴舔干净,你说下次你怎么用吧?说实话,“深入群众”这一关到现在也没过。当时只好托词说,组织有要求,不许随便在老百姓家吃饭,才避免这类令人尬尴的事儿。可总饿肚子也不行啊,只好硬着头皮吃。后来我们走哪儿,都把吃饭的家什儿随身带着。
延安是一座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1939年,日本飞机把它炸成了废墟,人们只好进山挖窑洞躲避起来,经济生活几乎陷于瘫痪。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许多年里土匪的打家劫舍、横行肆虐,整个陕甘宁边区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曾对斯诺感慨地说:“有一度时期,我们处境窘迫到无衣可穿,无粮可炊,纸张、蔬菜、鞋子,甚至过冬用的被褥,一无所有。”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曾跟随一个八路军连队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的土地上和这样的年代,开始了自己的生长。
都市女孩说:到了延安,最深的感受就是馋
来到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大都生长于富裕家庭,或是豪门闺秀,或是小家碧玉。身高体壮的王云告诉我们,女大毕业后,留在中央妇委工作的25个同学,有24个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1个出身富农。
都是20岁上下的娇娃,延安的生活对这些女孩儿来说,真是苦死了。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一度非常困难。原来每周一次的会餐,改为半月一次,后来半月一次也没影了。所谓“会餐”,就是菜里加些肉和豆腐粉条什么的,主食是小米饭或馍。原来每人每月还发3元边币,主要用来购买牙刷、牙粉、肥皂等生活日用品。有时大家馋了,就凑份子在女大合作食堂买些红烧肉,倒在小米饭桶内,搅匀分吃。零用钱停发后,红烧肉没得吃了,日用必需品也没钱买了,大家就找些猪鬃捆在旧牙刷把上代用,用盐末代替牙粉,用草木灰洗衣服洗头。
党中央对女大学生特别照顾,尽量创造一些条件让她们享受一些“特权”,比如每周她们可以到“澡堂子”洗一次澡。所谓“澡堂子”不过是个土墙围子,站在里边的地上,用水桶往身上冲一冲。
延安女大风行过一阵“烤浴”,可惜这好方法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已经失传了。白凌(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书记兼副院长)回忆说,那时女大学生经常下乡搞土改或征粮,上级要求要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开会。女同学们与村里的婆姨、姑嫂同住火炕,有时还盖同一床被,没几天身上头发里就长满虱子,再加上山里缺水,在那里工作许多天,经常不洗脸不洗澡。日子长子,身上奇痒,皮肤抓破出血,又会染上疥疮,严重的,手指缝、脚趾缝、胳膊肘、大腿根都长疥了,整天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边开会一边伸手到衣服里抓痒痒,活像一群猴子手脚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