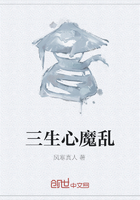四月四,重明节,赶着天光后半个时辰,林乱起了个早,把院子里挖开,取出一坛酒。
老林的骨灰按他临终时候的嘱咐,被冬天时候来的商队带走,按路程估计,现在已经洒在遥远的东海里了。林乱就在应山向阳靠山顶的地方,给他扫了一片地,糊上了灰泥,立了一个碑冢。他把那坛酒洒在了坟头上,然后返回院子里开始一天的作息。
烧水,煮饭,洗衣,扫地,读书。每天的日子还是井井有条,早起早睡,这是林乱的习惯,今天也是一样,这些日子都一样,这是在这几年里照顾老头的日子里养成的,林乱觉得这样做有益身心,只是有点怪怪的。人家家里的少爷,十岁了还不会自己整理发冠呢。
林乱想着,边把洗干净的抹布码好在阳光底下晾晒。
现在是晚春,最后一缕风把樱花树吹得差不多干净了。只不过今年没人再去用素布盛着这满地的花骸,这情形要被老林看见了,可不得好生教训林乱一顿。忙完以后,林乱喜欢坐在院子里就着天光看书,他将昨晚读了一半的《地演学概论》翻完,伸了个懒腰,张开的嘴正遇着最后一片飘落的樱花瓣,细细咀嚼一番,小小的花瓣就成了汁水。老林以前自诩走商前是个读书人,对吃花这种风雅书中所说粗鲁的事情从来都是嗤之以鼻,林乱也总那他要喝樱花酒却不要吃樱花瓣这事嘲讽他。
“你这就是婊子立牌坊,喝花酒跟吃花有什么区别?”这是林乱的原话,气的老林差点拿扫帚抽他,一老一小哇哇大叫着在院子里一逐一逃。
林乱似乎嗅到了花香,耸了耸鼻子。他背靠着石桌发呆,思绪飘忽。
林乱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林乱只知道自己在应山城里长了五年,在应山上长了六年。
聪慧如他,最不少的就是自知之明。他不属于这宁静的一隅,应城也不属于他。虽然老林走之前嘱咐要他好好照顾这两棵樱花…可笑的林老头,林乱觉得这种事情还没有那套比他自己还沉的《北洲博物志》有意思。难得来这茫茫世上一遭,北洲这么大,不去看看,太可惜了。
北洲之外还有瀛洲,还有遥远的中洲和传说中整个土地都是冰块聚成的极洲。但是现在,林乱只亲眼见过应山城,只见过温顺的应山,只见过奔腾的北江。矗州绝顶连绵的山峰、北洲外的东海、筮州南边的无尽深山、繁华的郾都和扬州城…他都知道,他曾在很多书里见过,现在他想再见一遍它们真实的模样。
“这个世界上有意思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能一件件体验过来,想想就觉得很快乐呢。”林乱是这么想的。游历这种事情时不可待,还好林乱有与生俱来的果断。
四月八,阴小雨,林乱在房里提笔给应山城里的李老板写了一封信。
几天前他雇了几个山下的闲人,也是因为春耕正值尾声,农务并不繁忙。林乱差遣他们把这些不仅堆到房梁高还堆满了三屋子的书给搬了出来,准备分发给应山城里需要的学子和渴读的人。有些书遭了囊虫,林乱顾的这些人就是专门替他翻书,查找被囊虫吃掉的纸张,然后再由他提笔将缺失的部分从脑海里提取出来誊写在纸上夹在书本里,这项工作他做了三四天,用了两斤上品的绥州纸,笔墨都是李老板差人送上山来的。
当然,那些花了百万黄金买回来的修行典籍,都被林乱收在了一个竹筐里。竹筐做功精良,里面码制了一层针脚细密的马革,上面还有个盖子,商行的人拍胸脯承诺,就算扔在五月的梅雨天里三天三夜也不会进水。竹筐大小正好适合他的身材,不至于背负行走时拖沓。
林乱在院子里留了两坛酒,另外两坛赠给了应山上的两户邻居,以表示这么多年他们不间断的柴火和新鲜野味的供应。山人哪识得这酒的昂贵,豪爽的猎户直接拍开来拉着林乱喝了半坛,他直呼“好喝好喝,这辈子没喝过这么香醇的酒!”,却不知这酿酒的灵酵一个小指甲盖就得他家四口人十年的开销。大家都是熟人,对林乱异于常人的成熟心智早就见怪不怪。那晚,林乱在猎户家吃了满桌由猎户的婆娘张罗的山珍席,还招呼来了柴户一家,猎户和柴户最后醉倒在地上,剩下的小半坛酒撒了一地。
四月十,李敢出城上了应山。
这段时间商行里出了很多事情,让他有点焦头烂额。原来的手足弟兄只剩下他一个还在应丰会里,虽说老林这些年也没管过事,但是他的离去始终给那些不安分的人感觉:大山又去了一座。新的几个股东没有之前他们的情谊,为人做事上一向咄咄逼人,有种要挤掉他这个应丰会最大元老的势头,他已经有了一些预感。绥州的商铺和行会已经很久没给他回过消息了,派过去的人也是人间蒸发。可就算是这些琐事再怎么繁杂,今天这一趟他也必须去见林乱。
院子里四处堆积的书籍都不见了,林乱坐在石桌边上翻看一本书。樱花已尽,李老板记得往年这个时候还能看到略带重明雨水的花,今年不知为何都落了。
“如果这是你的意向,叔叔会尊重你的意思。”
林乱在信中告诉李老板,他想想离开应山城,去郾都看看,书院或者皇城,然后看看这天下有什么有趣的地方,顺便帮老林完成他的遗愿。
林老头要看了信中的说辞必定会三尸暴跳,毕竟遗愿这种事情被顺手完成了,挂谁身上都不满意。
李敢年轻的时候被行当里的人叫敢死郎,字面意思,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说。可年过大衍的他却不敢把这个只比他腰带再高一点的小孩真正当成一个年仅十多岁的孩子。
李老板摇摇头,毫无疑问,林乱不会继承老林的事业。林之熙五年前就把自己的产业悉数都托付给了李敢。而李敢自己曾经想过,以后让林乱入赘李家,接受家业的想法。李敢只有一个独女,女婿是入赘的,可至今也只有一个孙女。女儿去年秋天刚有喜脉,至今隆起的小腹里还不知道是男是女。
“多谢李叔,也请你在我离开以后能派人好生照顾老头的这两棵樱花树,要是给出什么问题咯,他可得从黄泉里游出来弄死我。”
林乱一边说着一边拿小铲抹开院子里的浮土,直起身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小心翼翼得铲土,以防弄碎瓦瓶。几铲子下去以后,他取出一坛用纸和泥封好的樱花酒,拍开来给李敢倒上一碗。
“李叔,我敬你。”说罢抱着跟他脑袋一样大的坛子猛喝了一口,模样滑稽的不行。老李想笑,跟着林乱干完了这碗酒。
“此行一别,路途遥远。林乱,我死之前可得回来看我一眼啊,到时候可得名扬天下,给咱们应山城好好长脸面哦。”李老板说。
“那是自然,你别看我今年才十一岁,将来我可是要做那天底下修行第一的…”林乱边说边喝,学着那大人喝酒时发出的赞叹声:“哈!”
李敢一听,笑了,道:“那什么叫修行天下第一?”
“唔…就是那个,修行嘛,修的是身心,修的是天道,修的是脱离这繁杂世间,修的是自由,虽然这修行跟打架分不开关系…可是这修行一说,能有无数种解释,那和尚坐地参禅啥事儿不干也是修行,书院学士读书论道也是修行,我跟你说,我这天天吃饭睡觉干活,其实也是修行…喂你别笑,你看我跟你说你也不懂。打架第一厉害可不一定是修行第一厉害,就算是三山书院的大剑师,还不是要给境界比他高的一巴掌按到土里去?所以说这修行第一嘛…这个…总之就是…。”
李敢知道这小子能扯淡,林乱狡黠的表情放在他那张童稚的脸上却一点都没有不搭调的感觉。
“那人家怎么知道你修行天下第一呀?”
“我就打赢那打架第一的。”
“那岂不是还是打架天下第一?”
“我又没看不起打架天下第一的。”
李敢大笑,怪不得老林以前天天要跟小林斗气。想到老林,心中又黯然。于是他说:“此行一别,山水有期,贤侄,保重好自己啊。”
林乱忽然面容严肃下来,对李敢行了一礼,道:“这些年,多谢李叔了,我答应你,今后李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这种话从一个小孩子嘴里说出来分外滑稽,李敢却煞有其事得点点头。
“贤侄能这么说,我就算来年就随林哥而去,也心无担忧了。”
“小祈以后择夫之时,我会好好帮您把关的!”林乱面带肃容地说。
李老板一听这话,笑骂道:“滚滚滚!姑娘家爱嫁给谁你管得着吗?”
林乱放下酒坛子,说:“那你到时候可别哭着喊着要把小祈嫁给我…”
李老板被林乱呛得话在肚里讲不出来,这小子可是把老林的无赖劲儿学了个透彻,隐隐有升华的迹象。另一说,也是他心里的想法被林乱道破,有点面子上挂不过去,于是上前学着老林佯装要教训他的样子,林乱撒腿就跑。
日末时分,他从小院里离开,下山以后车马载着他回到了城中。
两天之后,乱随李家应丰商行一支去往绥州的商队出了应山城。
林乱将随着李家商队跋涉,去往遥远又繁华的郾都,实际上他是随行,李家小姐和姑爷要北上返京。
林乱随身携带的东西很少,竹筐里除去书,剩下的空间正好装得下,两套换洗衣物,盘缠之类的。李家的队伍却很长,将近百来号人,一半是护卫。
这是林乱第一次走过应山城这条唯一的官道。一直沿着它走,会到应州的首府,然后他们再从那边的水路去往郾都。但是水路并不能直接到达郾都,在郾州的边界,他们要换回陆路。实际上一般从应州去往郾都,大都是直接沿着绥州的官道直接走陆路,之所以走水路,因为应丰会现在的总会正在绥州绥阳城,那是绥州的中心,所有陆路通道的必经之路。应丰会里现在掌握各个商路的会董并不是最初创立它的五个人其中任何一个,那个人姓安,叫安道全。
这确确实实是林乱第一次离开应山城,却没有想象中的离愁别绪。长龙一般的队伍有四十匹马,李主家的马车最大,套了六匹马。他们用了三天时间从应山城到梡城,也就是应州首府,然后再稍作休整,一夜时间以后启程去往港口。北江到了梡城这儿水势豁然开朗,放眼望去只能看到江对岸蚂蚁大小的黑点儿,那是对面的码头,辽阔得让人以为是海。北江最宽的地方就在梡州。
江风在靠岸的时候会比其他地方要轻柔一些,但也没有软到哪里去。林乱就站在江边几丈高的浮萍码头边上,身边是来来往往搬运东西到船上的伙夫。
林乱问在他边上也在看人干活的船老大,他有没有见过大海。
“我还在海上跑过船呢,那海可看不见边儿啊,东海,你们家那两艘大船,扔进去就是两粒灰。”
林乱又问:“东海跟这北江比呢?”
“废讲,看的到边儿的就不叫海了。”
跟书上说的一样,林乱想,无边无垠,才叫海。但是大海怎么可能会没有边呢,只是人们没有看到罢了。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边,连生命都有边际,林乱猜这个世界也是有边际的,只不过没有人见到过…
“乱乱!”
他正看着大江思考人生,队伍还在做最后的清点,背后猛然遭受一股大力,差点往前摔出去。林乱被一个小女孩从腰后钳住,他一转身,女孩也跟着他的位置转动。
这是李敢的独孙女,李秋祈。
后面是急急忙忙赶来想拉她回去的奶娘。小姑娘调皮,不使劲儿拉不是,大力拉着也不是。
“喂喂,小姑奶奶别在水边上摇来要去了,小心你掉下水去,我们伙计不收钱可不救你啊。”船老大在边上打趣,他也觉得这孩子很可爱。李秋祈生得就很讨喜,大大的眼睛盯着奶娘不放,只要她位置一变,立马拽着林乱挡在她前面。
“小祈别调皮了,快跟奶娘回车上,这江风吹多了得受寒的哟,待会小姐发觉你不在了,少不得你又得收一顿骂!”
林乱被小女孩逗乐了,也不拉着她,跟着她一起玩。
“奶娘才调皮!奶娘才调皮!”小祈吧脑袋顶在林乱背上,将他的两只手拉在身后,说:“奶娘别烦我啦,我再跟乱乱玩一会一会儿就回车上,你再管我我可不回去了!”
奶娘不大知晓林乱的底细,实际上李家里除了李敢和他女儿女婿,大家都只当这是一个普通的十岁小孩。只知道是林老当家收养的孩子,平日里待林乱也是自家少爷一样的待遇。李秋祈跟林乱简直就是民间故事里如假包换的青梅竹马,林乱三岁刚能走路的时候就被带进李家,大人们交谈的时候他在后宅里逗弄襁褓里的小秋祈,小女孩平日里在宅门里接触不到其他孩子,也就林乱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哥哥,年初听说自己要添个弟弟或者妹妹,开心得晚饭都不吃了。下人们察言观色,见李敢对林乱的态度,知道老爷爱惜这孩子,没准再过十年,林乱就是李家的小老爷了。
林乱不刻意表露自己的与众不同,下人就只当他是个特别懂事的小孩了。
“乱乱,你再给我演一个昨晚演的那个那个!”小祈并不知道烛孔显像叫什么,只好用她惯用的口癖来马虎得表述。
林乱把她从身后拉到面前来,说:“那个戏法现在可玩不了,得晚上才能玩。”
“可是人家也想学来玩嘛…”小女孩嘟嘟嘴,两只小指别在一起。林乱扶住她的肩膀,说:“晚上在大船上用完晚膳,等天黑了再教你戏法如何?”
“好!”
李秋祈蹦蹦跳跳得又走了。奶娘摇了摇头,随着她走了,心道林乱只不过大小祈两岁,怎么就懂事这么多呢。
船老大招呼几个船员做好最后的检查,纵身一跳从码头上飞一般跃上甲板,大呼一声:
“起帆哟!”
众水手也跟着应和:“起帆哟!”。
林乱回到马车,赶车的人短鞭一挥,马踩着渡板笃笃得往船上走去。
江风骤急,离人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