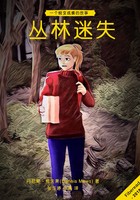在街上人时而恐慌,时而莫名尊大的气氛里,半个多月过去了,老街并没有什么异样,四乡也没有什么异样。就连那些爱在夜间乱叫的狗,也没有比平常多叫几声。
一天到晚劳累惯了的人们在歇息了几天后,觉得这歇息也实在不是个味儿,实在比干活还乏劲,于是又恢复了正常的劳作。可是这一重新劳作起来,却感到很不方便,要拿这样物什时没有,要找那样物什时不见,于是又从神仙岩将一些东西往回搬。往回搬时照样有理由:那日本人或许不会来了哩,是吓人的哩。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哟?
瞧着有人往家搬东西,父亲来了神气,对母亲说:
“你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人家都在往回搬了,人家往回搬可不远,下了神仙岩,就是扶夷江,有船。你呢,你硬要放进大山里,那么远,这下可好,你去把东西搬回来啊,我是不去了的啊,你有主见,有本事,你不听我的道理,还要说那什么马谡,自绝退路,这下你就去当诸葛亮,变出木牛流马来,把东西驮回来啊,别说我不管了哪,谁出的主意谁去……”
父亲说的这些话,实在不是一个负责的男人应该说的话。可父亲这么说时,母亲却并未生气,而是自言自语地说:
“别慌,别慌,再等一阵子,再看看,再看看。再观观场面,到时候再将东西搬回来也不迟。”
母亲感到事情有些奇怪。
母亲的奇怪并不是说日本人怎么竟然没来,还是认为这些天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生疑。
母亲觉得,日本人若是已经进了新宁县境,那么必定会有逃难的蜂拥而来。可是路上不见一个难民。如果说没有难民来,就说明日本人并没向这儿进发的话,那么平常那些来街上买货的乡人呢,怎么也少了许多,特别是那些熟客,一个也不见来。日本人既然没来,街上就应该恢复了往日的闹热……母亲以一个聪明女人的直觉和在生活中挣扎积累的经验,感到这不正常,而不正常就意味着会突然出事。
母亲的直觉非常准确。在这过于平静的日子里,谁也不会料到,日本人其实已经在老街不远处设伏,布下了重兵。
六
日本兵究竟是如何令老街人在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驻白沙,且埋下伏兵的,到今日依然无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问过很多老人,也问过从事文史工作的,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哩,日本人就那么悄悄地来了哩。谁知道?!但有一点,回答得都非常明确,那就是:日本人进了白沙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路口,在他们埋伏的区域内,所有的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
这也就是我母亲感到疑惑的,怎么连逃难的难民都没见着一个,怎么来街上买货的人那么少。
日本兵就在老街后面不远,行人路过必经之地,名为观瀑桥一带的山林里,整整埋伏了六天六夜。
观瀑桥下其实并没有水,是一座拱形的旱桥。许是哪位信奉“架桥修路”为最大善事的人捐资而建,但那资金本不多,要到河上架桥力不能及,便选一山路造一不需多少资金的桥。站在那桥上,能看得见远远的金芝岭上流下来的一道瀑布,倘阳光好时,还能看得到飞瀑溅玉,横空里展现的一道彩虹;若阴雨蒙蒙,则山色尽在雾气笼罩之中,风儿拖动雾气,时而拽出一片片翠绿,时而拽出一座座巉岩……翠绿和巉岩又相互幻化,实为一大景观。
日本兵选择的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景观之处,他们大概是要在进行大屠杀之前,利用这么一处如画的风景怡心养性。
整整六天六夜,老街人竟全都蒙在鼓里,无一人察觉。
日本兵要伏击的,是正在由宝庆府往新宁县城开来的国军的一个团。
按照常理,宝庆沦陷后,国军往新宁开来的这个团,只能是撤退的部队,而且是撤往广西,因为从宝庆经新宁去广西,白沙是必经之路。老街人说的不无道理,别说日军,就算是国军,也没有来白沙驻扎的道理,也只能是路过。而国军撤退,日本兵应该是追赶,只能在后面。可日本兵却抢先到了白沙,而且非常隐蔽地在白沙等了数日,而且对白沙地形熟悉,知道这儿好打埋伏。若过了白沙,便无险可伏。
而关于这支遭日军伏击、全团惨遭覆灭的国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到现在都没有说明,没有记载,官兵们更没有坟墓碑记。记事截至1989年的新修县志上也仅仅点明一句:
是年,国民军某部在白沙遭日军伏击,全团官兵阵亡。
国军这个团惨遭覆灭后,凡事先进入日本人埋伏区域内的人,即那些“只准进,不准出”的老百姓,全部被杀光,他们和国军某部的血,染红了江水;他们和国军某部的尸体,将扶夷江堵塞。
在国军某部正向日本兵的伏击圈一步步靠近时,在日本兵早已静候于老街人的身旁时,浑然不觉的人们又开始了“太平日子”。该搬回家的东西搬了回来,该打点礼性问候的打点礼性问候,忙完了活,到要好的人家坐一坐,抽着水烟筒,讲着白话,白话里少了原来那些担忧和惧怕,多了些某人某人如何如何在外面过夜,不敢回家睡觉的笑话。
我母亲就是被笑话的一个。
母亲在直觉的警惕中,不但不为将东西往回搬的“潮流”所动,反而一到天黑,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老街对面不远的山坡上过夜。那时我三弟出生才几个月,母亲用背带将他背在背上。父亲则无论如何也不愿跟随母亲行动,说母亲是无事多事,自讨苦吃。他说他哪里也不去,他要留下来看家,栏里还喂着一头猪哩!
这天晚上虽然没有月亮,但星星很是灿烂。
我母亲坐在老街对面,也就是扶夷江对岸,名唤香炉石的一家农户的床上。
香炉石这地名,因从江上看来,酷似一香炉而得名。而过得江来,又确有一巨型青石,横亘于江边,亦形似香炉。“香炉”的底端浸入江水中,两边又连绵着平坦的青石,于是常有漂洗的妇人、女子,穿红着绿,蹲于青石上,以棒槌槌衣。于是棒槌声声,此伏彼起,使得空旷的江野,反越显得寂静。稍倾,妇人、女子相互泼水嬉戏,笑声格格,话语撩人,惹人动心。若一见得有男人路过,那笑声、话语,倏地收敛,悄然无音,复只有棒槌声声……故有“棒打香炉声声脆”之语,被列为老街一景。
此时,我母亲正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看着天上的星星。她怀里抱着我三弟,脚头睡着我和我那刚满十岁的大姐。
当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来到香炉石,找到这家农户的主人,说要在他家里借宿几天时,这家农户的主人立即满口答应。这位男主人因为常到老街我父母开的“盛兴斋”买货,彼此已很熟悉。
“那我们就吵烦了,吵烦了。”我母亲说。
男主人赶紧回答:
“吵烦什么呢?我这里正好有一间空房,床铺也是现成的,只是没有你们街上的爽净。”
我母亲说:
“早先我连你们这样的房子都没有哩,在庙里都安过家哩。”
男主人说:
“只要你不嫌弃,我就是迎来贵客了。你们只管放心到我这里住,日本人不会到我这里来的。”
我母亲说:
“你老人家怎么就敢这样断言呢?”
男主人说:
“日本人要占也只占你们老街,要住也只会在你们街上住,他到我这个乡里来干什么?”
我母亲说:
“他们要是到乡里来抢粮呢?”
男主人说:
“他们要抢粮也是到人住得多的院落去,才能抢得多一些。你老人家看我这屋子,独门独户,又不打眼,过江来的人看不见我这屋子,站在我这窗户边,却能看见过江走来的人。就连在香炉石上捶衣的女子,我这里也看得清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不晓得跑啊!从后门一跑出去,就进了山……”
我母亲笑了。我母亲看中的,正是这个独门独户,前能看清几里路外沙滩和江边的动静,后靠大山,树林茂密。
男主人又说:
“你老人家,他四爷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呢?”
我母亲说:
“他不肯来,他讲我这是没事找事。”
男主人说:
“小心无大错,小心无大错,还是小心点好哩!”
我母亲说:
“话又说回来,家里也是要个人看着,栏里还有一头猪要喂潲。”
男主人立即说:
“那是,那是,四爷就是舍不得他那铺子。可万一日本人进了街,那猪不就正好成了日本人的下酒菜。”
男主人这么说时,女主人忙对我母亲说:
“四娘,你别听他那乌鸦嘴乱说。日本人怎么单单就会抢你老人家的猪呢?不会的,不会的!”
男主人笑了。说:
“我这也是胡乱讲讲而已。四娘,你最好要四爷将那头猪赶到我这里来,我家有猪栏,我那栏里的猪已经卖了,正好空着。你们一家人都到这里住着,房舍是差一点,但睡个安稳觉。”
男主人关于猪的建议的确引起了我母亲的重视,觉得他讲的非常有理。第二天,母亲回到老街,就和父亲商量,要把猪赶到香炉石借住的农户家里去,并要他一同离开老街。父亲一听就跳了起来,对我母亲说:“什么事都依着你这个女人了,放到外面的东西一件也没拿回来,家里已经完全不像个家了,你还要听人家的话,把这头猪也赶出去。人家那是哄你呢,是哄着你将猪赶到他家去,他家好吃过年肉呢!”
父亲吼着说:
“这个家你已经当了九成,这最后的一成,归我当!你想把猪赶走,除非你要那个想吃过年肉的家伙来把我抓走!”
父亲的话是这样的蛮横不晓事理。因为只是一头猪的问题,母亲便不好再坚持了。而就是这头留在家里的猪,几天后,成了我大姐被日本人抓住的原因之一。
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香炉石那独门独户的农户家歇宿的第三个夜晚,女主人告诉我母亲,他们第二天要到她娘家去,她父亲满五十,是大寿,不能不去的,得在娘家住一晚,但一定只住一晚,就回来!毕竟家里有这么多事,放不下的。我母亲说你们只管放心去,夜里有我帮你们看着家哩。
第二天吃过早饭,农户的男主人、女主人带着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最大的十四岁,女孩最小的刚满三岁,一家六口人高高兴兴回娘家祝寿。我母亲送他们出门。
“好走啊,你们好走哪!到了娘家记着给我捎上一句话,祝寿星老人家富比南山,寿如东海。”
我母亲像送自己的亲戚一样,一边说,一边将包有一些钱的红包封塞到女主人手里。
“你老人家太讲礼性,太讲礼性了。”
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时道谢。
我母亲又对那四个孩子说:
“在路上要听话哪,不要乱跑哪,不要喝生水哪,家里的生水能喝,外面的就不能喝哪,小妹妹走不动了,你们做哥哥姐姐的要轮流背,别要父母亲背哪……”
我母亲迎着阳光,微眯着眼睛,不停地叮嘱着。后来我母亲说,这恐怕就是预兆,我当时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呢?
那个三岁的小女孩则蹦跳着对站在母亲身边的我和大姐说:
“哥哥,哥哥,我回来带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你们,你们可要等着我回来,你们可不要走开哟!”
因为我大姐完全是一个男孩子的样,不仅是这个三岁的小女孩喊她哥哥,就连小女孩的父母亲也以为她是男孩。
小女孩蹦跳着,跑到前面去了。
然而,这农户一家六口去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走进了日本兵控制的埋伏区域。对于老百姓,日本兵在国军某部没有走进伏击圈时,是只准进,不准出,全部扣留。而在将国军某部消灭后,他们就对被扣留的老百姓实行大屠杀了。对日本兵来说,大屠杀也许需要理由,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说他们需要理由的话,那就是不让被扣留的老百姓泄露伏击的情况,或者是不让老百姓泄露被扣留的悲惨遭遇。但就连这样的理由,也是不存在的。其一,他们的伏击战已经打完,而且是全胜,不存在再泄密不泄密;其二,如果说被扣留的老百姓的悲惨遭遇怕被泄露,那么,他们随之而来的对神仙岩的手段,则比用枪炮屠杀更令人发指。
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实行大屠杀的事,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正因为太多,反而让人不相信,反而让人非要去找出个为什么来,反而能让屠杀者矢口否认。
后来他们驻扎在老街的一位小队长说,他们是拿这些老百姓,来试一试缴获的国军某部的枪和子弹,到底还能不能用!
我母亲在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看着外面的星星时,心里忐忑不安。她想着农户这一家子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好了只住一晚就回来的呀。
母亲掐着手指算着他们走了的日子,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难道会在娘家住上这么多日子?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是做女儿的单独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也有,但这是他们全家回娘家,即算是女儿硬被留住了,那女婿也会带着几个大的孩子回来的,这是乡下走亲戚的不成文的规矩。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难道……母亲不敢想下去了。
躺在母亲怀里的三弟哼呀哼呀地叫了起来,大概是饿了,要吃奶。母亲解开胸襟,将奶头塞进三弟的嘴里。璀璨的星光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射在母亲饱满而又白如凝脂的乳房上,也照着端庄美丽而又充满忧虑的母亲的脸庞。
三弟那几声哼呀,使得非常警觉的大姐立即醒来了。
大姐一醒来,就把我推醒。我们两姐弟同时坐了起来。
大姐虽然才刚满十岁,但她完全继承了母亲的优点,属于那种特别懂事、能干的假小子。
我母亲生她时,因为是头胎,我父亲守在门外面,寸步不离。他倒不是担心我母亲生头胎难产、出意外,而是在等着要一个儿子。当房内终于传出婴儿的啼哭,我父亲冲进房去,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往婴儿的胯里一探,当没探着小鸡鸡时,父亲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将房门“砰”的带上,震得窗棂上的纸“沙沙”作响。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房子,是租住在乡里,铁青着脸的父亲竟从乡里一口气走到老街,走进老街的一家酒店,赊了一碗酒。从不喝酒的他,在酒店整整坐了大半夜,直至酒店老板实在是要关门了,再三请他老人家回去,他才离开。
我母亲也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给夫家生个儿子的“罪孽”,她当即自己做主,给我大姐起了个男孩的名字,并从此将我大姐做男孩打扮。母亲说她要等我大姐到“来红之年”,再恢复她的女儿本相。母亲这样做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她不愿让人知道她生的是个女孩,她坚信她生第二个、第三个……时,肯定都是男孩!二是她知道女孩的苦处,从小就要低人一等,她要让她的女儿完全享受与男孩同等的待遇。但她又没有别的办法,她就只能将女儿唤做男孩,扮作男孩……
母亲的这一招,不但使得我大姐少受了许多歧视,就连她自己,也抬高了不少身价。因为是租房子住,只看哪里便宜就往哪里搬。一搬到新地方时,就没人知道我大姐是个女孩。新地方的人一把我大姐当成男孩,就夸我母亲会生,数落某某女人、某某女人全无点用,只会生些个和她一样的。当母亲终于跻身于老街时,老街的人也几乎全都以为我大姐是个男孩。
父亲在这一点上还算配合,也不将他的老大其实是个女孩这事说出去。加之我母亲又真的为他生出了男孩,他就更加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