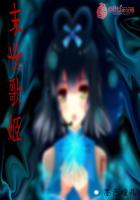然而,父亲仍然把我大姐看成以后反正是个“赔钱货”。只是我大姐也真的是以男孩自居,在外面敢和野小子打架,在家里敢当面顶撞父亲。当然,她之所以敢于顶撞,一则是顶撞的事她确实有理;二则,也是最主要的,有母亲在她后面撑着。她稍微大了一点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参与,且讲得头头是道,也干得有条不紊,终于使得父亲都有点怕她。她的地位逐渐上升,上升到了相当于当家的“老二”,除了母亲就是她。
我大姐在越来越懂事后,和母亲又可以说是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首先是母亲坚决支持她读书,从小就教她识字,算数。她考进县立完小,进校直接就读三年级,各科成绩却都是第一。当她又跳级念到高小时,父亲就不让她读了,父亲说女儿家识得几个字就行了,已经登上天了,每年要拿谷子去缴学费,哪里有那么多谷子缴!那时家里还没能开铺子,父亲要她回来去帮工;母亲却说,她的儿子(母亲从来不说女儿)就是要读书,就是不能一辈子像她父亲一样去帮工,只要儿子读书得第一,她就是累死也要供儿子上学!父亲为此大闹,且喊来他的兄弟,力诉休学能给家境带来的好处,力诉继续读书是浪费谷子,将会给家里带来的种种不利,到时候“家将不家时”可别怪他!父亲以为自己大闹,再加上兄弟的干预,就能迫使母亲让步,最后几乎闹到分家,结果还是母亲胜利。母亲胜利的举措很简单,她做了如下三件事:第一,打发我大姐上县城学校,不要回家,免得心烦,影响学习;第二,上学不就是要学费,要生活费吗?母亲对大姐说,学费、生活费按时由妈托人给你送来。打发大姐走后,母亲开始了第三,将愤而在外找人评理的父亲喊回,面对面坐下,说:“你不是要分家吗?那么现在就分,你去把你的兄弟喊来,哪个锅子该你拿,哪个鼎罐该归我,分清楚了,若有不公平处,也莫怪我不念夫妻一场!”
这分家其实就是离婚,但其时还没有离婚这一说。而分家实在也是简单得很,因为当时我父母亲一无房子,二无田地,就有些煮饭和睡觉的家什而已。而我母亲因为与人合伙打豆腐卖,已积攒了几个钱放在只有她知道之处。母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做好了“以防万一”准备的。
父亲见母亲真的要分家,慌了神。不惟是父亲心里清楚,倘若真的分了家,他到哪里再去找一个有母亲这么漂亮能干的女人?就连当时还只有五岁的我,也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甚至觉得,母亲为什么不和另一个叔爷或伯爷成一家呢?等我长大一些后,我的亲叔爷,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弟弟,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我说,那个村子里,有你母亲的一个相好哩!他原来也住在街上。我一听,竟惊讶地脱口而出,说:“啊,我母亲真是了不起!”这是我仿照我那读过书的大姐的口气说的。紧接着我要他立即陪我去看一看我母亲的相好,我认为我母亲的相好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伟丈夫,结果弄得叔爷很是尴尬,连忙说那人早就走了,离开白沙不知去什么地方了。而我想知道我母亲的相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的念头,反而更加强烈。
分家以父亲的再三赔不是而宣告结束。其实母亲倒是真的想分家,但她不能分,她知道如若真的分了家,她也许会幸福,但对儿女却不一定是好事。她一心为的就是儿女!
十岁的大姐跟着母亲借宿在外面,就知道时刻得保持高度的警惕。她一爬起来,就对母亲说:
“妈,是日本人来了吗?”
母亲说:
“没什么事,你睡你的吧。”
大姐说:
“妈,你到这时候还不睡,肯定有什么事!”
母亲说:
“要说有事,我是想着这一家子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们莫非……莫非出了什么事?”
大姐说:
“是啊,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不等母亲回答,大姐又说:
“妈,你不用担心,他们拜完寿,说不定又到别的亲戚家里去了呢!”
母亲说:
“我心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但又说不出究竟是哪方面的……”
大姐说:
“妈,他们不会有事的,不会的,你还是睡一下吧。”
尽管有着我大姐的宽慰,母亲依然忧心忡忡。
江边,传来一阵野狗的狂吠。
野狗的狂吠渐渐消失后,有着星光的黑夜显得更加寂静。
母亲见我三弟噙着奶头睡着了,便将三弟轻轻地放到床上,她点燃油灯,往堂屋里走去。
我大姐紧跟着下了床,从母亲手里接过油灯,照着母亲,陪着母亲。
母亲走到堂屋里。堂屋里除了设有神龛,还供有一尊观音菩萨。母亲点燃几根香,插到香炉里,而后双手合十,鞠躬祈祷,求观音菩萨保佑农户这一家人平安回来。
祈祷完毕,母亲又拿起摆在观音菩萨旁边的一副卦,口里念着:“菩萨显灵,我虽不是这家的什么亲戚,但这一家子都是好人,求菩萨大发慈悲,送我一个宝卦,他们明天就能平安回来了。”
母亲要求的宝卦是一片卦心在上,一片卦心在下,可母亲将卦往地上一扔,却是两片卦的卦心都扑在地下,是个阴卦。
母亲心里有点急了,喃喃念道: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难道真要出事……”
母亲正要再打一卦时,蓦地,只听得一片闷雷般的轰响,似从天边滚滚而来。
“妈,这是什么声音?!不是打雷吧。”我大姐问母亲。
“是炮声!”母亲手里的卦掉在了地上。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炮声越来越密集,夹杂着机关枪和步枪的响声,还有的炮弹似乎就落在扶夷江里,好像能听见江水被炸起的扑腾。
枪炮声是从老街后面传来的。
日本兵向进入伏击圈的国军某部开火了。
“他们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呢?”母亲不无惊恐地念叨着。
大姐忽地就去开门,要往外走。
“你到哪里去?!”刚刚还似乎害怕不已的母亲见大姐往外走,立即像变了一个人,厉声喊道。
“我得去看父亲,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大姐回答说。
在这危难已经来临的时候,大姐头一个想到的人还是父亲。可是她这一去,之所以被日本兵抓住,却是因父亲挡住了她逃跑的去路。
七
大姐刚要走出门,母亲说:
“你现在不能去!”
“为什么?”大姐不解地问。
“现在情形不明,到处是枪炮乱飞,你先别出去,什么时候我要你去你再去。”
母亲将大姐拉回身边。
这时候我已经赤着双脚站在床下,呆呆地听着那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七岁的我不知是被吓坏了,还是被那像鞭炮一样炸响的枪炮声吸引住,总之是傻傻地完全不知所以。
母亲对我喊道:“快把鞋子穿上,夜里地上凉。”她一把将我掼到床上,给我穿上鞋,套上罩衣,然后几下就把该随身带的东西捆扎成一个包袱,将仍然在熟睡的三弟用背带捆到背上,又将通往后山的后门门闩拉开。这一切,母亲在片刻便全部做完,利索得像一阵风。
母亲坐到床前,她背上背着三弟,左手将我揽在怀里,右手抱着大姐,开始了她的紧急应对安排。
在枪炮声掀得房屋都有点簌簌作响的震动中,母亲说:
“你们不要害怕啊,灾祸反正已经来了,来了就不怕,怕也没有用。你们都得听妈的,知道吗?”
我和大姐同时点了点头。
母亲先对我叮嘱道:
“你要时刻不离妈的左右,我往哪里跑,你就要跟着跑,路上不许哭,不许叫,妈要你躲到哪里你就躲到哪里!躲起来的时候不准做声,这就好比打仗,你要听命令!”
母亲说一句,我就做出懂事的样子点一下头。母亲说完后,我补了一句:
“妈,我倒是不会哭也不会叫呵,可要是三弟哭起来了怎么办呢?不就把日本人招来了吗?!”
母亲说:
“你三弟只要有奶吃,他就不会哭的。”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好像才放了心。但心里却仍在想,妈,你可要时刻都有奶给三弟吃嗬!
母亲又对大姐叮嘱道:
“你是老大,也是娘最放得心的。娘最不放心的其实还是你那父亲,他太弱,可又太倔,他弱起来时没有丝毫主意,他倔起来时又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所以你要跟他到一起,照应他。你跟他在一起时,又不能和他吵哪,你和他吵起来,他又会什么都不顾的哪。”
大姐说:
“那我们要分开啊?”
母亲说:
“对,都到一起太扎眼,反而不安全。况且现在你父亲一个人在街上,也到不了一起。到时候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你找到他后,千万千万不准他上神仙岩哪!你和他到你白毛姨妈那里去。我们也到你姨妈那里去,我们在你姨妈家里会合。”
母亲这么说着时,真像一个指挥官在下达命令。
聪明的大姐突然说:
“枪炮声好像是从老街后面的山上打出来的,我们还住在大山里的姨妈那里跑,太冒险了吧!”
母亲说:
“这一点我早就想到。按理说,日本兵来了,应该先占领老街,可他们却不占,这里面有名堂,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打谁?也没见有中央军过。莫非是在拿乡里的老百姓当靶打?这些暂不说,正因为他们先在老街后面打,打完后,肯定会冲进老街,然后就是往这边来。你想,他们在那里打完了仗,还会呆在那山里吗?他们要是不走,那就是扎在老街,再往这边进发。我们反而往那边去,不正是没有了日本人的地方吗?再说,你姨妈在八十里山,日本人要是在那大山里,我们这儿能听见枪炮声吗?所以,只要能够到达你姨妈家,就会没事!”
大姐觉得母亲说得有理。可她又说:
“妈,你要背着三弟,又带着二弟,还有一个包袱要提,你太累了啊!我在你身边,就能帮你背三弟,帮你提包袱啊!”
母亲说:
“你看你,会说乖巧话了吧。枪炮声刚一响,你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父亲!我说到底是亲生的哩!现在却来说帮我了。你妈不要你担心,万一危急了,我不晓得把包袱丢掉啊,丢掉点东西有什么要紧,只要救得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也都给我记住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要先顾东西,而要先顾命!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母亲又特别指着我,说:
“你和你三弟,以后都会长成男子汉的,男子汉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顶天立地!”
母亲说完,左手把我抱得更紧,右手把大姐也抱得更紧。
后来我想起母亲的这几句话,我觉得这是母亲给我上的最好的一堂人生教育课,那就是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来我又想,母亲这句话里还有许多没说完的意思,那就是她嫁的男人太弱,太不像个男人样。她这一辈子,在婚姻上,实在是太委屈了自己。如若依她的性格,她完全可以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不顾,完全能够将已经建立的家庭打碎,哪怕是陷入如利刃的舆论!她也会将那利刃折断。可是不知为什么,母亲却自始至终地当了家庭的“维持会长”。虽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但我宁愿她不为孩子,不为我们。在我长大成人后,我曾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母亲,母亲笑着说:“要不是为了你们,就算是三个你父亲那样的男人,我也早就将他抛开了!唉,唉,那时候,那时候,我……”母亲抓起衣袖,抹了抹带着泪花的眼睛。我清楚母亲没说出来的话,那时候,那时候,想着她的男人实在不少,即使是她已经成了母亲。
……
星光,终于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天,却终于透出了蒙蒙亮色,枪炮声渐渐弱了。
母亲毅然地松开大姐,把她轻轻地一推,说:“你可以走了,不要从这个石码头渡江,要沿着江边,从香炉石往上跑,再过江。还有,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女的!”
大姐应了一声,机灵地往外一跃,不见了。
八
当日本人把陷入埋伏圈、几乎不可能有还击之力的国军某部全部打死后(他们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俘虏,也不留下一个活口,因为老街和四乡幸存下来的老百姓没有见到一个被俘的穿黄军装的人),枪口转向了被扣留的百姓,枪杀百姓更为快捷,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活着逃出来,包括我们借宿的那家农户六口,包括那个只有三岁的小女孩。
母亲要大姐不要从石码头过江的话完全正确。当枪炮声稍一减弱,街上的人便纷纷往江边逃来,纷纷争抢着从石码头处过河,乱成一团的人们已经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渡过江去,赶快藏进那神仙岩。似乎只要一进了那神仙岩,就是进入了安全之处。
然而,过江的人们似乎并未得到神仙岩神仙的庇佑,素讲礼性的人们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已没有礼性可讲,也不可能讲礼性。在无人组织、无人指挥的混乱中,不断地有人因拥挤而落入江中。
不要以为住在江边的街上人都识水性,恰恰相反,他们中识水性的不多。街上人大概正因为在江边住得太久,对从身边日夜流淌的江水反而有两大畏惧,老人们对子女的训诫中便有两条,一是训诫不要到江中洗冷水,洗冷水容易得病,而这得病,正是最可怕的事之一,故无论是街上人,乡下人,都有一句口头禅:张飞猛子不怕死,只怕病;二是训诫不要到江中划澡,这划澡就是游泳,说每年都有划澡的被淹死,落水鬼年年找替身!学会撑船一世就包用了!所以街上人会撑船的不少,会划澡的不多。
划澡的本事,只有这个时候方能显出它的用处。可事后即使有人提出为何当初不让我学划澡的质问,老人们也会振振有词:“谁知道要逃难哩?谁知道日本人要来哩?”
在不断有人落入江中的混乱之际,一条平素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汉子——老街人爱说,他有什么本事哩?他一不会做生意,二不会节省,就会在涨大水时,跃入江中捞些个浮财,捎带救几个人上来,得些谢礼,讲话没大没小的猛子——从岸边拥挤的人群中冲了出来。
这条汉子,或曰猛子,对着拥挤的人群又是大喊,又是大骂。他大喊的是不要挤,不要挤,再挤下去谁也过不去!他大骂的是街上管事的哪去了?他妈的平常只晓得拿着撮箕来收税粮,日本人一来他妈的就不见影了!为什么不多备几条渡船?他一边喊一边骂,要会水的先下水去救人,说完就将几个会水的人推下江去;他要人将扮禾的扮桶统统拿来做船划,将捆扎在吊脚楼下、大水来时用以护身的划子、木排,统统拿来渡人,谁要是不肯拿他就先放火烧了谁的家!他又要腿脚快的干脆往上游跑,跑到泥弯码头去渡江……他这么喊着骂着,拥挤的人群开始有了些秩序,然后他将衣裤脱得精光,露出一身紧邦邦的肌肉,几把将衣裤盘缠到头上,跳入江中,指挥渡船、扮桶、划子、木排往对岸划……
这条汉子,或曰猛子,倘若与人当面相见时,还是被喊做二爷。
二爷没去神仙岩,他说他懒去得。他说他就在这江边游荡,日本人奈他不何。但二爷后来被说成通日本,受了几十年的磨难,最后还是死在这个汉奸的名上。可我在后来却想,这位二爷,应该就是我母亲年轻时的相好。
大姐赶回老街,老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有些铺门上了锁,有些铺子却大敞开着,显见得走的人已是什么也不顾了。
大姐想着父亲可能已经跟着逃难的人跑了,她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她走到自己家门口,却发现铺门紧关,不过不是从外面上锁,而是从里面关着。
父亲是关着铺门把他自己关在里面。
大姐忙捶门,喊父亲。
她使劲捶,使劲喊,里面却无人应答,而且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姐急了,慌忙绕到屋后,后门也是从里面关着。
大姐又捶后门,又使劲喊,仍然没人应答。
大姐抬脚踹门,想把门踹开,后门虽然没有前面的铺门结实,但要凭一个十岁孩子的力气把它踹开,只能是徒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