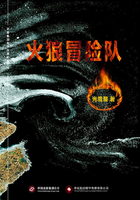二爷说:
“你干等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我这一去也不是一会半会的事,我非得把情况全弄清楚了再来。干脆到明天晚上,你再到这里来。还有一点,你一定得听我的,你千万别直接到老街来找我,万一你也被他们抓去,那你家就没有一个能做决断的人了哪!”
这话说得我母亲心里热乎乎的。什么时候,我父亲也能对她说句这么样的话呢?
母亲还想再说点什么,可二爷已经迈开了步子。
二爷走时,我母亲又对他不放心了,连连嘱咐说:
“你自己也要当心哪,小心哪,有事来和我商量哪,不要独自做主哪,两个人的主意总比一个人强哪……”
二爷连头都没回,只回了一句话:
“你放心,明天晚上在这儿等着我就是了!”
二爷走了。
我母亲目送着二爷走后,独自一人在月亮谷的草坪上又坐了很久,她应当是浮想联翩,也许是想着自己怎么就没有找上二爷这样的丈夫,偏跟个我父亲那样的人过一世;也许是想着二爷这个人她算没看错,算是认准了,同时为自己平素对二爷的做为感到欣慰,到了关键时候,二爷终于能为她挺身而出;也许,她在为二爷的安全担心,万一二爷遭遇不测,她将失去这唯一一个可以与之商议,并能为她做决断的人;也许,她在为二爷祈祷,祈祷菩萨保佑二爷能打听到我大姐的下落,甚或能将我大姐带回来……总之,她坐了很久后,才起身,才慢慢地离开月亮谷。
……
第二天晚上,我母亲准时来到了这个月亮谷,可是二爷没来。
第三天晚上,还是不见二爷的踪影……
十三
在我母亲晚上出去,清早回来的这几日里,我父亲对母亲产生了莫大的怀疑。可是他不敢明说,也不直接问一问我母亲到底打听到了我大姐的什么情况没有,而只是暗地里嘀咕,却又故意能让我母亲听到。他嘀咕的大致意思是,这叫什么女人,一到晚上就往外面跑,谁晓得跑出去干什么好事呵,唉,唉。可我母亲根本就不理睬,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有时候他实在嘀咕得太烦人了,我母亲就蓦地迸出一句:“我是去会汉子去了,你要怎么样?!有本事你出去啊,你去把我儿子救回来啊!”
我母亲这么一说,我父亲就不做声了,他最怕的就是提到我大姐。可用不了多久,他又会嘀咕起来,这回嘀咕的是:“会汉子你倒是不会哩!你不晓得白天出去,晚上回来啊……”
母亲因为连续两个晚上都没会着二爷,完全不知道我大姐的情况,心里焦急不安。可是她又不肯将她自己的计划说出来。她的计划是,如果这个晚上还没见着二爷的面,她就要单独行动,闯进老街去!
我虽然不知道母亲正在下着的决心,但我知道母亲是在为我大姐焦急,于是我靠到母亲身边,说一些其实没有任何作用的安慰话。母亲将我搂到怀里,反而说着些要我别怕,也别担心,说我大姐一定会完好无损地回来的话。在母亲的怀里,我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可是就在母亲怀里睡着之后,小小年纪的我,在这个白天,做了一个非常可怕而又奇怪的梦。我一从梦中惊醒过来,就对母亲说:“我怎么做了一个这样的梦,这样的梦?”
我梦见一只饿极了的鱼鹰,在和一条在干涸的池塘里喘息的鲇鱼搏斗。
我们老街后面铺着石板的小道,是沿着一条溪流通到一口池塘的,池塘里的水再往江中流。小溪两旁本是一片蒸腾着雾霭的黄绿色的水草地,闪耀着水珠的淡白色光点。池塘里的水呈醉人的绿,醇醇地诱人。可是我梦里的小溪全干涸了,溪边的水草是一片枯黄。池塘里的水也只剩下潮润的泥巴,和一条将长长的鲇须紧贴在泥巴中,露出苍黑背部的鲇鱼。这条鲇鱼拼命挤攒,希冀在泥巴下面挤攒出一汪清波。
我梦见老街上空的天怎么竟漆黑得像口棺材,而这棺材蓦地被劈开时,兀地飞出了一只鱼鹰,这只鱼鹰尽管在如同布满鬃毛的脊椎骨一样的树林中歇息了一晚,但因为饥肠辘辘而彻夜未眠。它奋力振翅飞出枯竭的树林,第一件事便是寻觅食物。然而它看见的,只是被烤晒得爆出了一道道裂缝的老街。这些裂缝又深又干,如同让干渴折磨的嘴唇一样。它闻见的是炽热的干风,干风中透着杀人的铁枪的气息,以及嗜血的刺刀的腥味。
鱼鹰极不甘心地竭力在空中盘旋,鱼鹰一会儿左翅在上,一会儿右翅在上,它知道自己体内的能量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它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跌落到爆开的裂缝中去,它再想振开双翅重上山冈已经不可能。为了自我生存,它必须捕获另一个生灵。正当它的希望如同老街四乡田野里的庄稼一样枯萎了时,它不经意地瞥了瞥池塘一眼,那口池塘,它从来是不屑一顾的。就在它不经意地一瞥时,它发现没有水的池塘里有一条正在蠕动的鲇鱼……
我在这个小小年纪做的这个梦,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至于我一直没有忘记。而最奇怪的是,我的这个梦竟然印证在了我白毛姨妈身上。
我在对母亲说着这个梦时,白毛姨妈走拢来听。我说完后,母亲也无法判断这个梦的吉凶。她只是说小孩子有什么梦?是野梦三千呢!母亲说的野梦三千,是指小孩乱做的梦是算不得数的,无吉凶可言。但母亲这是在宽慰着她自己的心,她其实判断出这个梦不是个好的兆头。
当我母亲在为这不是个好兆头的梦紧蹙眉头时,白毛姨妈却笑了起来。白毛姨妈说:
“哎呀呀,什么干涸的池塘,什么鲇鱼,什么鱼鹰,老二你是见着了我家后面竹林里的那个池塘,那个池塘不正是干得没有水了吗?原先那池塘里是有鱼的,很多很多,当然就有鲇鱼哪!我这山林里哪天没有老鹰在飞,天天都有的。老二你个小孩子,会做什么梦,还不是瞎想,想出这么个梦来。快别说了,别说了,省得又烦了你妈!”
白毛姨妈这么说时,我用心地想了想,我确实是跟着母亲从白毛姨妈家后面竹林里那口干涸的池塘走过,我也确实看见了在池塘上空飞过的老鹰,但我没见着鲇鱼啊!而我最喜欢在白毛姨妈厨房的小水道里玩水,怎么就没梦见这条流淌着清水的水道?我最喜欢拿吊桶在白毛姨妈打出的那口很深的井里吊水玩,怎么也没梦见这口打得很深的井呢?我确实是在大白天做了这么一个梦,我并没有瞎想啊!
然而,正因为我这个梦,正因为母亲认为这不是个好兆头的梦,母亲把她和二爷会面的事,把二爷失约,她决定晚上再去一趟,如果还没碰见二爷,她就要独自行动的事,全告诉了我白毛姨妈。
白毛姨妈说:
“姐,你讲的那个二爷是在蒙哄你吧,在眼下这个生死关头,他顾自己只怕还顾不赢哩!你就真的把他的话当真啊?!”
母亲回答说: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二爷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或者有什么意外,来不了月亮谷。”
白毛姨妈想了想,说:
“姐,那就这样吧,今晚上我陪你去,如果再没见着那个人,我两姊妹也好有个商量。”
我母亲同意了我白毛姨妈的意见。可谁也不会想到的是,我白毛姨妈跟着我母亲这一去,不但再没能回来,而且悲惨至极。
我白毛姨妈的命运,真的好像应了干涸的池塘里那条可怜的鲇鱼落入了鱼鹰利爪的梦境。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真的是在看见了鲇鱼和鱼鹰的搏击之后,才惨遭杀害的。以至于我怀疑自己的那个梦,到底是事先做的呢,还是在我白毛姨妈惨遭日本鬼的轮奸、肢解、身首异处之后的臆想。
这个晚上格外地黑,黑得让人心悸。
母亲说月圆的日子都过去这么多天了,是该到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日子了。
我白毛姨妈离开了她那嫁到八十里山后,辛勤构筑起来的宽敞的茅草屋、亲手挖掘的水道和引来的潺潺流水、亲手打出来的水井,和那片有着青翠的竹林,有着幽静的小道的山坡。
白毛姨妈跟着我母亲来到了月亮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