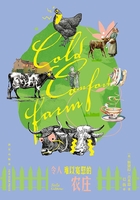巧巧本来是蓝禾儿的嫂子,当工程兵的哥哥死了以后,她成了他的媳妇,他们两个是用眼泪粘和在一起的。
巧巧大他两个月,刚交三十,头发就花了。看她现在,你咋样也想象不出她的当年。巧巧嫁到蓝家时间不长,南塬上就传开了一句俏皮话:“黄家湾的柳条子,蓝老大的辫梢子。”黄家湾的柳条子,是说黄家湾出的毛柳好,条子又柔又长,编筐织箕都是好材料;蓝老大的辫梢子,是说嫂子巧巧模样儿长得受看,不光模样儿好,最招人的还是那两条大辫子,又黑又长,一直垂到腰眼上,走起路来扎着红头绳的辫梢子一跳一跳的,象两只蝴蝶飞。哥哥当兵的第三年回家和她结的婚。家乡的习俗,姑娘出嫁,再不兴留辫子,巧巧拿把剪子要铰头,让哥哥挡住了,他说铰了可惜。巧巧留住了辫子,蓝禾儿心里高兴,他也觉得嫂子留着辫子好,好看。
结婚不久,哥哥就回部队上去了,家里只剩下了爹、巧巧和他三个人。蓝禾儿从小没妈,他们兄弟两个是父亲一手带大的。家里没女人,再富再有,也显得凄惶,出门一块冷馍,回家半瓢凉水,没点热气儿。自打嫂子进门以后,蓝禾儿慢慢体味到了别样一种滋味,这滋味,在他走过的十八年里是从未感受过的,他觉得熨贴、温暖、甜丝丝的,他觉着父亲和自己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着一种温存的约束。“甭吃冷馍!”“甭喝凉水!”“把衣服脱下来搓搓!”嫂子对他们说,他们服从着。以前他们住的是窝,现在,有了女人,象个家了。
那时候,蓝禾儿已经有了相好的,她叫冬云,是邻村的。他们在一个学校念过书,蓝禾儿上初三的时候,她初一。蓝禾儿初中毕业回家种地一年多了,她还在中学念书。学校在南塬上,离她家远,刮风下雨天回不去的时候,她就吃住在蓝禾儿家,和嫂子睡在一起,嫂子贤慧,拿冬云当客待,专拣好的给她吃。
天长日久,他们好上了。
“禾儿,你有个好嫂子,我都眼热。”冬云吃着嫂了扯的长面,对蓝禾儿说。
“我哥有福。”蓝禾儿说。
“你爱她不爱?”
“爱。”
“爱她哪点?”
“她心眼儿好,不毒,知道敬老的,知道疼小的。”
“还有呢?”冬云歪着头问。
“还有……好处多呢。”
“模样儿也好。”冬云笑着说,“怀娃了还水灵灵的,象刚打苞的桃花。”--那时候嫂子已经怀孕。
“性子也绵。”
“……”冬云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她用筷子挑着碗里的面,过一会儿,问,“我呢?”
“你也好。”蓝禾儿笑着说。
“我俩比,谁好点?”
“你比不上嫂子。”
“哪点比不上?”
“哪点都比不上。”蓝禾儿开玩笑说。
冬云不说话了,手中的筷子也停下了,她望着院子角上那颗挂满青杏儿的杏树发愣。蓝禾儿也没吭声。嫂子正挑着两桶泔水,往猪圈走,她的背上跳动着两只灵巧的蝴蝶。
“我照着嫂子的样子学。”冬云红着脸说。
“你真好。”
“模样儿可学不上,人明明一辈子”冬云试探着说。
“谁说你丑!”
“我啥时候也长不白。”冬云用手搓着自己的脸说。
“要那白干啥呢,心实比啥都好。”
蓝禾儿和冬云还都处于春心初荫的时期,他们谁都没有说谎,他们的心还和高邈湛蓝的天空一样明净,生活的尘垢还没有将它们污染。
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过去了半年,巧巧穿件肥肥大大的衫子也挡不住下身的那个小鼓包了。她依然担水,做饭,洗衣服,喂猪,跑到山上去拾柴挑猪菜。
“跟你嫂子说说,出力气的活儿甭干了。”父亲对小儿子说。
“嫂子,往后,出力气的活儿甭干了。”禾儿对巧巧说,他指指地上的扁担潲桶、“以后我来担。”
“这哪能行,哪有男人干这个的!”巧巧说。她停顿了一下,脸忽地红了,她说,“他叔,闲下来给队伍上写个信,日子快了,让你哥给想个名字,生男叫啥,生女叫啥,到时候要上户口哩。”说完,她勾下头,羞红脸走了--她在娘家小小年纪就爬锅头,没念下书,不会写信。
禾儿给哥哥发了一封信。
六月天下冷子。他刚把信发出去,就传来了哥哥因公牺牲的噩耗。
蓝禾儿记得,那时候还在学大寨,他被征到北塬上修人造平原,垒堰,三天没回家。第三天回到家里天已擦黑,一进院门,他就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空气,出奇的静,出奇的闷,除了猪在圈里拱食的声音,再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心里不由一阵紧张。走进屋后,最先看见的是嫂子的背影,她坐在外屋灶间的风箱前,脸朝着墙。最让他吃惊的是嫂子的两根辫子不见了。他进屋时,她也没动弹,仍然呆呆地坐着--往常,她从来没有这样过。
“嫂子,出事了?”他似乎有了什么预感,赶紧问。
巧巧的肩膀忽然猛烈抽搐起来,她用手绢紧紧捂着嘴,堵住悲恸的哭声。
蓝禾儿掀开里屋的门帘,一眼就看见了挂着黑纱的哥哥的遗像,看见了桌子上的供果、香火……
哥哥是在一次坑道塌方中被石头砸死的。
巧巧一下子老了许多,几天工夫,脸就瘦了一圈儿,也不再那样光润。父亲整天长吁短叹,把更多的时光撂在地里,他怕走进屋子,他怕看见媳妇忧戚的脸。她依然喂猪,做饭,依然洗衣服,拾柴,不过不再笑,不再说话就脸红。她的长辫子没有了。经常一个人坐在哥哥的相片前发呆、流泪。
过了两个月,来了征兵的,蓝禾儿说死说活要当兵,说要继承哥哥的遗志。父亲一开始不同意,嫂子劝爹说:“让兄弟去吧,在家他也憋屈。”结果,蓝禾儿验上了。
走的那天,嫂子拿出一件土布衬衫和一付绣着莲花祥云的鞋垫送给他:“我缝的,我绣的,本打算给你哥的,但用不上了,你拿着。”
蓝禾儿接过衬衣鞋垫,不知说啥好,只觉得眼圈儿发热。
“兄弟,还有件事。”过了一阵儿,嫂子又说,“你念过书,有文化,你哥不在了,你就给娃起个名字吧,快了,要上户口哩。”
“哦,哦。”蓝禾儿嗫嚅着,一阵难受,他沉吟半响,说,“我想了两个名字,不知道行不。”
“你说。”
“要是男的,叫蓝天,要是女的,叫蓝草。蓝天高阔深远,祝娃有个好前程,蓝草香味纯正,女娃子,要的是个好品行。”
“我记下了,这名字好记。”
巧巧和冬云一直把他送到塬边上的那棵大柳树下。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
“走吧,好好当兵,甭操心家哩。”分手的时候,巧巧说。
“我常来着。”冬云说。
蓝禾儿走了,他没有再回头看一眼。他觉得自己的两条腿无比沉重。
就这样,蓝禾儿由陇东的黄土塬上来到了广袤粗犷的戈壁滩上,当了一名边防战士。在服役的四年间,他常给家里写信,他也收到过嫂子托人代写的几封信。他记得,最早一封信上说她已经生了,是个丫头,按他起的名字叫蓝草,登记户口的公社干部说这个名字起得好,不俗。另一封信上说爹病了一次,好得也差不多了,要他甭牵挂;还有一封信上说冬云有意思让他早点回来结婚。其余几封都是措词相同的平安家信。
第四年超期服役有探亲假,他请假回家。除了自已几年攒下的钱以外,又向战友们借了二百来块钱。打算回来如果方便的话,就和冬云顺便把事办了,他跟连里领导说了,连里考虑到边防上回一趟家不容易,也很赞成。
蓝禾儿没有料到,那次回家,遇上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羞辱。
那天,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提着旅行包走上南塬。在离村子老远的地方,就隐隐约约听见了迎亲接轿的唢呐声,离别四年的乡音,唤起了以往岁月的甜蜜记忆。他加快脚步,朝村子走去。一进村子,他就被热闹非凡的气氛包围了,一巷子的男男女女大人娃娃都拥挤在喜财子的院门前,唢呐声和鞭炮声就是从那院子里传出来的。
“哦!禾儿回来了!”看热闹的王泰大爷迎面碰见了他,先是一惊一喜,接着神情马上不自然起来,“快回去看看你爹,四年了……”
“大爷,喜财子办事了?”他问。
“嗯,喜财子这两年发了。”王泰支吾着说。
“怪不得这么红火。”蓝禾儿感慨地说,“媳妇是哪家的?”他问。
“这……没顾上打听呢……”王泰大爷慌张地说,避开了他的目光。
旁边一个六七岁的小娃娃告诉他:“是北塬上的冬云。”
谁?冬云?
蓝禾儿一下子懵了,他木呆呆地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禾儿!”好半天,他才听到王泰叫他的声音,“这种事,想开点。”王泰同情地劝慰着他,“唉,这女子……谁都没看来……”
“大爷,你在。”他向王泰强笑笑,提起旅行包,朝自己家里走去。
他走得飞快,不敢回头看。他觉着背后有许多人在看他,羞他,指划他,他觉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有个老鼠洞钻进去。他家在离村街三里路的塬垴上,这不长的一截路他今天走起来觉得特别漫长。
终于到家了。他推开院门,瘫乏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屋门开了,跑出来一个小女孩,腼腆地看着他。
他朝小女孩努力笑了笑,说:“你是小蓝草,对不对?”
小女孩瞪着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那眼睛真象她妈。
小女孩也笑了,她认真地说:“我也知道你。叔叔,对吗?妈说过,你快回来了。”
“你妈呢?”
“下地了。”
“爷爷呢?”
“在。”
蓝禾儿拉着蓝草,提着旅行包走进了屋子。爹正躺在炕上养神。
“爹!”他轻轻叫了一声。爹睁开了眼睛,一阵欢喜,“呵!禾儿,真的回来了!”
“你哪里不畅快?”见爹躺着不动,他问。
“唉,这号拖累人的病,没办法。”爹轻描淡写地说。
“爹,你得的是啥病?”他狐疑地问。
“就是这瘫病。”
“咋的?你瘫了?”他紧张地问。
“你不知道?”
“几时得的?”
“两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