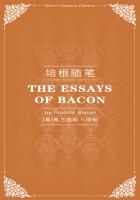九华山的灵气似乎皆在于佛的渗透。漫步九华街,只见一个个佛品都摆上了沿街的小摊,金光闪闪的菩萨铜像,光滑的木鱼、漆亮的佛珠等,佛成为商品,待价而沽,而不同的是,佛的占领似乎使整个九华街虔诚了些,买卖中没有敲诈,没有欺骗,只有和善的讨价还价。录制的佛教圣歌悠扬在九华街的上空,仿佛神秘的声音,使天地变得浑厚和神圣。
九华山所尊仰的是地藏菩萨,据佛经介绍,其是释迦既灭之后,弥勒诞生之前,众生赖以救苦的大悲菩萨,他的誓言是:“众生尽度,方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这里尊供他的佛寺随处可见,1200多年前,由金乔觉创佛寺起,香烟日益鼎盛,现存寺庙83座,佛像6000尊,聚全国四大佛山之首。
这里,佛彷佛仍主宰着众生,几乎每一座寺庙的正堂皆挂有“有求必应”四个金光闪闪的字。而这里的居民也确实是受了佛的荫庇,他们大多靠卖佛教圣品而生活,那些夹杂在游客中的朝圣者,他们五步一跪,十步一拜,满眼充满了对佛的虔诚。
当然,如果真能像地藏菩萨立下的誓言那样“地狱未空,誓不成佛”,那么佛也实在是令人敬仰的!
二、佛道险峻
等九华山,入天台寺,尊供四方神灵,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通往天台正顶的路陡峭而险峻。盘桓而上的石级,如天梯,直插而下,人攀石级,只得将信仰一步步向上挪动。看样子,人与佛的距离实在是高不可攀。当然,我们作为登山看顶的一类,心中无佛,自然天地就显得格外狭窄。
与我们同行的嘉鱼县文联副主席谢忠告65岁,他的攀爬就更有挑战的意味,他笑着说他每一步都把他的年龄踩出一个深坑。
登到半山腰,路彷佛竖了起来,路彷佛缠在了我们身上,紧紧地勒住我们,这时,路实质在爬我们。我们所登的天台正顶位于十王峰,其海拔1342米。九华山的一座座寺庙正是依山而建。佛的神谕仿佛是一道道留给人间的,每一处险峻都有一处佳境,都有一座寺庙,都有一座有关佛的故事。
从凤凰松沿级而上,过慧居寺、长生洞、朝阳庵、翠去庵至观音峰寺,之间半空中一巨石凌空而下,形似观音,衣帽可辨,飘然欲动,后人给其披上一件白色长衣,更觉仙气缭绕,十分神秘。据说观音曾在此观云雾,以测天象。我们踏上神的地盘,俯视下界,只见远处,山影皆无,未有滚滚白雾,而进出的山尖,时隐时现,似要露出,似要被淹没。
上观音峰寺,我们便可以长长地喘息一下了,因为悬在半空中的天台正顶距我们只有百步之遥了,眠眠之中,佛的大手已经开始抚摸我们的头顶。一种征服了山道,征服了自己的胜利感,使我们感到崇高了很多。
正当我们依着石级休歇时,后面传来了“吭唷吭唷”的声音,回头看,只见一些山民挑着沙石正一步一步艰难地朝上攀。粗而硬的扁担被压弯了,但他们的身板却挺得很直。他们黝黑的背上,万道江河在流。据说他们每个人肩上都压着近150斤的沙石,为山上建造新的佛寺,他们将沙石从山下挑到山上,这需要多么大的力量和多么大的毅力呀!他们粗糙的臂膀在太阳下闪着光,他们隆起的肌肉群山般起伏。
看着他们远上的背影,征服山的自豪感顿时消失,在感受自然的强大后,我开始礼赞人的力量,我们开始攀登一种新的神谕……
三一线天的彻悟
过了观音寺,朝上攀,窄窄的山道左侧立起一巨石,极像一个巨大的脚板。同行的导游说,这是地藏菩萨登山累了在这里休息。
爬得满头是汗的谢老说:“神仙不及人,三步一喘,五步一歇,不如我65岁的老翁!”
正在这时,山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是登上了天台顶的游人放的,他们是在庆祝自己登上了如此陡峭的山道?
其实不然。当我们终于过古拜经台顺石级转弯到天台寺时,只见寺左面有“一”字形石崖,过石崖,便有渡仙桥,昔日飘然而过的仙人早已不复存在,而今,一些不辞劳苦的小商贩们在这里安设了一个个小摊点,摊点上大多摆放着鞭炮。小导游让我们买一挂鞭炮在天台正顶燃放。说是绕山的仙人和大神太多,既已登山顶,就应燃一挂鞭,告诉仙人和大佛们,你们已不辞劳苦登上了佛教的至高处。
在我们点燃鞭炮时,小导游还郑重其事得把我们的名字一个个告诉了大佛们。但见天台正顶上的香炉,烟火十分旺盛,熊熊烈烈地彷佛要把天空烧出一个窟窿。不知佛们是否真的听见了我们的声音。
俯首望去,四周的群山却是低下去了很多。绕峰的白雾象是从峰脊上浸了出来。缭绕的雾气中,好像真的隐藏着一些仙人。
我们痴痴地看着那些变幻莫测的雾,只觉得眼前开始朦胧。这时,阳光变得极其透明和纯净,照在脸上像是佛的双手,正对着我们彻悟般抚摸。这就是李白所称的佛光吗?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但不知等待什么?恍惚中,彷佛有一种神的力量正对我们进行皈依……
由天台正顶的天台寺出后门,走过形如青龙的山背,有两青石直立如门,下窄上宽,从下仰望长空,只有隐隐的一线,这就是九华山著名的“一线天”了。
“一线天”彷佛天空真的只有窄窄的一线。两面的青石相对而应,沉重而威严,如两道不可抗拒的神谕。在此修炼的佛徒们,站在此处看那圣佛天堂真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吗?其实向前跨上一步便海阔天高,为何非要讲自己圈于一块小小的佛地呢?当然,一步之遥也许正是凡人与佛的天壤之别。
“一线天”右边的那块青石上鲜血淋漓地写着四个红字:极乐世界!这四个字不禁让我们惊惧。佛的寓意,大概是从“一线天”真正看到了圣佛天堂,那么,修炼自然就成了正果,进入了极乐世界!
站在“极乐世界”处,山风忽然变得极其清凉,一股寒意从脊背后面升了起来,彷佛全身也轻了很多。这是让人肃穆的佛地,这是佛的极乐处,也是人的苦难处。我们作为凡人当然抵挡不了那佛的清凉和神的寒意,我们抱着膀子逃下这神秘兮兮的圣处。绕过天台寺,顺着观音测天的脚印,我们疲劳而惆怅地从仙雾缭绕的佛经走下来。吐一口长气,稳稳地站在凡人所站的山石上,再看百米开外的天台寺,顿感遥远了许多。
1993年7月17日于温泉。
早春之夜
“哇哇哇”
女儿又开始啼哭,妻那听起来很遥远的摇篮曲又从门缝里钻了进来,缭绕耳际,扰乱着我的思绪。
远方的路灯彷佛熄了,又彷佛没熄……
想到一只小船,搁浅在离海水只有几米的沙滩。海水在汹涌。翻滚的海浪咆哮于一片蓝盈盈之中,却没有最后的力量把小船带入大海……谁笔下的意境?是舒婷?还是……
“哇哇哇……”
我开始叹息。作为踏着诗的韵脚冒险而来的我,想起来,不该在二十四岁就匆匆地拥有这样一个爱哭的女儿,这样一个年轻的妻子,这样一个负载过重的家。
妻是中学同学,因与我谈恋爱的缘故,没有考上大学。但她总是甜柔的浅笑,用她的酿浓我们的感情;正是在她如梦的眼睛里,我误入了诗的圣堂,并且在茫然于自己脚步的回声中愈走愈远。而我的名字也开始在一次次退稿中定格成铅字。仿佛所有的诗门都带着五彩的光圈像我展开,走近时才发现,在五光十色的诗门前布满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疲倦了,在疲倦中,我选择了妻子那莹莹低泣的泪光,选择了妻那盛满爱的温床。于是,我有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家庭,有了这样一个不该出世的女儿;于是,无始无终的家务琐事肢解了我的诗趣,无止无休的哭声扰乱了我的诗情……
然而,在我眼里却总来回闪现着一只小船,而我固执地认为这只小船会被海潮带入大海。于是,我仍在诗的韵律的薄冰上走着。每到夜色渐渐覆盖一些人安逸的甜梦时,我仍然固执地坐在黯淡的窗子边,让排排路灯,照亮我的希望……
“哇哇哇……”
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小了,而妻子的摇篮曲也渐渐地把自己摇入了梦乡。我的思路又开始回到那个空泛的主题。我开始静候着灵感的再一次闪射。然而,无边无际的静使挂在墙上的钟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它的存在-
“嘀嗒、嘀嗒……”
我的思路渐渐被来回踱步的时间引入岔道……
猛然想到是星期六,而明天星期天又得加入那些买米买油的长队里了!
我又一事无成地枉费了一个苦恼的初春夜。
原载《江汉早报》1987年4月9日。
我捧着一片红色的秋叶
当南方的雨轻轻地敲打着一个湿淋淋的季节时,当九月风吹过乡野吹过宁馨的夜晚,悄悄地滑进我的窗棂时,我从沾满泥土清香的屋檐下,拾起一片红色的秋叶,庄重而敬仰地把她久久凝望。
我的窗前,沿着柏油路延伸的是茂盛的树,那笔直的树干,在那微风中发出沙沙声响的树叶,那仍在凉雨中深处触角不断向上猛长的树枝,那似乎要穿破天空的傲立的形象,以一种坚韧的支撑力,仿佛要支撑一个时代,一个世界。
然而,在我手中却捧着一片飘落而下的红色枫叶。从那微皱的有些卷曲的叶片,我听见了遥远处缓缓地蔓延而来的秋风,在诗的低诉下,我又仿佛听见了一位外国诗人秋风般弹奏的诗句:“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的,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是的,叶的事业是谦逊的额,总是垂下的,总是纷纷飘落的。她使人想到季节的衰老,想到岁月的流逝。然而,它又使人猛然意识到一个新生季节的繁茂,感觉到在纷纷落下那树干的粗壮,那栋梁之才的雄伟……
我突然想到那些在秋叶纷飞中退了色的浅红的平房,想到了从那简陋的平房里传来的读书声。是的,童年的回忆总是伴着隐隐的读书声轻轻而来的,而不时在童年的读书声里闪现的还有那戴着眼镜,微微佝偻着的老师的形象。老师那缓缓挪动步子的身影那么高大地占据着整个童年时代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