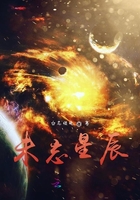你在家里等。你没有挂电话给她。也没有去问老芳。你不想证实。你甚至没有怪她的意思。你很平静。平静得就像死了一般。你平静地等着她。就像一个有耐性的垂钓者,等着鱼上勾。
你又觉得自己像一个柔弱的孩子,坐在家门口,等着父母亲回来。家里静得要闹鬼。
你觉得自己必须去做点什么。你跑进书房,打开电脑。可是你打开了电脑,你又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什么都不足以去做。
邮件收件人:嵇康
邮件发件人:
恭喜!
又是一封垃圾邮件。这下是完全没有署名。
你想起有一次从外滩折进了南京路。你蓦然瞧见一张脸,它探了一下,从浦东发展银行大楼侧面,那石砌墙体边。你愣了一下。那脸陌生,但又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也对你愣了一会,又缩了回去。再没有出现。
他认识我?我认识他?你身处两座巨大大楼间的窄窄的路,静得能出鬼。你的后面就是繁华喧闹的外滩,车流如织,人影憧憧。世界显得不真实。
有时候会突然在你身边出现一个人,跟你说话:恭喜你!
我有何喜可恭的?
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获奖者!您的车牌获奖了。
莫名其妙……让人感觉这世界的一切变得那么荒谬。包括这熟悉的街道,楼房,那块广告牌。
可是那人倏忽又离你而去。你想喊住他,都不知道到哪里喊。
抓不住。
有一次你在路上,迎面汹涌而来的人流,忽地远远瞥见一双眼睛,好像有点熟。紧身紫色上衣,齐肩黑发。你不由自主向她走去。那双眼睛在错落的面孔之间闪着闪着,走进更拥挤的百货大楼。你费力地在人群中跋涉,大楼像张开的大嘴。那双眼睛,紫色上衣,齐肩黑发,消失了,只有不认识的人像虫子向你涌来。撞你的肩,撞你的手臂和大腿。
日光渐晦。你蓦然一惊。一颗单纯的心猛地撞到了黑暗。你几乎要哭出来。
你的神经绷得要断了。
她回来了。开了灯。
你说这老张有意思没有意思。一开口,她就说。
老张!
昨晚后来她去跟踪了老张。她说。老芳和老张在一家咖啡屋见面,她就在远处一张桌子上等。老张和老芳说话时,就一直朝这边瞥。说了一会儿,他就走过来。
谈得怎么样?她问老张。
谈好了。老张应。
什么谈好了。她笑了。是谈恋爱,又不是吃饭,做事情。哪有谈好和没谈好的?
老张说,看来你对谈恋爱,有很深的了解。
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这个老张!
……老张说他还有事,要先走。
她忽然想证实他是不是在撒谎。她跟踪而去。
老张爬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真的急着要去办什么事似的。她也叫上了一辆出租车。跟上那一辆!她对司机说。
司机回头瞥了她一眼。是不是太像电影了?这样的跟踪。
前面的车直奔而去。到了空旷的地带。她陌生的地方。
这里是哪里?她问司机。
司机回答了。地名也陌生。
这条路下去是哪里?她又问。
司机又说了个地名。她仍然陌生。
沿途荒凉。感觉危险了起来。
这跟踪充满危险同时也充满刺激、充满趣味。你不知道危险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你甚至无法想好摆脱的办法。到时候你只能一头栽进去,躺倒在危险的怀里,听天由命。
他会去哪里呢?
我怎么知道?司机答。
她从后视镜发现司机笑了。她的脸猛地热了起来。不是问你……她连忙支吾。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企图骗我们。她说。
你们男人是不是特爱撒谎?她又说。
我不撒谎。司机幽默地说。我是忠实地照着你指引的方向走的,跟前头那车。要撒谎,也是他撒谎。
乐果脸更红了。
司机又说:一个出租车司机要给人不忠实的感觉,那他的车就没人敢坐了。坐他的车太危险。我不危险,是他危险。
乐果的心猛地揪紧了。
前头的车终于停下了。在一个还不算很偏僻的地方。所谓不算很偏僻,是因为有两幢酒楼似的建筑。后面是一座山。老张出来了。他向其中一座楼房走去。他进去了。乐果赶忙付了车钱,出来,跟进去。
原来不是一家酒楼,迎面的是一个很空的大厅,堆着一些杂物。乐果仿佛记得刚才是瞥见外面悬着酒楼牌子的。她已经来不及折出去看。老张已经倏然进了里面。里面是一条小弄。有些暗。她跟了进去。前面是老张的背影。我看你逃得了!
她断定是这一座人家。
也许是老张的家。他说他住在虹口区,他在撒谎!我戳穿了你的谎言。她觉得很激动。
可是在跟一个撒谎的男人打交道,她又有些慌张。
她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像个机警的警察。一个女警察。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警察的素质。她只能是和平环境中的教师,象牙塔里跟学生打交道的教师。她微微有些激动。她在冒险。人生有时候需要冒险。
她终于选定了逃生的路线。按照自己对普通居家环境的了解。她安心了下来,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她跟老张。
老张没有发现她。在前面走着,傻乎乎的样子。是傻乎乎!她蓦然发现,男人有时候是傻才可爱。
弄子很长。非常长。她感觉透不过气来。被谁扼着脖子的感觉。要死了。要死了……
终于走出了小弄。是一片天井。亮。有盆花,有挂衣服的尼龙绳子。没有挂着衣服。很乱,是住家房屋的乱。没有人。
她牢牢跟在他后面,像放着一根长线。放长线钓大鱼。
有一刻,老张好像回过头来了。她慌忙躲闪。他没有掉过头,只是看边上。他的耳朵在亮光中很透明。
他上了楼梯。她跟上去。他的身影很快上了楼梯,消失了。你心一紧,惟恐在这一刹那他消失在她视线之外。
勿宁是她被对方钓上了。
老张没有消失。他在开一个房间的门。难道就是他的家?他住在这样的地方?野地。她觉得自己原来的想法给毁了,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个老张!这就是他要急着去办的事情吗?他开了门,进去了。她上去。里面居然没有他的影子。
他在哪里?她悄然踏进去。步步进入。门忽然关了起来。
老张在她后面朝她笑。她早就是他的囊中物!--这个老张!她说。
你说这男人狡猾不狡猾?她问你。
狡猾。你应。
你没有感觉。
坏不坏?她又问。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应。
你什么感觉也没有。
好什么呀?她说,我可不敢把这样的男人介绍给老芳。我可得给老芳把关!
那你就留给自己吧。
你说什么呀?她叫。你看他那么老。
不是老了才懂得疼吗?
你说什么呀!
啪!一巴掌。
她好像没有反应过来。仰着头,瞧着你。脸颊上渐渐绽出红红的五个手指痕。 (我这是怎么了?你问自己。)
很久,她才猛地捂住脸。那眼光仍从指缝里射出来。好像不认识你。
(我这是怎么了?)
你的手在麻麻发疼。出手是那样的有力,好像积蓄了几十年的仇恨。被我逮住了!被我逮住了!你欢快地叫着。你的头脑却一片空白。轻松,虚脱。
她嗷地叫一声,跑了出去。
你后悔了。
你跑到街上去找她。没有找到。你跑尽了她可能去的地方,她的同事。都没有找到她。
她在这城市举目无亲,除了你的家族。还有就是朴,朴是你的同学也是她的同学。你打电话给朴。朴说:你的老婆又没有交给我保管。
你又问老芳。也没有。
老芳问怎么回事?你不敢说。
怎么敢说呢?说自己的妻子,她的介绍人,跟被介绍的男人搞上了?也许并没有这么回事。她只是过于热心。你愿意相信,是的。你发现了自己的嫉妒。
你奇怪自己怎么嫉妒起来了?已经很久没有了。自从你们结婚以后就没有。从充满变数的一盘没下完的棋,到了永远下不完的棋。你甚至有时候还希望有谁来追追她。
在跟她恋爱的时候,你曾嫉妒过。那时另有一个男生在追她。是体育系的。你们吵架时,她总是叫,后悔爱错人了,不如去爱那个体育系。你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她就应,头脑简单也没什么不好,省得神经病。
确实是。当年,诗人的你头脑发达到了有点神经质的地步。有一次你们吵大了,她真的跑到他那里去。你又恨又怕。你守在体育系宿舍楼前,盯着那宿舍窗户的灯光。那晚上,你发誓不再写诗。
后来她出来了。你给了她最猛烈的爱。你向她显示了强劲的肢体。你的身体一点也不比那体育系的差。你年轻力壮。你简直累坏。
嫉妒是一盅酣畅的烈酒。现在,嫉妒让你渴望找到她。她在哪里?
她终于回来了。你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上床。她背对着你。你扳她的肩。她扭动身子,挣脱了。你又去抱她。你一定要把她搂在怀中。你向她赔罪。她嘤嘤哭了。她这才哭了起来。
这似乎是她结婚以后的第一次哭。结婚前她倒是挺会哭的。是不是她意识到,结了婚,哭的权利也应该取消了?
她更加坚韧地挣扎。好像已死了心,要跟你一刀两断。然后,她又蓦然转过身来,抱住你。
被宽恕气氛笼罩,有一种异常的温馨。像严冬中生起了一堆篝火,感觉特别好。你也抱住她。你用手抚摸她的脸。她的脸上有你的巴掌印。五个手指,一、二、三、四、五,清晰可见。也许是由于那皮肤太白了。从白色底部浮出来。
她的皮肤真白哪。细嫩。这些年来,她几乎没有变。你把它揉皱,又抻平。它揉皱时,骤然变成一个老太婆,你一放松,它又马上变成了年轻女人,你的老婆。
你又去揉皱,恶毒地。你欣赏着她的丑陋形骸。
她的皮肤像橡皮一样富有弹性。那五个手指痕也随着你的抻拉与放松,一下一下绽现出来,像花。
你去锉它。也不知道是要消掉它,还是要触摸它。使劲地锉。起初还沾上口水。口水磨擦干了,手感涩了。你就干涩地蹭。你的心被磨擦得发热,擦出了火。那伤痕更红了,好像要爆开。你简直在践踏。
大凡医生给病人疗伤,都是这种情形,用碘酒洗,用火罐拔,用手术刀剜,用绷带扎,用抗生素,放疗,化疗……一种更大的屠戮。只有屠戮,才能治疗。
你甚至想用指甲刮那伤痕。
你瞧见她疼痛的神情。可是她坚忍地闭上了眼睛,没有缩。像个懂事的孩子。医生最喜欢这样的孩子,懂事,又弱小,你可以尽情屠戮,同时射精一样发泄怜悯。
是我不好。你说。
不,是我不好。她也说。
是我。你又说。
不不,是我!她大叫一声,好像要被人摁进水里窒息,她扑腾着挣扎出来。(她为什么要争这?)
实在是没有车了。她又说。
什么?
那里,晚上没有车。她说。你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她怎么又提起昨晚的事?
你本来就不该去嘛。你说,那么迟了。
人家想知道嘛。她说。网络上认识的人,可靠不可靠,毕竟不知道。
那么,知道了吗?你问。
不可靠。她说。
怎么不可靠?你问。
你发觉自己简直居心叵测。
你看他邋遢得,她说,那床铺简直是鸡窝,还要我给整理……乱七八糟,乱七八糟。
这不是很好吗?
乱七八糟还好?
就因为乱七八糟才好。乱七八糟的床适合睡觉。
我没有。
那你在哪里睡?
我没睡。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不是说了吗没有车了吗?
你根本就不该去。你叫,你跟踪去了。跟踪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追逐?
我没有!
啪!
你又打了她。
这么快。相隔短促,只几个小时。在得到她原谅后,又打了她。简直是不可遏制。简直迫不及待。
好像这打是一种救赎。你惟恐失去了救命的稻草。
我说呢,你怎么会那么热心。你叫道,这些日子来,你怎么不对了。你这样说,好像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她的身上。把粪便倾倒在她的身上。你自己也觉得卑鄙。这些日子来,到底是谁不对了呢?
你的胳膊拎着手掌。立着,被子退到了脚下。你感觉到轻松。很久没有这么轻松了。你是在报复。你是个受害人。
有时候受害者比施害者清爽。他解脱了。他可以胡作非为了。无论他采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
抽对方的嘴巴子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一切都否定了。简捷明了。用最小的动作取得最大效果。一下子就把对方彻底否决了。对方顿时什么尊严也没有了,捂着脸,呆在那里,稀里哗啦捡不起自己来。而打的人,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还可以再一个回掌。手背骨打在对方的颊上,鼻上,嘴上。足够的硬度。淌出血来了。
然后,再一下。她又被挂了一下似的,跌跌撞撞,像一只迷失方向的母狗。
再顺便地扫上一脚。你对自己的动作很惬意。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武功家。你不会武功。你毕业时连基础体育都补考后才达标。你只会舞文弄墨。这样的人一旦感觉到自己竟还能如此手脚利索,还有如此杀伤力,骄傲之心简直膨胀了。也许是那时起,心底就有着一种欲望,要喷薄而出。它被压抑太久了。你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这样的发泄。你渴望暴力。你总想抓住一个人狠揍一顿,揍得死狗一样。
你发现,自己潜意识中有着流氓的情结。
于是,她像母狗一样摔出了床。被窝荒凉。你好像听到她在嘟囔什么。她在争辩?是的。她一定会争辩。你说什么?你低下头,侧过耳去,倾听她辩解。她没有说。她没有在说什么。她怎么不辩解?说她跟他没有关系,说她不是这样的,她根本不是这样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说?
假如她辩解,你就有了可以抓住的更坚实的东西了。你要证明她有,她竭力辩解自己没有。她没有,也就是说,她还是承认你;你恨她,因为你还把她当老婆。可是她不说。
你感到空虚。你把她提了起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其实她一遍也不曾说。)……你说呀!你叫。你把她一下一下提起来,提到自己的耳朵位置。又放下。她仍然没有声音。像一只羸弱的羔羊。
也许是因为她伤得太重?她说不出来。也许她真的无辜。无辜……你也可以相信她是真的无辜。可是即使如此,你也要揍。不是因为她有辜才揍她,而是因为她无辜。(其实是我没有道理。你对自己说。她根本没有跟老张。假如承认她真的和老张,那岂不是彻底绝望了?)
甚至,揍得让她更无辜。土匪?(你与其是要用打来惩戒她,勿宁是以此来抓住她,增强你们的联系。)
你要将她提起来。她慌忙抓住床腿。地上再没有东西可抓。床腿被抓得摇摇欲坠。可是很快就脱落了。她就去抓地面。地面哪里留得住她。她就像死猪一样赖在地上。企图靠自己的重量。可是她并没有什么重量。她的重量根本敌不过你。她无可奈何。她绝望地望着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几分钟前还好好的。你们还互相责备自己。她不明白。她盯着你,好像不是乞求你不要赶她出去,而是想弄个明白。
就是不要你明白!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不要明白!
你把她提起来。像提小母鸡似的。摔下楼去。
那身影流畅地滚了下去。乖乖地。你的神经被拉舒展了。大花瓶倒了,碎了。这是你钟爱的花瓶。彻底碎了。你有一种彻底了结的感觉。
她滚落在楼梯脚下,一块地毯上。那地毯,她每次做卫生都要翻出底来打扫,再用吸尘器吸干净,摆得工工整整。它摆得太工整了,虽然被她的身子蹭歪了,却又跟她的姿势很吻合,很俏地托着她的身体,像水果盘托着一挂葡萄。简直是对你的抗拒。你冲了下去。又将她提起,你张望着。面前是大厅,华贵而典雅。沙发,茶几。你瞅准茶几,摔了过去。为什么要砸向茶几?因为它是什物堆得最杂,最容易被毁坏的心脏部位。你听到了玻璃和瓷器撞碎的声音。像雄浑的英雄交响曲。简直完美。茶几坍塌了。她浑身都是玻璃屑,闪光得一塌糊涂。
你们的身体在地毯上,身下周围碎玻璃闪烁。像祭品。
这样的打,让你获得极大的快感。把自己整个身心给清洗了。清洗得那么痛快淋漓的。
与其是因为自己得到了抚慰,勿宁是因为把自己彻底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