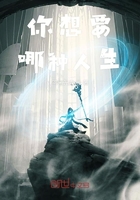很少有人的童年少年过得像我母亲一样奇怪。
姜二南下后,已经脱了军装,进入省宣传部任一名处长。姜二哪是个舞文弄墨的人啊,真是大错特错。不过,组织上的决定,他二话不说,坚决执行。每天姜二都准时上班,分秒不差,却从来不准时下班,在办公室里哪怕只是再扫一次地,他都很满意,对自己满意,他觉得又为革命多做了一份贡献。
但姜二其实对自己的状况一点都不满意,太不满意了,整天心里空荡荡的,老觉得有事需要做,却又弄不清究竟什么事,更不清楚能怎么做。想来是有什么不对头了,肯定缺了什么少了什么。他因此常坐着发呆,不知不觉就呆了,眼睛虚了,木木地望着某个不确定的地点。这时候,那个地点正枪声四起,弹雨横飞,烽火连天。啧啧啧,那才叫日子啊!有一次他对我外婆说:“革命要是迟几年胜利就好了。”话音未落,他的觉悟马上浮起来,“妈的!”他骂了自己一句,甩起巴掌直往脸上摔去,脸上立即起了两片红云,被子弹过的那个洞在周围红云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幽黑。
但过后他并不是再也不说,他还是要说的,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向上向前伸着,伸成手枪状,不停地舞动。他坐在窗前,有气无力地望着外面歌舞升平的场面,叹口气,把手枪状的手指头舞过我外婆的眼前,他说:“不打仗了。怎么不打仗呢?打呀打呀!”抗美援朝如果能把姜二招唤上就好了,偏偏没有,他已经转入地方建设,再也不是军人了。
我母亲姜榕树小时候从来没穿过花衣服与裙子,她穿我外公旧军装改制的小军装。每天早上五点半,我外公口中含着哨子尖利一吹,全家就得立即起来,包括我母亲。即使生病了,正发烧,也得先起来,穿好衣服,然后经测定的确浑身滚烫滚烫的,才能重新躺下。一日三顿也吹哨子,哨声一响,刻不容缓马上拿起筷子;哨声再响,则立即放下碗筷,须臾不可拖延。姜二说,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出人才。他的妻子倒是理解他,觉得这是姜二爱女儿的独特方式。姜二对女儿爱肯定是爱的,种在省直机关内的那棵茁壮成长的榕树可以作证。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他这么呕心沥血,无非是要把女儿炼成一块无与伦比的优质好钢。
但是我母亲姜榕树不理解,姜榕树居然把家看成是渣宰洞,把我外公看成恶魔徐鹏飞。有一次放学后她甚至不回家,一整夜不知去向。我外婆急得都快疯了,在城里的榕树间跑来跑去,到处问:“看到我女儿姜榕树吗?”问得她舌头都抽筋了。
姜榕树后来被她母亲从同学家中找回,姜二肺气炸了,啪啪,他二话不说,便以急风骤雨般的气势重重拍过两巴掌,然后一手插腰,一手狠狠往前一戳,吼道:“关一天禁闭去!”
我外公这两巴掌下去可不得了,那是一双扛枪握炮的有力大手啊,我母亲的小鼻孔里立即流出血来了。我外婆想把她送往医院,我外公厉声喝道:“敢?流点血算什么?以前你没流过血吗?我没流过血吗?关禁闭去!”
我母亲就在她的小屋里关了一天,没吃没喝。晚上我外婆开门进来时,她已经昏倒在地,鼻孔中血已经止了,结成一条咖啡色的痂,像一道伤疤似地挂在那里。
我母亲自从那次之后看她父亲的眼神就喷出火来了,正是这一次,她觉得自己彻底看清了这个家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他是反革命,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在家里说革命最好迟几年成功。”这是我母亲写的揭发材料中最致命的句子,她父亲因此被判刑劳改,她母亲也逃不了干系,一起去了边远山区。城里只留下我母亲一个人,她快乐地加入红卫兵,唱着东风吹战鼓,又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接着就背起行李喊着口号,插队到娥眉来了。
那一段历史现在看来荒诞得不可理喻,其实仅仅隔了几十年,可是在我,却是完全不能弄懂的,仿佛隔着数百年岁月的团团迷雾。
刚开始每个月我母亲都让我给她母亲送去二十元钱,算是许盼望的生活费。我母亲工资那时每月不过五十七元,她给我二十元,给许盼望二十元,剩下十七元是她和我奶奶的生活。好在我外婆拒收了,我外婆说:“拿回去,还给你妈。”我母亲收下退回的钱,第二个月再让我拿去,还是被退回。如此反复了十几次,终于就不再继续了。许盼望在城里长大,她简直有如鱼得水之感,被宠得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时我去那里,看到我外公削好一个苹果,低三下四地求许盼望吃,而许盼望则噘着嘴,恶声恶气地说不吃不吃臭死了!
我都替许盼望难为情了,心里其实也有点酸楚。我外公外婆对许盼望一下子就爱入骨髓里去,许盼望仿佛是一块盐,而这个家则像是一汪腾腾冒气的热水,眨眼间彼此就相融在一起了。可是对我,不知为什么,他们一直隔山隔水地客气着,不苟言笑,也不越雷池一步。我对他们当然也始终保持一份距离感。
所有的女友,不管爱得怎么颠三倒四魂不守舍,我都不往我外公外婆家带。
沙佳邦都觉得奇怪,她说:“你姥姥不想看看我吗?”
我摇头,又怕她误解,只好说:“我姥姥身体不好,怕陌生人打扰。”
其实我外婆虽然瘦小,其身体也许比我母亲都好。她每天一大早都穿着宽宽的练功裤去西湖公园跳交际舞,接着又甩弄一把系着红缨的长剑,英姿飒爽,精神焕发,健步如飞。而我母亲,当年虽然又跳白毛女又跳吴清华又跳英嫂,如今却是怎么都懒得动弹一下了,多举一次手多抬一次腿她都不乐意。娥眉的人看到,中学老师姜榕树每天从家中往学校走去的步子,一天比一天笨重迟缓。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我父亲去日本之后,我母亲可能都没有过轻快的步子。镇上夕阳红中老年舞蹈队搞得热火朝天,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朵奇葩,她们就曾请我母亲去指导。那些把脸用力抹得红红绿绿的老大妈们,当年都曾坐在台下,仰头望着我母亲在台上光彩夺目地舞臂举腿,无限的羡慕与向往之情在心里澎湃起伏。她们挤到我母亲跟前,个个都毫不掩饰地尽情流露出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殷切表情。
她们说:“来吧来吧姜老师你来教教我们吧。”
我母亲姜榕树不为所动,理都不理。
我知道我母亲其实是看不起那些人的。夕阳红中老年舞蹈队参加文艺进社区汇演,舞台就搭在我们家附近。那群突然散发青春与浪漫的老女人在那里又跳又蹦,十分卖力。我母亲去看了一小会儿,她能够到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过大家发现,整个过程,她的嘴角始终有一丝淡淡的冷笑。我不觉得我母亲是对的,她其实把生活弄得很糟,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去年,她过五十岁生日,我替她煮了一碗线面,搁了两粒蛋。我母亲吃了一半,突然放下筷子,眼睛红得像兔子。
我安慰她,我说:“妈,你要把心放宽。”
我母亲又笑了起来,笑得十分短促,她说:“儿子,我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人生好像还没开始,一辈子却完了。”说着,一粒泪叭哒着滴进面碗里。我父亲刚走那两年,我母亲在私下无人时,有过如雨的泪,但后来,就一点点少了,直至全无,如同一口干涸的老井。而这一次,因为一碗长寿面,竟然又溢出了水份。
“如果我姐姐姜辽沈在就好了。”她又说,“我姐姐姜辽沈在,生活就不是这样了。”
我母亲的意思好理解,她觉得如果姜辽沈在,我外公外婆就不至于以那种方式培养她,她最终也不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外公我外婆始终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自己把这一辈子糟蹋掉了,恶果是她自己种下的,不关别人什么事。“你妈妈根本不该嫁给许鹦鹉!”姜二说。我能感觉得出他这句话里仍然含着沉甸甸的一股怨气。
我母亲写揭发信并没有真正伤了她父母,那时候家里人写揭发信又不是稀罕事,大家见怪不怪。而且我外公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确在私字一闪念中讲错话了,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罪该万死啊。我母亲敢于站出来揭发,我外公不恨她,反而为她有这样的政治觉悟高兴。“毕竟是我的女儿啊!”他很欣慰地对我外婆说,“我的女儿就是不一样。”
我外公外婆去了边远山区,心里仍牵挂着留在城里女儿,他们不停地写信回来,教育我母亲应怎样怎样。我母亲从来不回信,甚至信封连拆都懒得拆,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她去了娥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她有点被报纸上描绘的火热生活迷住了。但到来了娥眉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各种各样的虫子先把她吓得半死。幸亏能跳舞,我外婆就是部队文工团出身的,能歌善舞还能打快板拉二胡,我母亲秉承了这个优点,并且发扬光大了。
我外公外婆得知我母亲在娥眉大有作为倒也有几分欣慰,但是后来,我母亲跟我父亲许鹦鹉的交往惹起大祸,许鹦鹉有个不明来历不知去向的竹篾匠父亲,又有个被日本人强奸过的古里古怪的母亲,我父亲说:“我们是革命家庭,跟这种人来往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按我的理解,我外公如果不强烈反对,我母亲也不见得一定会跟许鹦鹉好下去,那时她毕竟年轻,人生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可能性。我母亲在台上多姿多彩地蹦跳,让台下无数根正苗红的男人神魂颠倒夜不能寐,他们中有公社的领导和宣传队的头目。像很多伤痕小说中写道的那样,那些人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就能把美丽单纯渴望改变命运的女知青占为己有。一个小小的许鹦鹉算得了什么?公社领导和宣传队的头目拨了一个小指头,许鹦鹉就扫出宣传队回生产队下田了,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姜榕树就从容在握。谁知姜榕树这个小女子,她像白毛女吴清华一样犟得像头牛,她离开宣传队,直接去了许鹦鹉家,上了许鹦鹉的床,接着就有关于怀孕打胎的消息传出。
我的确不是我母亲头胎怀下的,在我之前,据说她至少打过两次胎,这在当地未婚少女中是创下纪录的,因此名闻遐迩。
多亏当时我外公还在边远山区劳动改造,行动不自由;也多亏我外公早已脱了军装卸了手枪,否则许鹦鹉与姜榕树肯定一起没命了。当我外公“解放”回城,已经是“四人帮”倒台以后的事,我都已经来到人间。生米煮成熟饭,一切都无济于事,可是我外公还是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毛发刺拉、呼呼喘着粗气出现在娥眉。娥眉群情振奋,宛若过节。许鹦鹉家门外顿时出现经典盛况,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伸长脖子急于观看的人群。
“姜榕树!”我外公双手插腰,声色俱厉,气贯长虹,仿佛回到当年千军万马齐奔腾的战场。“姜榕树!”他又大吼一声。
我母亲姜榕树抱着我应声从屋里慢悠悠地出来,她好像很惊奇,笑眯眯地看着姜二。她说:“哎呀,您来了,您是老革命呀还亲自来。”我母亲那时性格还很健康,关键时候,她懂得及时弄出逗趣的话试图调剂气氛。
我父亲许鹦鹉迅速跑出来,拦在我母亲与我外公之间,用身子护着我母亲和我。他说:“有事进屋说,进屋,快进屋。”
我外公看都不看他。我外公姜二把头往旁伸过,两眼还是盯着我母亲,嘴张得极大,仿佛想一口把我母亲吞掉。“你!”他的手指向我母亲,“你是叛徒!他妈个B你是叛徒!”
我母亲说:“是吗,叛徒?我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了吗?我跟‘四人帮’穿一条裤子了吗?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我当过反革命吗?”
“你你你!”我外公手举起来了,往前猛扑。我母亲站着不动,一动都不动。是我父亲拼命地推开我外公。我外公与我父亲头顶头用着相反的力气,于是胶着在一起。此时我奶奶也突然从屋里冲出来,她英勇地撞到我外公身上,张大尖尖的十指又抓又揪,嘴里还发出母狼般凶狠的嚎叫。
人群中嗡嗡嗡响成一片,感觉得到那股炙人的热烈气氛。
我哭起来,哭声虽然弱小,却透着一股怒不可遏的恼火。
我母亲手在我后背上轻拍着安慰我,又扫了人群一眼,突然转身往屋里走去。
我外公喊道:“姜榕树,我跟你断绝一切关系!你不是我女儿,你听着,你一辈子也别想再跨进我家门一步。”
我母亲其实已经在屋里,听了这话,又走出来,倚在门旁,望着我外公姜二,慢吞吞地说:“好的,我记住了。”
我外公手枪状的指头气势汹汹地戳向我母亲。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如果我外公手里真有枪,怦,他一定就扣动扳机了。“有种你一辈子呆在这里!”
我母亲说:“行啊,我会呆一辈子,一辈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