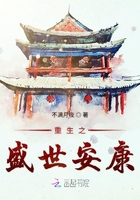大雪裹狭着整个延盛皇城 ,饰着风雪夜归人的戏码,打更人的更也只有自己听得见,指引着归去的路。
我强行走着,远处的皇宫现下在茫茫的雪中,再看不见任何的朱红,看不见半点灯,彻底的蛰伏了下去。
我松了手中的伞,倚在墙上,笑声夹杂着低低的抽泣与呼啸的风声,声音虚弱地显得如此荒凉,逐渐淹没在白白霭雪之中,意识渐渐模糊,身子渐渐的脱力滑落。
交了兵符,此事了却……了却后我又该如何?又能如何。
我不甘就此,苍白着脸重新拾起落在地上的油纸伞,将锦红大氅弃去,挺直了身子,撑着油纸伞,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盖着雪的延盛城的青石板路上。
我还要将这延盛城走完。
这儿,亲身相护过的地方。
护它不要颠世流离,护它如它的名字一般,延盛。
半吊着命的人,又何须如何,半吊着魂的人又会怕如何?
我依旧哼着曲,去到城墙,去到小巷,去到迁月湖的老柳下,将当年埋下的酒挖出,那封着陈年老酒的酒坛晃荡,两旁白雪皑皑。
我行走在这延盛城,只为看遍它的雪,我独自一人,不知归处。
没有什么遗憾了罢。
还有什么遗憾呢?
拍开酒坛的封盖,清冽的酒当头灌下。
我大笑:
岁月光阴熬酒,临前灌得酩酊。
当不惧瘦马独行,梅雨花落尽,归期寻不到径。
酒液携着微醺,淌过衣襟,催得青翠色深的苍然。
我咳着摔躺在了迁月湖畔,那颗熟悉的老柳下,伞倒在了一旁。
未束的及膝墨发与宽袖在雪上纠葛着铺开,没了伞,落雪很快将我的发缀上白。
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也不知是酒的缘故,还是其他。但我却依旧能够透过老柳枝叶间的缝隙,看到它盛在身上的雪。
我咳嗽,呼出来的雾气飘远,流出来的血将那些白色染红,沁透。
怎么……会没有遗憾呐……
终是瞌上眼,雪落在眼上,凉的透彻。
…………
翠色的宫装散了一地,远看着像是凭得生出的藤蔓铺在雪中,却在他的心上点上一颗朱砂痣。
发间眉间落了霜雪,白了他的眉目,灰袍将军走上前,停下一直跟着的步子。
他一路跟着她,自从她出了皇宫。
她想走遍延盛城,他便陪着她,她想让这风雪延盛送她最后一遭,他便也陪着
——就像许多年前,他们一同打马对饮,看遍延盛繁华那般。
他走进,将她捞起在怀,她的半白发丝从他的臂上流下,他的发也半白。
宸天将她抱紧,眉间白了的颜色,被氤氲的热气化去。
那么久了,久到他几乎都觉得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他终究是见着了。
冷了那么久了,总算是觉到了那么些暖意。
他未去将伞捡起,就这么像她来时那样,一步一步的走回,抱着她,顶着风雪。
“回家罢。”他也不知道是在跟谁说。
她青翠的裙摆乘风而起,与白雪一同纷飞。
风雪夜归人,回首再难问。
————
他走了许久,才回到了府上。
下人将漆门打开见到他时,几乎是觉得自己出现了癔症,是否是看见了民间传说的雪妖,相携而来。
他将她安置好,再未踏出过房门。
屋子里头很暖和,这是他早给她在自己府上留下的屋子。
云纱帷帐,千工拔步,琉璃珠帘,亲笔墨屏,无一不上等,无一不亲手。
他以前总信誓旦旦,这里他终究会交给她,她也终有一天会走进。
这还是她第一次进来。
她昏的早没有意识了,但还在不住的咳血。
被上的绣纹几乎都要被那嫣红染得再看不见。
他抚了抚她的脸,将她唇边的血拭去,从柜中取了香点上。
一时间,烟雾缭绕,她的脸都迷蒙了起来。
这是世间最后一柱华佗香,若是再挽不回她的命,那这世间这就再无其他法子能够留住她了。
宸天垂下眼,看着她仿佛是睡沉的模样。
若是留住了,这屋子今后就有主人了,若是留不住……又何妨。
能再见到她已经是天赐的惊喜。
他靠着床柱坐了下来,挨在她的身边,让她枕着他的腿。
烟透过了窗细缝,又留下一卷绕着他,绕着他的眉眼。
低低的哼着无词的曲,仿佛塞外黄沙般粗犷的曲,在低哑间藏着难懂的深情。
窗边的小几上摆着酒坛,那是他与她一同酿的酒,一人一坛,自个藏好,等着时候到了便取出来对酌。
她的那坛,以被她喝尽,与延盛作了别。
而他的那一坛,他想,待她醒来,他们一同分饮。
但他终是没能等到。
或是她……不想留。
宸天眼睁睁的看着,她呼出最后一口气,了无生息。
他坐了许久,在她的身旁。
他站起来,用着麻掉的身子将窗打开。
烟飘了出去,风雪吹了进来,吹得他身后案几上的一叠纸满室纷飞,吹得他的衣袖鼓风而起。
雪吹到他的面上,化了去,成了水顺着颊滑落,落在了他的衣襟上,浸出些许微深湿色,又凉透了。
他身后的纸,全数歇了下来,都是大片大片的空白。
他转身将酒坛拎起,放好,等着下次什么时候将它拿出。
她是不归人,那他等着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