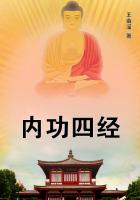“我不懂白人的风俗习惯。拉合尔妙屋里那位管理佛像的僧人要比这瘦子和气得多,他们将当我面把孩子带走。他们会把我的弟子变成洋大人吗?哭,伤心啊!这一来我怎么去找我那条河?难道他们没有弟子吗?问他们。”
“他说他很难过,不能再去找那条河了。他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弟子,别再麻烦他?他要洗清他的罪孽。”
班奈特和维克托神父一时都回答不出。
基姆见到喇嘛心里难过,便用英语说:“我想要是你们现在放我走,我们会悄悄地走掉,并不抢东西。我们将像我被你们捉到以前那样继续去找那条河,我但愿自己不是来找什么红公牛等那一套东西的、我可以不要它。”
“孩子你从来没替你自己干过这么一件好事。”班奈特说。
“我的天,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维克托神父两眼紧望着喇嘛说,“他不能把孩子带走,然而他是个好人-我敢说他是个好人,班奈特,要是你把那枚卢比给他,他会对你诅咒,把你咒个臭死!”
他们大家不言语,只听彼此的呼吸声,长达三分钟到五分钟,喇嘛后来抬起头,两眼掠过他们凝望空际。
“我是学佛修道的,”他痛心地说,“这是我的罪孽,我须受的惩罚,我使自己的假想-我现在看来只是假想-你是奉派来帮助我找那条河的,于是你的好心肠,你那彬彬有礼的态度和你年纪虽小却通达事理的智慧,博得了我的喜欢,可是修道的人不能有任何欲爱,因为那些都是空幻,然后……”他引述了一段中国经文,接着又引述了两段。“我偏离了道,徒弟,这不是我的错,我看到众生,路上那些新的人,和你看到这些东西那种喜欢的样子,心里都高兴。我对你也暗自得意,一心一意以为你只是为我的搜寻而来的,现在我伤心了,因为有人要把你带走,我的河离我好远,这是我犯了戒律的缘故。”
“撒旦真厉害!”维克托神父说,他听人告解经验丰富,听出喇嘛的每一句话都全带痛苦。
“我现在看出那红公牛的征兆不但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一切欲念都是红色,而且是邪恶的,我将忏悔赎罪,独自去找那条河。”
“至少要回到库鲁女人那里去。”基姆说,“不过你在路上会走失,她会奉养你,直到我回来。”
喇嘛扬起手,表示这件事在他心里已经解决。
“现在,”他转对基姆说,声调改变,“他们预备把你怎样?我至少可以说,多积功德,消灭过去的罪过。”
“要把我变成一个洋大人-他们这样想,后天我就回来,别难过。”
“哪一种的?像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他指着维克托神父,“还是像我今晚所看见的那种佩剑脚步沉重的?”
“也许是。”
“那可不好,那些人完全受欲念驱使,将来一切都是空的,你可不能成为他们那种人。”
“乌姆巴拉的僧人说我的星象是战争。”基姆插嘴说,“我会问这些傻瓜-可是真的没有必要。我今天夜间就会逃回来,因为我所要的只是看看新奇事物。”
基姆用英语向维克托神父提出两三个问题,然后把答复翻译给喇嘛听。
然后讲:“他说,‘你们把他从我身边带走而不能说你们要把他琢磨成怎样的人。’他说,‘在我走以前要告诉我,因为把孩子教养到大可不是小事。’”
“会把你送到学校去,然后,我们再看情形,基姆波尔,我猜想你愿意当兵?”
“白人,我不要!不要!”他拼命摇头,他秉性不喜欢操练和刻板行动,“我可不要当兵。”
“叫你做什么,你就得乖乖地做什么。”班奈特说,“我们帮助你,你应该感激我们。”
基姆做出体恤的微笑。要是这些人以为他什么都肯做,连不喜欢的都做,那就更好。
又是长长一阵缄默。班奈特躁急得不耐烦,提议叫哨兵来把喇嘛赶走。
“洋人之间是否买卖学问?问他们。”喇嘛说。基姆便翻译了。
“他们说钱是付给教师,可是那笔钱将由团队付……那又何必?只是住一个晚上。”
“是不是-钱付得越多,传授的学问越好?”喇嘛不理基姆的早日脱逃计划,“付钱求学不是坏事,帮助无知的人得到智慧永远是一桩功德。”念珠像打算盘那样掐得飞快,喇嘛然后面对他的压迫者。
“问他们明智的、适当的教学要付多少钱?而且在哪个城市有?”
“嗯,”基姆译过之后维克托神父用英语说,“那要看情形,你在军人孤儿院里,一切费用由团队付;你也许会在旁遮布共济会孤儿院的名单上(他和你都不会懂是什么意思);可是一个男孩子在印度所能受的最好教育,当然是勒克瑙市的圣查威尔学校。”翻译这一段话很花一些时间,因为班奈特要插嘴。
“他要知道多少钱?”基姆淡然问。
“每年两三百卢比。”维克托神父早已不感觉惊奇。躁急的班奈特却不明白。
“他说把那学校的名字和钱的数额写在一张纸上给他。他还说你一定要在底下写上你的名字,因为过些时候他会写信给你,他说你是个好人。他说另一个人是傻瓜。他现在要走了。”
喇嘛蓦地站起来。“我将追循我的寻求,”他大声说,随即走掉。
“他会撞上哨兵。”维克托神父喊道,跟着一跃而起,“可是我不能离开这孩子。”基姆想拔脚跟出去,可是强自忍住。外面没有喝止声,喇嘛已经隐去。
基姆镇静地坐在行军床上,喇嘛至少已经答应会和库鲁来的那位妇人在一起,其余的完全无关紧要,他暗自得意的是那两个军中神职人员显然十分激动。他俩低声谈论了好久,维克托神父有所劝说,班奈特看来不觉相信,这一切都新鲜有趣?只不过基姆觉得困了,他们把人叫进来-其中之一肯定是上校,就像他父亲所预言的,那些人问他无数问题,主要是关于抚养他的那个女人,基姆统统照实答复,那些人认为那个女人不是良好的监护人。
说来这是他最新的经历,只要他高兴,迟早都可以脱逃,混入广大、灰暗、无形的印度,远离营帐、随军种职人员和上校,要是这些洋大人希望得到深刻印象,他就竭力命他们满足,他自己也是白人。
那些人讲了半天他听不懂的话之后,把他交给军士,并且严令军士不得让他脱逃。全团人马将开往乌姆巴拉,基姆运往桑纳瓦去,费用大部分由共济会分会担负,一部分由大家认捐。
“这真是连欢呼也不足表达庆喜的奇迹,上校。”维克托神父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十分钟的话,“他的佛教忘年交得到我的名字和地址之后便溜掉,我搞不清楚他究竟是要替这孩子付教育费还是准备用巫术作法。”他转对基姆说:“你要感榭你那朋友红公牛才对,我们将在桑纳瓦把你琢磨成铁铮铮的好汉-哪怕牺牲掉使你成为基督徒的机会,也在所不惜。”
“一定会-绝对会,”班奈特说。
“可是你们不到桑纳瓦去。”基姆说。
“可是我们一定会去桑纳瓦,小家伙,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他比欧哈拉的儿子稍微重要些。”
“你们不会去桑纳瓦,你们会去打仗。”
整个帐篷里的人都哈哈大笑。
“将来你对你自己的团队认识稍微清楚一点,你就不会把行军路线和战线混为一谈了。基姆,我们倒希望能有关于打仗的一天。”
“哦,这我都知道。”基姆又大胆放肆起来,要是他们不去打仗,那他们至少还不知道他所听到的乌姆巴拉某幢房子走廊上所讲的话。
“我知道你们现在不去打仗,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开到乌姆巴拉,就会调派去打仗,有八千人将参加那场战争,炮不在内。”
“你说得够清楚的,你的本事可别添加预言这一项。军士,把他带走,从鼓手那里弄套衣服给他穿,小心别让他溜掉,谁说奇迹时代过去了?我想我要去睡了,我那可怜的脑子已经不行了。”
一小时后,基姆坐在营地另一端,像头野兽似的默不吭声,浑身刚洗干净,穿着一套扎手扎脚,好难受的军服。
“一个真了不起的小子,”军士说,“他率领了一位黑头婆罗门野僧人来,脖子上挂着他父亲的共济会会员证,满口天晓得的什么红公牛。那婆罗门野僧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这小子盘腿坐在军中牧师的床上,对众人预言将有激战。印度对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来说,实在是个野地方,我把他的一只腿绑在帐篷柱上,要是他想穿出篷顶逃走的话。你那关于打仗的话是怎么说的?”
“八千人,炮在外。”基姆说,“就快发生了,你等着瞧吧。”“你这搅扰人心的小鬼,躺在两名炮手当中,睡觉吧,那两个孩子会看着你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