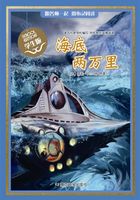我又回自己家来。
吃饱喝足得到宽恕。
这些人是我的父母,
和同胞兄弟姊妹!
肥牛为我而宰,
可是没价值的东西对我更有刺激……
我想我的猪对我最好,
所以拔脚朝猪圈走去。
The Prdigal Son。
用绳来相连的行列又懒洋洋地拖着脚步向前进发,老夫人睡到下一个歇脚处才醒,这段行程很短,离太阳下山还有一小时,基姆便走来走去找乐子。
“为什么不坐下休息?”一个侍从说,“只有魔鬼和英国人无缘无故地走来走去。”
“永远别跟魔鬼或是驴子和小男孩交朋友,没人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另一侍从说。
基姆回头给他们一个白眼-他不要诌魔鬼怎样玩弄小男孩后来悔之莫及的老故事,然后懒散地穿过乡野。
喇嘛大踏步跟在他后面,那天他们每次经过一条小河,喇嘛便跑过去看看,可是始终没有他要找到他那条河的启示,如今他可以用相当有修养的口吻和人相谈。又有一位贵妇适当地尊敬他,奉他为宗教顾问,便不再一时急于要找那条河了。而且他准备花上很多岁月安安静静地去找;他没有白人那种急性子,却极有信心。
“你哪里去?”他向基姆遥呼。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去-那段行程很短,而这一切,”基姆对西周围挥手说,“对我都是新奇的。”
“她毫无疑问是个明智、有眼光的女人。可是有时候很难沉思默想,当你-”
“女人统统都如此。”基姆的这句话简直像所罗门王说的。
“喇嘛寺前有一个宽敞平坛,”喇嘛喃喃说,一面拈起每一颗都掐得非常光滑的念珠,“是石头的,我在坛上留下摇着这个走来走去的足迹。”
他掐念珠,开始低诵“唵嚤呢叭嘀畔”;很高兴那地方阴凉、安静、没有灰尘。
基姆的眼睛在平原上望来望去,他只是漫步,毫无目标,不过附近有些农舍似乎是新筑的,他想过去看看。
他们来到一片放牧地,在下午的光线中呈现棕色和紫色,中间有丛密的芒果树。基姆暗自奇怪这个地方这么适当,怎么没有个神龛。这孩子是用僧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远处有四个人并排走来,人显得非常小,基姆掌心弯回罩着两眼聚精会神地看,瞥到他们身上的金光。
“是兵,白种兵!”他说,“我们看看。”
“你我两人单独走出去的时候总是碰见兵,我可从没见过白种兵。”
“他们只有喝醉酒了才伤人。好好躲在这棵树后。”
他们走到阴凉芒果林口的大树后。两个小小的身影停住;另外两位踟蹰地走向前来,他们是在行军的一个团的探子,前来勘察扎营地点的,他们向两旁散开,手持五尺长的杆子互相呼应,杆子上旗帜飞扬。
他们终于步步为营地走入芒果林。
“我想官长们的营帐就在这里或这里一带的树下,我们其余的,可以在林外扎营,他们定好后面辎重车的停车地点没有?”
他们再向远处弟兄遥呼,应声隐约圆润。
“那么就把旗插在这里。”其中一个说。
“他们在部署什么?”喇嘛非常好奇,“这是个既大又了不起的世界。旗上那个东西是什么?”
一个兵在离他们仅数尺处插下旗杆,可是嘴里咕哝表示不满,把它拔起和他的伙伴商量,那个伙伴朝林阴深处上下打量,把它插回原处。
基姆两眼睁得大大的看傻了,呼吸变得急促,那两个兵朝阳光处走去。
“我的天!”他气喘吁吁地说,“这我要交运了!这正如是乌姆巴拉地方那僧人在地上所画的!你记得他所说的话?先来两个仆人来准备一切,在一个阴暗地方-幻象总是这样开始的。”
“这不是幻象,”喇嘛说,“这只是尘世间的虚惑而已。”
“在他们之后来一只公牛-绿地上的一只红公牛,你瞧!就是它!”
他指着不到十尺外,被晚风吹得拍拍有声的那面旗帜。它只不过是一面普通的扎营标志旗;可是那个团对于徽饰之类的事一向极为认真,把团徽也绣了上去-这就是爱尔兰绿底上一只大金色公牛的小牛队团徽。
“我看到了,现在也记得了,”喇嘛说,“那绝对就是你那只牛。两个人前来部署准备的话也应验了。”
“他们是兵-白种兵,那僧人是怎么说的?公牛象征战争和武装人员。啊,圣者,当前的情况和我所寻求的相符合。”
“真的,确是真的,”喇嘛凝视着那面在暮色中像红宝石一样泛红的旗帜,“乌姆巴拉村僧说这是战争之象。”
“现在怎么办?”
“等着看,我们等着看。”
“现在黑暗就明朗起来。”基姆说。日落以前,斜阳残照,使树林在几分钟内呈现为一片金光本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不过基姆认为这是乌姆巴拉僧人的预言完全应验的迹象。
“你听!”喇嘛说,“有击鼓声,很远!”
那鼓声在寂静中从远处传来,起初像头里血管的噗托声,不久又听出还有尖锐的声音。
“啊!军乐。”基姆解释。他知道那是团乐队的声音,可是喇嘛觉得听得惊奇。
平原远处,尘土滚滚中出现一队人马,管乐器奏出乐曲:
我们请你倾听。
莫里根禁军。
向斯立哥港行进!
跟着是清脆的横笛声:
我们扛枪。
我们行军,我们开拔。
从凤凰园。
直到都伯林湾,
鼓与横笛。
铿锵可闻,
我们前进-前进,英里根禁军前进!
这是小牛团队的乐队在鸣金扎营:因为这些健儿是携带辎重行军的!队伍随着地形起伏的人马来到了平地,左右两行后面是缓缓而行的辎重车,还有……
“这简直是妖术!”喇嘛说。
平原上突然营帐星罗棋布,它们仿佛是从辎重车上伸展开的。另有一批人拥入林中,默然搭起一座大营帐,取出锅釜和一捆捆的东西,这些都由一群随军士仆拿下,整个芒果林在基姆和喇嘛注视之下变成了一座井然有序的城。
“我们走吧。”喇嘛说。他害怕地向后退缩,因为这时火光渐渐明亮,身上所佩军刀叮当响的白人军官昂然步入权充膳堂的大帐篷。
“向后站在阴影里。”基姆说,两眼仍盯在旗上。他从没见过训练有素的一团人在三十分钟内扎营的情形。“瞧!瞧!瞧!”喇嘛急促地喊道:“那边来了一个僧人。”
来者是美国国教的随军牧师班奈特,腿一瘸一瘸地走着,一身黑衣上尽是土。一个弟兄曾讲起牧师是否吃得消的问题:为了给那人点颜色看看,他那天和弟兄并肩行军。凭他身上那件黑服,表链上的金十字架,没有须毛的脸和那顶宽边软黑帽,在印度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出他是僧人。他在帐门口旁边一张帆布新椅上坐下,脱掉靴子,三四个军官围上来对他这番行军壮迹哈哈大笑并且开玩笑。
“那些白人说话完全欠缺庄重,”喇嘛凭声音判断,“我已经端详过那僧人的脸,我想他有学问,他会不会听得懂我们的话?我要跟他讲我的寻求。”
“在白人塞饱肚子以前,千万别跟他讲话。”基姆引证一句有名的谚语说。“他们现在要吃饭了-我想他们不是好相与的,不便跟他乞讨,我们还是回到歇脚处去,吃过了再来。那一定是一个红雄牛-我的红雄牛。”
老夫人的随从替他们开饭时,他们都很明显地心不在焉,大家都没跟他们说话,因为得罪客人是不吉利的。
“现在,”基姆一面刷牙一面说,“我们回到那地方去,不过圣者,你一定要在稍微离开那里一点的地方等着,因为你的脚步比我的沉重,而我急欲多看看那红公牛。”
“可是你怎么听得懂他们讲的话?慢慢地走,这段路很黑。”喇嘛不放心地说。
基姆不撇开那个问题,只说:“我已在一处相近的地方做了记号。你可以坐在那里,等我叫你。”“不!”喇嘛表示反对-“要记得这是我的寻求,是寻求那红公牛的行动。天上的星象现在不是对你有作用。我懂一点白种兵的风俗习惯,而且我一直想看些新奇事物。”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你不知道的?”喇嘛很听话,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坐在离黑漆漆的芒果树丛不到百码的一片小洼地里。
“我不叫你你就别动。”基姆迅速没入暮色中。他深知营地四周有哨兵,听到一名哨兵的厚军靴声不禁窃笑。月明之夜能在拉合尔屋顶上利用每片黑暗和角落躲进追逐者的一个孩子,是不大可能被一排训练有素的兵截住的。他大胆地在两个哨兵之间匍匐而过,然后跑跑停停,有时蹲伏,有时卧倒,逼近灯火明亮的膳堂帐篷,身子紧蜷在一棵芒果树后,等待听到可够应声的只字片语,借机会混进去。
基姆心里只想对那红公牛知道得更多些。据他所知道,而他虽然知道的有限却会很奇怪地忽然增加,那些人,他父亲所预言的那九百名什么都做得出的健儿在天黑后很可能向那红公牛祈祷,就像印度人对圣牛祈祷一样。这至少是完全对的,合理的。因此在这里可以请教的是那身悬金十字架的随军牧师。可是基姆又想起他在拉合尔所规避的那位面色凛漠寒霜的牧师,因为那牧师可能很讨厌地要他读书,然而不是正在乌姆巴拉证明了他的星象预示战争和武装的人吗?他不是星辰和世界之友,有一肚子可怕的秘密吗?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支配他所有快速思潮的一个基本念头-这次历险,虽然他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不但能使他翻墙头爬屋顶那套老把戏很有意思地继续下去,而且还使伟大的预言趋干实现。他腹部贴地,朝膳堂帐篷口匍匐蠕动过去,一只手按住他脖子上挂的护身符。
一切悉如他所料,那些洋大人在向他们的神祈祷,因为餐台当中-行军时惟一的摆设-放着一只金牛,是仿照从圆明园掠劫来的原件仿制的,一只金红色公牛低着头在一片爱尔兰绿野上乱撞,那些洋大人都举杯向它乱喊。
班奈特牧师总是在举杯祝酒之后,离开膳堂,今晚因为白天行军疲乏,离去的动作比平时来得突兀。基姆正在抬头瞪望台上的金牛,牧师的脚忽然踹在他的右肩胛上。基姆在那厚皮靴下疼得身子猛缩,朝旁边翻滚,牧师重心一失,身子倒下,不过那牧师动作敏捷,一把捏住基姆的脖子,几乎把这孩子扼死。基姆拼命踢牧师的肚子,牧师疼得直喘气,身子弯下去,可是始终不松手。他后来身子翻上去,不声不响地把基姆拖回他自己的帐篷去,小牛团队的官兵却是非常喜欢恶作剧的,牧师心想把事情问清楚以前最好不做声。
“哈,原来是个孩子!”他把他的俘虏拉到灯光下一看,然后使劲摇晃那小身子,一面吼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个小偷、小贼,你懂我的话吗?”他只会说一点点印度话,基姆恼了,就装作是个小贼。他喘过气之后便编出一番听来像真的假话,一面说他是一个火头军的亲戚,一面注意牧师的肋下。机会来了,他猛朝帐篷口蹿去,可是一只长臂迅即伸出揪住他的脖子,弄断脖子上的系绳,手抓到那护身符囊。
“还给我,哟,还给我,丢了吗?把那些纸还给我。”
他说的是英语-在印度出生的人讲的那种声音细弱无力,像锯断的那种英语。牧师惊得跳起来。
“一块肩胛骨,”他一面说一面把手伸开,“不,是一种异教徒的护身符,怎么-怎么你讲英语?小孩子偷东西是要挨揍的,你知道吗?”
“我不偷-我没偷东西。”基姆像个小狗见到举起的棍子那样,难受得乱跳。“哟,还给我,是我的护身符,别把我的偷走。”
牧师毫不理会,迳自走到帐篷口大声喊,一个脸修得很干净、胖墩墩的人出现了。
“维克托神父,我有事向你请教。”班奈特牧师说,“我在膳堂帐篷门口黑暗里撞到这孩子,按照常情我本会训他一顿,放掉他,因为我相信他是小偷,可是他似乎讲英语,而且十分珍视他脖子上挂的一个护身符,我想你也许能帮助我。”
班奈特认为他和爱尔兰团队的天主教随军神父之间有无从跨越的鸿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教一旦有了关于人的问题,总是要找天主教咨商,班奈特在教会主张上十分僧恶天主教和天主教的一套,然而同时却十分尊重维克托神父。
“一个说英语的小贼,是吗?我们先看看他的护身符。不,这不是一块肩胛骨,班奈特。”他伸出手。
“不过你我有权把它弄开吗?好好地鞭挞他一顿-”
“我没偷东西,”基姆抗议,“你把我全身都踢疼了,把护身符还我,我就走。”
“别那么急,我们先看一看。”维克托神父不慌不忙地把可怜的基姆波尔·欧哈拉那张“不得转让”的羊皮纸、他的退伍证件和基姆领洗的证件一摊开。基姆波尔对那张领洗证件只模糊地觉得会对他儿子有妙用-在纸上写了几遍:“照顾这孩子。请照顾这孩子,”还签了他的全名和他在团里的号码。
“地下的撤旦真厉害!”维克托神父说,一面把那几份证件递给班奈特牧师,“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知道,”基姆说,“都是我的,我想走。”
“我不大明白,”班奈特说,“他也许是故意带来的。可能是一种行乞的骗人伎俩。”
“我还没见过这样不愿意缠人的乞丐。这件事有点不可思议的奥秘,你相信天意吗,班奈特?”
“希望如此。”
“我是相信奇迹的,说来都是一回事,撒旦真厉害!基姆波尔·欧哈拉!他的儿子!可是这孩子是土著,而我是亲手替基姆波尔和安妮·萧特主持婚礼的。孩子,你有这些东西多久了?”
“我从小就有。”
维克托神父迅速走上前去,解开基姆的上衣。“你瞧,班奈特,他不是很黑,你名叫什么?”
“基姆。”
“或者是基姆波尔?”
“也许是,你们让我走,行吗?”
“还叫什么?”
“他们叫我基姆·爱尔希提·克,就是爱尔希提的基姆的意思。”
“爱尔希提-那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爱尔-兰-我父亲的那个团。”
“-哦,原来如此。”
“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住过了。”
“住过什么地方?”
“他住过了,他当然已经死了-走掉了。”
“哦!这是你的莽撞说话,是吗?”
班奈特插嘴了:“我可能冤枉了这孩子,他绝对是白人,不过显然没有人抚养他,我一定把他弄伤了,我想烈酒不-”
“那么给他一杯雪利酒,让他蹲在行军床上。基姆,没人会伤害你,把那喝下去,把你自己的一切讲给我们听。说实话,如果你不反对。”
基姆把空酒杯放下之后,咳了一两声,心里在思量,这似乎是既需要谨慎又需要有想像力。在营地一带徘徊的孩子通常是挨一顿鞭挞之后被撵走,可是他没有挨揍;那护身符显然对他发生作用,看来,那乌姆巴拉僧人所说的和他所记得的那一点子父亲所说的话极为灵验,不然那胖随军神父何以有凛然起敬的神情,那瘦的又为何给他一杯有点辣嗓子的黄水喝?
“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在拉合尔死了,那女人在出租马车的地方附近开了一爿旧货店。”基姆开始鼓起勇气讲,没有把握说实话对他究竟有多大的好处。
“你母亲呢?”
“不知道!”-他用个表示讨厌的姿态说,“我一出生她就走掉了。我父亲,他从贾都-佳(共济食堂)-你们叫什么?(班奈特点头)要了这些纸来,因为他声名很好,你们叫那什么?(班奈特又点点头)。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他还说,雨天前在乌姆巴拉地上画命宫图的婆罗门僧人也说,我将找到绦地上的一只红公牛,那只牛将帮助我。”
“好了得的一个小撒谎精。”班奈特喃喃说。
“撒旦真厉害,这是多么妙的一个地方!”维克托神父喃喃说,“讲下去,基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