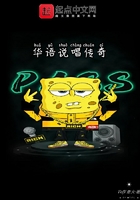钟鱼丢了工作,落下一个“强奸犯”的罪名,尽管是无罪释放,可居民们并不认同;无风不起浪,公安都来抄家了,大牢里蹲了七天,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人。最初钟鱼还能鼓起勇气走出家门,以直面的坦然证明自己的无辜,然而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妇女们一见他走来,就像见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个个慌忙地躲进门里去,甚至于将近六十岁的尤寡妇,也跟着别人乱钻,而且将十岁的孙女都叫进去了。钟鱼享受的是当年阿Q的待遇。男群众也不见有丝毫的宽容,虽然对钟鱼敢想敢干心动立即行动的果敢私下有钦佩和暗羡之意,但绝不能纵容他放肆无忌惮地招摇过市,以“性侵”为“性福”。所以他们握紧铁拳,怒目而视,逼仄得钟鱼低下忏悔的头颅。钟鱼的希望之旅半途而废,他想表明自己的清白,反而确凿了他的龌龊。他带来的恶劣影响还不止这些,因为他这个隐患的存在,致使棬子树街的夜晚笼罩上一层惶恐不安的气氛,清冷萧条。晚饭后走动串门扯闲拉呱的妇女匿迹了,即便出门,也须二人以上同行,上下夜班的妇女再不敢独自往来,一定要丈夫接送至巷口,一个人在家的妇女必定关门闭户,门窗锁死,枕头下藏一把剪刀,随时准备戳死钟鱼。
声名狼藉的日子里,钟鱼只能蛰居在家,潦倒度日;蒙头大睡、目光空洞、一地烟蒂或是辗转叹息……他的沉默逃避并未平息余波。这一天,有人在院墙外高声叫喊钟鱼的名字。钟鱼趿拉着鞋下地出去打开院门,门口站着两个穿海魂衫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后面架着几辆自行车,或倚或坐四五个穿海魂衫少年,脖上吊着书包,大约是一个帮派,少年们嘴上都叼着烟,斜睨着钟鱼。
“强哥,就是这小子。”一个少年向首领报告。
这群少年钟鱼不陌生,有尤寡妇的小儿子,老蒋的二儿子,刘小脚的孙子,马小辫的外甥。只那个年纪稍长的“强哥”不是棬子树街的人。“强哥”穿的是白色套头衫,外面披一件黑色风衣,搭一条长围脖,墨镜,打了发蜡的背头油光可鉴。这是《上海滩》里许文强的造型,钟鱼很眼熟。
强哥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倜傥地嘘出一口烟才缓缓地问:“你就是钟鱼?”
“我就是,有什么事?”
“什么事?”强哥像睡落枕一样来回转动脖子,微笑道,“我听说你挺冲啊。”强哥挥挥手,“带走!”
钟鱼的胳膊立刻被左右钳制,挟持着上路,来到了李疯子曾经栖身的破园子。如今这里已是墙倒屋塌,荒草丛生。一群少年将钟鱼围在中间,强哥潇洒地抖落风衣,取下围脖,摘掉墨镜,一个少年恭敬地替老大收好。
“好好的棬子树街怎能容你一个强奸犯称王称霸?”强哥发话了。
“你们知道什么?一帮毛孩子不好好读书,跟着瞎起哄。”钟鱼痛心道,“我也是你们这么大过来的,打打杀杀的有什么用?到时后悔的是自……”
话音未落,一记“凌空飞脚”踹在钟鱼的面门上,钟鱼一个趔趄几乎仰倒。众手下见老大出手,蜂拥而上,拳脚相加,一时间草偃风从,乱絮飞扬,夕阳的血红渲染下甚是悲壮。钟鱼在雨点般的群殴下毫无还手之力,或是他根本没打算还手,仿佛一个人肉沙包供练家子尽情施展拳脚。少年们只劈头盖脸地一通乱打,唯独强哥是按着功夫套路打,一招一式演绎得淋漓尽致。最后气喘吁吁才罢手,原本以为这是场恶战,都揣了家伙,没想到钟鱼如此不堪一击,但一仗下来仍可功成名就;钟鱼是“进去过的人”,打一个“进去过的人”在道上便是扬名立万的资本,并且还是为民除害,惩恶扬善之义举。
强哥披上风衣,戴上围脖墨镜,向后抹了抹弄乱的头发,整装完毕后蹲下身来,拍着钟鱼贴在泥土上的脸说:
“今后不可嚣张,否则见一回灭你一回。”
少年们呼啸着走远了。钟鱼找到自己的鞋,挣扎这从地上爬起来,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少年们出手很重,钟鱼的腰背疼痛难忍,他撑着腰喘息着。面前的一片瓦砾曾经是一幢破旧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个老怪物李疯子,钟鱼仿佛看到童年是自己,坐在那道门槛上,旁边一个煤球炉青烟缭绕,李疯子抖抖袍袖,伸出枯手,在他身体上下游走,摸骨测命,钟鱼还能回忆起他指缝间那股萝卜咸菜味儿,李疯子说了一大堆话,可他绝算不出此地此景,几十年后钟鱼还有这样的命运。
钟鱼肆然长笑,艰难走出园子,园子外已聚集起一帮闲杂人等,他们见证了热血少年痛殴流氓的全过程,此时隔阂冷漠又颇感困惑地看着钟鱼,不明白他笑从何来?他们困惑地目送面带微笑的钟鱼,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回家……
钟鱼夜不成寐,痛定思痛,这个城市已经不再属于他,烟雾缭绕中,一个遥远的地方在他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那里年轻而富有激情,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遍地是梦想,用报纸上的话说那是一片“热土”。她的名字是:深圳。
钟鱼翻开地图,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找到了这片“热土”,他用铅笔沿着铁路线一直连接到自己身处的“冷漠的土地”,弯弯曲曲的铅笔线东西横跨五省,漫长的路程。漫长到足以扯断与故乡有关的所有联系,那里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没人知道他的过去,没人知道他是谁。
钟鱼似乎拿定主意,要背上行囊,开始人生第二次的远行,不同的是,这次是他独自上路,去向一个未知的地方,他怀揣的不是淘金梦,而是浪迹天涯的自由。钟鱼站在窗前,夜空里一颗启明星熠熠生辉,映照得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然而这亮光须臾黯淡下去。心底有一份责任和牵挂是他不能割舍的。
钟鱼轻轻拉开房门,堂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电视屏幕闪着雪花,母亲似乎睡着了。钟鱼轻手轻脚走过去,看见母亲靠在躺椅上,腿上搭着的毛毯已经滑落下来,她脑袋耷拉着,嘴角一线口涎,喉咙里发出滞重的呼吸声。
钟鱼蹲下来将小心地将毛毯拉上盖好,然后充满内疚地端详着母亲,一闪一闪的亮光里,母亲的面容那样的疲惫衰老,干瘪的嘴唇,深深的皱纹,枯涩的白发,就像一盏熬干灯油的灯,再不能跳跃欢快的火苗,而在钟鱼的记忆中,母亲曾经是一个多么好强干练的人。钟鱼明白,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是他把母亲变成这样的,十年的漫长等待,等来的却是今天的结果。钟鱼忍不住潸然落泪,他亏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钟鱼的啜泣声惊醒了母亲。她揉揉眼睛,“哟,啥时候了?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妈,你太累了。”钟鱼赶紧擦干眼泪。
“我呀,才刚做了一个好梦。”
“梦见什么了?”钟鱼笑问。
“梦见你爸了,说是咱们一家三口在天井里吃晚饭”母亲幸福地回忆道,“……应该是夏天,你爸摇着蒲扇,还穿着那件漏洞的背心,你小时候他常穿的那件,你还记得不?”
“记得。”钟鱼笑道,“……前面印着‘生产大会战纪念’的红字。”
“你爸喝了酒话多,给咱们讲了一个笑话,哎呦,可招笑了,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你那时还小,正换牙呢,也吃吃笑个没够,喷了满桌子饭粒。”母亲露出开心的笑容。
“是吗?”钟鱼也呵呵地笑起来。
“唉……可惜,讲的什么一睁眼全忘了。”母亲黯然道,“……你爸是看咱娘俩过得太憋屈了,所以托梦逗咱们乐呢。”
钟鱼看一眼墙上的父亲,怅然叹气:“妈,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才会想到父亲。”
“不孤单,妈有你陪着呢。”
钟鱼心里有很多话,却不知从何讲起。他握着母亲的手笑道:“妈,您守寡这么多年了,没想过再找个伴儿?我支持您。”
“傻孩子,说什么傻话呢,妈都半截入土的人了,哪有那心思。”母亲翕然笑道,“我们老辈的人呐,认死理,一辈子只在乎一个人,活着想着他,死了还念着他,心里再容不下旁人。”
“这就是情有独钟……”钟鱼叹一声气,“妈,您说当年还没有计划生育,您干嘛不多生几个孩子呢?像别人家一样?”
“怎么忽然琢磨这事了呢,孩子?”母亲笑道。“妈生你的时候难产,伤了元气,以后就不行了……再说,日子艰难,养活一帮孩子不易,饥一顿饱一顿的,遭罪,不如只一个,不愁吃穿,好生带大。”
“小时候我是没吃过苦。”钟鱼点头,“……可是,假如多几个孩子的话,我不在身边,也有他们陪你,照顾你,或者像我一个不争气的,还有其他出人头地的,您老也能宽心。”
“唉,妈有你就知足了……”母亲摩挲着钟鱼的手背,“妈觉得你最好,谁都比不上。”
“妈,您让我无地自容了。”钟鱼惭愧地低下头。
“要说呢,多几个兄弟姐妹也是好的……”母亲若有所思道,“有个一般岁数的人和你说说心里话,开导开导,也许你的心就敞亮了。妈毕竟是老了,思想跟不上。”
“妈……”钟鱼将头伏在母亲腿上,“我无所谓了,只怕你操心受累。”
“妈没事儿,好着呢,别担心,啊。”母亲抚摩着他的头发,“别想那么多了,时候不早了,休息吧,孩子。”
“诶。”钟鱼起身拿过拐棍。母亲颤巍巍地站起来,忽然蹙眉捂住胸口,站立不稳。
“妈,您怎么了?”钟鱼赶紧扶住她。
“没事儿,没事儿。”母亲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坐久了胸口有点痛。”
钟鱼一直将母亲搀扶进卧室,服侍她躺下,盖好被子,才关门离开。回到自己的屋子,钟鱼拿起桌上的地图看了看,长舒一口气,然后放下来,拿起铅笔,在那道蜿蜒的铁路线钟鱼画一道大“X”,中止了异乡的梦想。
夜深人静,钟鱼走出家门,一个人走在阒寂的街道上,头顶星光璀璨,晚风淡淡地吹拂,只有一条长长的影子和他做伴。心沉静了,脑海便波澜起伏。钟鱼回顾自己半生的过往,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话,“怅望卅秋一卅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话原是杜甫说的,被张爱玲改动了一个字,便从“悲家国”变成“悯小我”了。这些日子钟鱼蛰居在家,看了不少张爱玲的书,她的文章第底色是荒凉的,弥散着冷郁、忧伤、孤独和凋零的气息,“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其实荒凉也是一种美,像无边际的沙漠上一棵孤零零的树,掉光了叶子,枝干还遒虬地屹立着,繁芜落尽唯有骨立形销的宿命才是真实可信的。犹如此刻钟鱼的境遇,身陷世俗的漩涡中然而内心已超然物外,无谓炎凉,无欲无求。他很喜欢张爱玲说过的一些话;“生命是一袭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再联想到佛家所说的“一切不留,无可记忆。”更觉人生惨淡。
钟鱼慢慢地走着,漫漫地思索着,不觉来到巷口,歪脖树下,一盏灯光照耀着氤氲的热气,大萍清冷地坐在矮桌前,胳肘趁在桌上,两手托腮眼神呆呆的。钟鱼猜想大约她和自己一样,在这寂静的夜晚思考人生,而且同样看不到希望。
钟鱼看看左右无人,走过去喊了声:“萍姐。”大萍毫无反应,他又提高了声音,“萍姐!”
大萍蓦然惊醒,抬头看看,“哟,钟鱼……这么晚了还没睡?”
“没有。”钟鱼笑笑,“这么晚了你还不收摊?”
“等等看,也许有人来吃……再说回去也睡不着。”大萍恹恹地一笑。
“对。一会儿有下夜班的。”钟鱼点头。
大萍递过一把小凳,“坐吧。”
钟鱼再次观察左右无人后,才坐下来,拘谨地搓着手。
“我看你这么紧张呢?”大萍笑问。
“不是。我是怕现在……我名声……对你影响不好。”钟鱼难以启齿道。
“我是不怕了,只要你不怕就好。”大萍无所谓道。
钟鱼想起两人是一前一后的遭遇,勉强一笑。
“你吃点东西么?我给你做。”大萍说着要起身。
“我不饿,你别忙活了。”钟鱼拦住她。
大萍重新坐下来。一旁蜂窝煤炉上的铝锅静静地弥散着雾气,夜半更深,万籁俱寂,只有风吹树叶的飒飒声,此情此景,两个同样有男女问题的男女相对而坐,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了。
钟鱼搓着手,没话找话道:“你一个人支撑着生意,真,真是不容易啊。”
“有什么法子呢,工作没了。”大萍叹气道。
“我的破工作也丢了。”
“再找也难,人家嫌……”
“没错。破鼓万人捶,墙倒众人推。”
四目相望,同病相怜,眼睛里全是落魄。钟鱼赶紧把目光躲开,转移话题:
“二萍……现在好吧?”
“嗯。工作顺心,家庭和睦,孩子可爱,人也长胖了。”大萍淡淡地笑道。
“二萍算是苦尽甘来了……老天爷把她失去的全补尝她了。”钟鱼感慨良多。
“人这一辈子,有苦就有甜,谁的面前都摆着两杯水,一杯苦水,一杯甜水,先喝了苦的,剩下的都是甜了,先喝了甜的,剩下的只有苦了。”
“我那杯甜水一定让我小时候一口干了。”钟鱼自嘲道。“唉……真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你说那时候咱们,你,我,二萍、英红天天一起,也没什么像样的玩具,却多么开心,一条小小的棬子树街,就能找到无限的乐趣。”
“也不全是开心吧,咱们还打过架呢。”大萍笑道。
“哦……我想起了,呵呵。你和二萍一伙儿,我和英红一伙儿,打群架,结果是不分胜负。”
“我记得小时候你不爱说话,一双小眼睛骨溜溜乱转,不知道琢磨什么。后来就颠颠地跟在英红,你的小媳妇姐屁股后头跑。”大萍戏谑道。
“那,那时候我总受欺负,我妈让她保护我”钟鱼难为情道,“……哎,对了,从前你家门口每天都有屎尿,其实那事是我干的。”
“啊?真是你。”大萍惊讶道,“你可把我们家害苦了,专门养了一条****的狗。”
“今天我正式道个谦,你别生气。”
“生什么气呀。”大萍咯咯笑道,“你可够蔫坏的。现在想想真有意思。”
“我小时候干过不少坏事呢,看他们下象棋,我挤进去放一个臭屁就跑了。”钟鱼也开心地笑道。
“呵呵呵……真有你的。”大萍笑痛了肚子。
笑过之后又觉怅惘。钟鱼叹一口气道:“转眼间就长大了,各奔东西,各走各的路了。”
“是啊。就跟昨天的事似的,转眼间人到中年了,时间太快了。”
“就剩咱俩了。”
“嗯……就剩咱俩了。”
两人相视喟然一笑,黯然无语。一叶棬子树叶轻飘飘落到两人中间。钟鱼抬头望望,感慨道:
“人要是一棵树就好了,落地生根,一年四季自在生长,没有烦恼,没有世态炎凉。”
大萍也偏着头望上去,幽幽地说:“人不是树,毕竟有血有肉。”
“这歪脖树好像变矮了呢,我记得很高似的。”钟鱼疑惑道,“文革听最高指示那会儿,我没少爬,躲搜查。”
大萍扑哧一笑,“我还跟你爬过一回呢,吓得不行……不过得感谢你,让我躲过一劫。”
“那会儿咱们算患难之交。”钟鱼呵呵笑道。
“这会儿……也算。”大萍搓着手说。
钟鱼看她一眼,苦楚地点头,“对……这会儿也算。”
这一天,百无聊赖的钟鱼靠在藤椅上看电视剧《上海滩》。已经是大结局了,看到许文强被长枪短枪一通扫射,殒命街头,忍不住鼻子酸了一回。母亲香华推开院门走进来,手上提着菜篮,面色蜡黄,身体发抖,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粒。钟鱼见状赶紧趿上鞋跑去搀住母亲。
“妈,您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母亲虚弱地摇摇头。
钟鱼接过菜篮,扶她进屋坐下。香华疲惫地靠在藤椅上,手捂着心口,大口喘息。
“妈,您到底怎么了?”钟鱼焦急地问。
“没事儿……就是胸口闷。”
“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那帮长舌妇又戳脊梁骨说三道四了?我找她们去!”钟鱼呼地站起身。
“没人惹妈生气。一点小毛病,不要紧……”母亲制止住他,吃力地从菜篮下拿出一样东西,“儿啊,你看,妈给你买什么了?”
“录音机!”钟鱼眼睛一亮,接过来爱不释手地摆弄着,“……单卡的,这可是新潮玩意……这东西可不便宜,妈。”
“你高兴就好。我看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它,就给你买了一个,心烦的时候解解闷。”母亲艰难地笑道,“……里面还有一盘什么‘瓷带’,我也不懂,售货员说是流行歌曲。”
“谢谢妈!”钟鱼兴奋地来了个拥抱,然后雀跃地跑进自己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