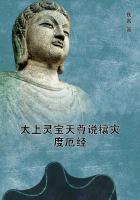他好像没有尽兴:“说起萭章这竖子,那是很早的事了。那时他两位兄长都在京兆尹手下做事,后来京兆尹被人劾奏坐赃为盗,萭章的兄长们也被牵连,诏书命令将他们下长安狱,由廷尉和长安令一起审问。李克当时主要负责审理萭章的两个兄长,在审问过程中发现这两人还和群盗有所勾结。按照律令,凡是勾结群盗的官吏,本人腰斩,家属应当连坐。萭章的大兄萭子卿当初和我有一面之交,我有些不忍,劝李克装作不知道,才仅仅斩了他两位兄长。后来我才听说这位侥幸获救的萭子夏竟然靠斗鸡成了家资千万的富人。”
我笑道,“君况兄实在是侠义心肠,我想萭子夏起码应该把家产的一半分给兄才是。”
“我他妈的才不稀罕呢。”甘延寿好像很兴奋,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他把家产分给了一位叫吕仲的人,这件事我倒是知道的,在三辅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位吕仲不知什么来历,据说也是他的恩人,在太原曾帮他解围,赶走了一批想讹诈他的无赖。”
“那时你正好是太原令罢,自己的辖地盗贼这么多,是软弱不胜任啊?”我又跟他开玩笑。
“少来,我当太原令是后来的事,这可不能算到我账上。”他认真地辩解。
“好吧,就算不是。这个萭章不知道你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否则至少也该把他家产的三分之一分给你。如果你有了三百万的家资,就算纳粟朝廷,至少也可以得个五大夫的爵位。”
他摇摇手:“府君真是小看我甘延寿了,我虽然想做官想得发疯,但是救人不图报这一条还是懂得的。他现在得罪了府君,我就要他好看,你说怎么做,就算是杀他,那也很容易。”
我道:“谁不知道甘君况武功盖世,能挽三石的强弓,百发百中,奔跑速度赛过骏马,杀个斗鸡的竖子还不是手到擒来。但是这个竖子是子公的好友,我答应了子公不杀他。君况如果不嫌麻烦,就帮我查查他还和什么人有来往。我也不是派不出人去做这件事,但是就怕他们莽撞,料想君况你会有更好的办法。”
他得意地笑道:“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一般的人,架不住老子一拳都得被打晕。除这之外,我还学过一点医术,只要吃了我的药,他们肚子里的事,都会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一五一十地倒到我面前。”
我拍掌道:“就知道君况当年任北地太守时,从匈奴胡巫那里抢了很多幻药。如果帮我办成这件事,我真要好好报答你了。”
“一家人,谈什么报答。你就等着好消息罢。”
我正准备审问王黑狗的时候,陈汤来了。
“我刚从西域回来,一下车就往这里赶。”他见我和甘延寿都在,非常高兴,继而又扫了一眼我们面前跪着的王黑狗,有些奇怪地说,“这个人我认识,好像是王翁季的贴身家仆,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对王黑狗叫道,“喂,黑狗,还认识我吗?”
王黑狗翻翻眼皮看了看他:“你是谁?”
“连我陈汤都不认识了?”
“陈汤那个小无赖,我当然认识。”王黑狗道。
陈汤脸红了:“你他妈的说什么,想找打。”我很少听他说粗话,现在被人揭了老底,恼羞成怒了。
甘延寿倒是哈哈笑道:“子公是很会写文章的,怎么也像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一样开骂。”
“这种畜生,狗眼看人低。当年在瑕丘县的时候,他就住在我家附近,这竖子本来是个流民,又算什么好货了。自从投靠了王翁季,就他妈的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陈汤还有些愤然,“咦,这竖子好像喝醉了。”
“不是喝醉了,而是吃错了。”甘延寿笑着纠正他。
我也笑道:“子公,你来得正好,这竖子是君况抓来的,君况给他灌了胡巫的幻药,现在我们想问什么,他就会回答什么。你有什么想问的没有?”
一听见王黑狗被灌了幻药,陈汤的神情似乎变得有些紧张。“哦,原来这样。”他不自然地说,“西域的幻药果然厉害,果然厉害。”他又眯起眼睛,好像在回忆着什么,继而又看着我们,补充道,“没什么好问的,府君你先问,你问完了正事再说。”
我对甘延寿道:“君况你说说看,什么叫正事?难道男女情爱就不叫正事?”
甘延寿道:“男女情爱——当然不算……他看看陈汤,赶忙刹住,“难道子公也懂得情爱吗?我看这竖子倒更像个做官狂。”
陈汤对着甘延寿笑笑:“彼此彼此。”
“好了,不废话了。我们开始罢,等会儿药性过了又要重新一番折腾。”我道。
我们三个人坐到王黑狗面前。我开始发问:“王黑狗,你们家主人认不认识一个叫萭章的人?”
“当然认识,那是陈长年介绍给我们主人的。”
第一个回答就这么可怕,我气得骂道:“难道是陈长年叫萭章来杀我?”
“你,你是谁?”他迷茫地看着我。
甘延寿插话道:“府君,你得告诉他你的名字,否则他不知道。”
“我可不想让王翁季知道我在查他。”我有些迟疑。
“不要紧。等药效一过,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得,比他妈的做梦还糊涂。这是确定无疑的。”甘延寿道。
我点点头:“我叫陈遂,当今大汉朝廷的廷尉。”
“嗯,陈遂我知道,陈长年说了,陈遂那竖子是个伪君子,一天到晚就谋划着要杀死弟弟,谋夺弟弟的家产。陈长年还说,他自小受到节侯的厚恩,一定要保护节侯的幼子平安。”他回答得出奇流利。
我忍住愤怒:“难道陈遂就不是节侯的儿子?”
他道:“陈遂是不孝子,节侯不想让他继承爵位。子不孝,父就可以不慈。孝武帝当年杀卫太子也是这样。”
这竖子懂得还不少,看来在官宦人家做下人,也会长很多见识。
“陈长年怎么能这么说?凭什么说陈遂不孝?”我的肺都要气炸了。
他道:“那是陈遂的父亲历陵节侯生前的评价,父亲说儿子不孝,儿子就是不孝,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好,上次刺杀陈遂没有成功是罢?”
“没有,不过还有下次。”
“下次在什么时候?”我追问。
他很干脆:“不知道。”
“你是王翁季的贴身家仆,怎么会不知道?”
“他没告诉我,不过曾经提到,按照现在的进度,应该快了。”他竟然显得有点委屈。
“进度?”我有些狐疑,“什么意思。”
“不知道。”
这竖子两眼目光呆滞,看来也有可能前言不搭后语。我继续问:“王翁季为什么又要帮萭章杀我?我跟他可无冤无仇。”
“你是谁?”他的两眼又翻白,像奄奄一息的样子,可是说来奇怪,跪坐得却很稳当。
我纠正道:“王翁季为什么要杀陈遂,他们之间有仇吗?”
他道:“当然,我家主君一直很恨陈遂,因为陈遂竟然庇护陈汤那个无赖子,使得我家主君杀死陈汤的愿望落空。而且陈遂最近很得车骑将军宠幸,非常嚣张,我家主君才华远过陈遂,当然也不服气。”
原来如此,我看了一眼陈汤:“子公,看来我为你负累不少啊。”
陈汤拱手道:“深知连累了府君,非常惭愧。干脆我也问一问罢。”
“请便。”我朝王黑狗一伸手。
陈汤对王黑狗说:“为什么王翁季一定要杀我?”
“你是谁?”
“为什么王翁季一定要杀陈汤?”陈汤重复道。
王黑狗回答很爽快:“因为陈汤那小竖子大胆,竟敢勾引我家的小主母,虽然最终没有得逞,但也罪不容诛。”
“王翁季官为京兆尹,想陈汤一个小小的人物,怎么敢勾引京兆尹家的小主母,是不是弄错了?”陈汤道。
“没错,当然那是在瑕丘县的事了,那时我家主君还不是京兆尹,仅仅是瑕丘县长。”
陈汤道:“既然如此,王翁季完全可以去官府告发陈汤,以取公道,为什么要暗害?难道不知道汉法规定报私仇是不允许的吗?”
王黑狗道:“因为王家是官宦人家,怕伤了脸面,只能背地里想办法。”
“王翁季想过什么办法?”陈汤道。
王黑狗道:“我家主人派人杀死了陈汤的父亲陈黑,陈汤必然回乡奔丧,主人准备在陈汤回乡的途中截杀他。哪知陈汤竟然不肯辞官,我家主人于是派人告发陈汤父死不奔丧,并勾结群盗,伤风败俗,大逆无道。陈汤由此下狱论死。可惜功亏一篑,最后被陈遂那竖子救了。真是遗憾。”
陈汤顿时呆了,浑身颤抖:“原来我父亲竟是王翁季派人杀死的。”他突然一把揪住王黑狗,作势欲打,甘延寿赶忙拦住他道:“子公,打他没什么用,打死了反而没法问话了。”
陈汤缓缓点头,怒声问道:“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
“不知道。”
陈汤道:“王家的小主母过得怎么样,据说自从她生子后不久,三辅的大族就很少有人见她露过面。”
王黑狗突然嘿嘿笑了一声,表情显得非常恐怖:“早死了,当然见不到。”
陈汤果然失声道:“什么?你说她死了?”
“她是谁?”
陈汤重复:“王家的小主母是不是叫乐萦?”
王黑狗道:“对,那是她的闺名。”
“你说乐萦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很多年了。”
“到底什么时候?”
“她在小主人过完周岁不久,突然自杀了,死后据说还曾闹鬼作祟呢。”
“一般有冤屈的鬼才会作祟,为什么乐萦会作祟,肯定是有冤屈,乐萦是不是王翁季害死的?”陈汤还想套问。
王黑狗不屑地说:“乐萦会有什么冤屈。我家主人说乐萦因为和陈汤那竖子通奸的事实被发觉,才畏罪自杀的。”
“既然乐萦死了,为什么我没听说王君房再娶妻子。”我看见陈汤的眼睛湿润了。
“因为我家少主对乐萦念念不忘。对了,你又是谁?”王黑狗反问。
陈汤一拳砸在案几上:“王翁季这个禽兽,乐萦很可能是被他害死的。我很了解她,她不是那么轻易想不开的人,尤其在她儿子还那么小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其实她是被你害死的,如果当时你能勇敢点,带了她私奔,又何至于落得这种下场。当然你不会那么做,因为做官才是你的第一渴望。但是觉得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没必要再责备。于是我又问王黑狗:“萭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杀陈遂?”
王黑狗仍是响亮地回答:“不知道。”
这时甘延寿道:“府君,以我的经验,再也问不出什么了,他的确是不知道。不如现在我把他弄回原处,免得王翁季发现他丢失了会起疑心。”
我说:“那好吧。有烦君况了。”
甘延寿站起来,走到王黑狗身后,竖起手掌“啪”的一声往王黑狗颈项上剁去,王黑狗立刻往前一扑,像条死狗一样晕倒在地。甘延寿手臂一伸,抓起他往腋下一挟,说:“我过会儿再来。”说着他大踏步往堂外奔去,转瞬不见了踪影。
有一天深夜,我和罗敷谈起这件事。罗敷有些担心:“这件事越来越麻烦,看来不派人逐捕萭章是不行了。”
我亲亲她的脸颊:“那天我也跟陈汤谈过,我说我不是食言,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是萭章一直想杀我,下次碰到他,我不会再轻轻饶过。”
“那你现在也没有主动出击,发文书派人拘捕啊。”她奇怪了。
我说:“暂时以静制动罢,就当我不忍食言。”
“可是,夫君身为朝廷的廷尉,位列九卿,却要处处躲着一个长安的无赖,未免太好笑了罢。”罗敷趴在我身上,低声呢喃。
我捏捏她的鼻子,笑道:“大张旗鼓地拘捕也不大好。何况我上次受伤的事,当时也没声张,现在我只有暗暗派人去搜寻。一旦搜到,也不用抓来,当场就斩了拉倒。”
她也捏捏我的鼻子,道:“究竟仍是个酷吏,我想夫君也没有这么好放过他们。”
我道:“那是当然,难道我会等他们杀到家里?当然,廷尉府像铁桶一样牢固,他们来了,也只能是送死。至于我们家,没看到最近我又调拨了数十个廷尉吏卒,三班轮值吗?只怕鹳雀也别想飞进来。尤其是你我现在居住的露华堂,更是时刻有人在外围徼巡。”我用手指指月光下的墙壁,除了树影参差之外,上面隐隐闪过士卒徼巡的身影。
她点点头,又叹了口气:“虽然如此,但我担心,守得再牢,也未免会有瑕疵。我看《太白阴符经》上说:‘守不足者攻有余。’到底以攻为守,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我也不由得叹了口气:“可是最近半个月派出的人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下落,难道他们都逃出了长安。”
“也许罢。一个无赖子想刺杀廷尉,未免太滑稽了。夫君,夜漏三更了,睡罢。”说着她突然把我抱得紧紧的,院外正好传来更漏的响声。
我抚摸着她软软的背脊,摇摇头:“那可不一定,你想想,甘露四年,未央卫尉冯不识不就在渭桥上被刺客杀了吗?那刺客也不过是个匹夫,可是极有耐心,他知道冯不识喜欢从渭桥经过,干脆装成乞丐,在渭桥桥洞下住宿寻找时机,最后竟被他成功了。可怜冯不识自身膂力过人,身边又是侍卫环护,却被一个干瘦的刺客取了性命。”
“夫君既然知道,那就不要随便过桥。”罗敷一边说,手一边不老实地往我下边挪去。很快我也有了反应。
我们正在榻上缠绵,关键时刻,我忽然听见身后有异样的响声,不由得停止了动作。
“你听见有什么声音吗?”我侧着头倾听着。
罗敷满脸潮红:“夫君不要太紧张了,哪有什么声音,就算有,现在是深秋,可能是落叶的声音罢。”
我喃喃地说:“也有道理。”
我被她的激情打动,又动作起来。猛然我感觉房间的门被推开了,这次很大的吱呀声可以证明我的耳朵没有问题。
最后的冲刺还没来得及完成,我感觉自己后颈上一阵冰凉,顺着我的脊椎下行。一个声音阴沉地说:“不要动,否则马上死了可不能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