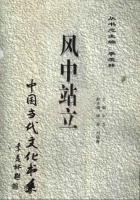丫鬟秋水是个想追求幸福爱情的女子,她不能忍受被陆老太爷******,不甘心嫁给陆老爷做妾,在新婚前夜,把贞操献给与之偷偷相爱的琴师廖玉青之后,两人逃出陆家。但是,她到了廖家之后才发现原来廖玉青已有妻子与儿子。她仍然没逃出做小的命运。也就是说,只要封建男权家族/家庭的伦理秩序还存在,只要男人封建传统的性别观念不改变,无论地位高下的男人都可能以爱的名誉占有女人的性,进而占有这个女人,而女人往往认为这就是男人的爱。秋水的悲剧在于渴望爱却不懂得什么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真正的爱。从女性历史处境来看,家族/家庭是女人遭遇性政治强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最长的私密场所。而且,这种性政治强权是超越种族的、阶级的,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最深处的。就这点而言,整个人类的男权文化体系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尤其值得探究的是,陆氏家族的第二代女人形象陆文荫、陆文芯。“我”的祖母陆文荫,她在92年岁月寻找爱情的生命长河里,渴望得到男人的真爱,疯狂地与自己爱的男人做爱。但是,所有被她爱过的或恨过的男人,都让她尝尽爱与性、灵与肉分裂的耻辱体验。她美丽光华的容颜,风情万种的体韵,燃烧着真诚的性与爱,满足了男人的审美欲、****与征服欲。但是,她无论如何努力终生也没有真正被爱过,没能真正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她有女人独特的生存智慧,无论是对婚姻还是对爱情,她总能主动出击,巧于周旋,从容而退。但是,由于她的自私和嫉妒,把自己的丈夫骗回国又送到监狱,在非常时期为不受牵连与丈夫离婚。为把情人廖思城拴在自己身边,撮合其女儿与之结婚。她品阅社会与家庭日常情感生活里各色变换身份地位的男人,意识到“因爱而性”只是女人一厢情愿,男人是靠不住的靠山。因此,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回到陆家大院里她少年时代的绣房,弥留之际的灵魂,放弃一生对所有男人偶像的膜拜,脸上带着不屑与微笑平静安详地寿终正寝。她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与她顽强的“本我”生命“超越了人们存活的形式,超越了自我的认知,超越了失败与成功,甚至超越了美与善。“她存活着,在生活昏暗的悲伤深处,保留着纯粹的光明;在死亡漆黑的绝望之上翱翔着永恒的辉煌。”
“我”的姨祖母陆文芯和姐姐陆文荫不一样。她因不满意的婚姻与丈夫的弟弟王福义相爱,抗战时期,王福义冒死把她赤裸裸的怀着孕的身体从日本人的刀下救走。“****”时期,在她遭遇革委会主任王虎柱的强暴跳楼自杀后,王福义又陪她一同走向了死亡,多么凄美感人的爱情。而王福义的一句“她是我的”,击碎了所有女人对男人最美好的向往。但是,她跳下楼时身穿象征着与王福义爱情的绿色旗袍,就是以生命反抗以阶级的、性政治的压迫,以死来捍卫爱情,绽放出混沌生活里生命的本色美丽。这是她的灵魂,把情感生活的“疼痛的感知”净化为“灵性”,滋养的生命能量一点一点地拱而破壁,化蝶的飞翔。但是,却仍是一个女人的一厢情愿。
陆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女人,主要是以“我”的姑姑方美彬、姨表姑王静梅和“我”为代表的。与前几辈女人相比,她们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以及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力。她们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越来越觉醒,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情感方式,甚至建构自己想要的爱情理想生活。她们可以选择结婚而建立“丁克”家庭,拒绝做母亲,也可以选择独身生活方式拥抱爱情,拒绝做妻子,还可以选择即拥抱婚姻有拥抱爱情的“情人”。但是,她们追逐钱权的欲望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热衷于享乐快感的情感生活方式,甚至失去道德伦理底线的钱权******,却迎合了旧男权性政治文化的“变相”,新男权文化“潜规则”的等级制,对女性的强权与歧视。比如,陆文荫的女儿方美彬,为了大学毕业能够留在城市,却与母亲的情夫廖思城结婚,廖思城却把她的年轻貌美当成陆文荫的“替身”。当廖思城官势已去,她不想过平常的家庭生活,主动提出离婚而与当时在军管会有权力的王军结婚。陆文芯的女儿王静梅,在“****”中,她竟然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告发相依为命的母亲“私藏金条”。她为了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出卖自己的身体,与年龄能做自己父亲的美国老头结婚,达到目的后一走了之。而在她们的灵魂里,女性主体意识却误入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歧途。
如果说前几辈女人可以用生命的代价渴望得到男人的爱,但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话。这一辈的女人不仅无视家庭血缘亲情,而且决不谈爱情。男人在不谈爱情的婚姻里合法得到了最想要的女人的性,女人在不谈爱情的婚姻里以合法的性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丰厚物质。这样以婚姻的名誉,比傍大款的“情人”身份“物化”得更彻底,还被美其名曰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社会时尚。而“我”陆文荫的孙女方佳瑜,与陆家前几代女人的****观都不一样。她不仅摆脱了对男人的物质与精神依赖,而且有强烈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对于男人是“想走就走,想爱就爱”,感情自由的游曳,甚至还有“****”前卫幻想。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并不满意的婚姻里。其实,这种纷杂的女性情感心理状态,真实反映出消费时代女性的爱与性被商品化之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心灵成长的更加艰难。因为,当下社会的男权性别意识仍渗透在各个文化层面,“精英男性仍占据着社会文化和物质财富的中心,牢牢掌控欲望制高点和话语中心权,居高临下,霸视一切,欲望在倾斜的关系中无限地膨胀。”当代女性在这样的生存文化处境里被物化和自我物化,而失去自我生命的尊严。
如果从小说描述的家族历史的更深处、女性个体灵魂的更深层来考察的话,真正的女性自我主体觉醒,在陆氏家族第一代、第二代女人曾祖母与祖母意识里,是一个“裂开的空白”,而在陆氏家族第三代、第四代女人姑妈们与“我”辈的意识里,却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空虚”。那么,现实社会女性觉醒了的自我,是真实的、理想的女性主体自我吗?女性自我主体生成的文化经验到底是什么?施玮作为一个女作家、女性意识“觉醒者”,发现了女性在理直气壮的表象之下失去“耻辱感”和“尊严感”,在内心里却深藏着迷途的灵魂疼痛、孤独与寂寞。
从小说塑造女性形象的整体结构而言,也许是距离产生“真相”,“我”的奶奶陆文荫是这部小说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其性格的矛盾、复杂的丰富性不仅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有同质性,而且,陆文荫形象对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就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但是,讲述者“我”作为一个线索人物是成功的,而作为陆氏家族的第四代女人形象,对人物的性格内力与灵魂归宿的指向是不明确的。这一点施玮在她的长篇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里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是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番评述的。
施玮在《放逐伊甸》里,把一批“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准诗人,在改革大潮时期坚守自我理想“失重”“焦虑”的群体生命,以宗教信仰的精神“洞照”,发出这群人物灵台深处的真实声音,使其内在精神得以深化、变化与成长,并在绝望的“死亡”中获得重生。这部小说里的李亚与戴航的爱情,赵溟与王玲的婚姻,就是陆氏家族第四代女人情感故事新的演义。而且,施玮的说法证明了我的判断。她说小说《放逐伊甸》里的女性现实生存状态,就是以当时写《世家美眷》时真实的生活为背景的。其实,我在施玮的诗歌全集《歌中雅歌》里,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她在诗歌《以诗为证》写道:“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经死亡,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但是“那一份对爱和真理的‘相信’仍然在我的肉体生活之外存活着。”我认为,这就是《世家美眷》文本之外的那位讲述者“我”的灵魂真相。
而且,施玮与现实生活中的“我”,和那位讲述者“我”继续讲述着“我们”生活现实的故事。她在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里,继续从更深的心理层面开拓女性自我灵魂的成长与觉醒。小说用“红墙”隐喻女性追求纯粹爱情、人格完善与心灵成长的“天路”,以红墙上的每一块砖隐喻人性的自私、欲望、贪婪、嫉妒、仇恨等等。因为自我的种种行为,一块砖一块砖地砌上去,最后砌成了一道不可逾越命运之墙。小说用“白玉兰”象征真爱的宽容。当爱从“占有”的****转化为博爱与圣爱的时候,那一堵红墙就会轰然坍塌。小说用“红杉树”象征女性人格独立和理想之爱的永恒存在。小说精彩描写在于,当女主人公秦小小与丈夫刘如海、恋人杨修平之间的“红墙”崩塌之后,三个灵魂灿烂如炬,相互温暖照亮,每个生命都得到了救赎。男女两性的心灵在情感磨难中得到了共同成长。
因此,《世家美着》《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陆氏家族四代女人的故事。同时,我也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施玮30年创作分量比较重的“女性命运三部曲”。是她把女性意识、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融合在一起,以诗学思维的想象之翼,以“灵性写作”的创作实验,书写女性“生存→精神→灵魂”不同境界,从反思女性命运达到对男权性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尖锐批判。而且,她小说中的一个个女性形象,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灵性”“神性”的人类精神发起者,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处都燃起了一支支火炬,构筑成一个精神通过的巨型仪式,正在飞向真正觉醒的“信仰”极地。正如小说《世家美眷》结尾诗:“死去的祖先们,一个个在遥远的地方,逸若霞烟/被他们说过的话,都像金色的不死鸟,永无倦意地飘翔/它们飞越重重时光不染一丝霜尘,进出于我们的思想。”从而成就着人性的美善,人类不可轻视的光耀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