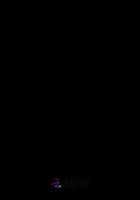小说里的配角章一谆是另一个奇特的成功人物。这位人物是个贪权夺利的卑鄙无耻之徒,但他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好女色,而且女色诱惑当前时,他就把仕途大计放到一边去了。对于这个“嗜好”,作者有荒诞、妙趣横生的描写。其中一个地方写到,章一谆还在任时,有人揭发他和女村民偷情,于是组织上的人去抓他。他得知捉奸的人就在外头之后,不仅不逃窜、求饶,反而要求大家让他把他正在做的“好事”做完再抓人。这恰恰揭示这个人并不把好色当作耻辱,更不像很多男人那样在关键时候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斥责“狐狸精”如何引诱他。这也许是他身上唯一看起来不怎么卑鄙的特点,但其真实原因不是他有“担当”的意识,而是因为他把性能力看作男人的骄傲。他这种性格在临死前更得到放大。章一谆临死前去找自己的情妇发廊女,结果发现发廊女正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一气之下拿起凶器要杀死奸夫,但就在要下手的瞬间,他突然发现奸夫是一个无比雄壮的男人,其男性力量一下子把他震慑住了,他不禁崇拜起对方来,于是丧失了行凶的机会,反而被对方夺过凶器杀死了。从这个人物中,我们就可以领会到芜华十分独特、敏锐的观察视角,她的人物太有个性了,是小说中最夺目的部分。
我不能不说芜华在描绘人物的坏和畸形、矛盾性时更有天赋,她更能抓住“魔界”的“魔气”。相对于刘秀红、章一谆这些光彩夺目的“坏”人物,被当作爱与美的象征、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第一女主人公燕小小反而显得有点单薄了,因为她被作者描绘得太完美了,只有好,没有坏,只有光亮,没有阴暗。我注意到芜华作品的最出色之处不在于她的技巧纯熟、笔法老到,而往往在于她文字中的一股生气勃勃的“魔”力,属于芜华独有的精灵古怪之处。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芜华善于“转变”女性视角,所以她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一样精彩。她写“****”中因好女色落魄的镇长章一谆,写利用单纯的燕小小得到副市长职位的王风,以及一心复仇的章放,都写得淋漓尽致。在几个不同的“坏”男性身上,芜华以冷静、中性的视角和笔调,将蛰伏于男性内心的“根性”东西挖掘出来,把男人们坏与坏的不同、好与好的差别、人性的分裂,表达得极为到位,写出了深度,写出了严峻的格调,这是一般的女性作者不容易做到的。
《魔界》中辽阔的背景、时空交错的手法,以及那种要把社会众生囊括其中的创作宏图,这一切颇有雄性的阳刚气概,但《魔界》在构架上的大手笔和其行文的细腻、感性却不矛盾。芜华的描写大处可以驾驭历史波澜,细处则细如发丝,将看似寻常的情节往深处挖,直到这寻常里不寻常的意义被挖掘出来,或者从看似单色的色彩中分离出种种其他我们不曾看到的色彩。《魔界》感性的语言、女性的视角、具有女性特质的联想,都使它成为一部纯粹的女性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就像作者本身一样充满了女性气质。这充分证明小说的实质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作者可以写同样大的题材,可以跨越历史、俯瞰人世变迁,但他们的写法、切入点、措辞是迥然不同的。这不是说男人就是一定是男性主义作者,女人就一定是女性主义作者。其实,文学史上有不少男性作者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特质,如法国的普鲁斯特,日本的川端康成,台湾的白先勇……谁会觉得《游园惊梦》是一篇男性主义小说呢?
《魔界》中不乏男女****的描写,这类描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部分,很能代表小说的气质和芜华的写作风格。****描写的词汇用得美丽、空灵,具有诗歌特点的联想和比喻层层叠叠,如花团锦簇,但飘渺朦胧,是“花非花,雾非雾”的感觉。我甚至觉得这些描写过于如梦如幻了,禁不住怀疑:真有这么美吗?因此,我觉得芜华心里还住着一个徜徉于梦幻花园的少女,再反观芜华其人,我对这个结论更有信心了:一个50多岁的成熟女性,言谈举止中不时流露出一种少女般的天真神态,尤其开心一笑的时候。所以,芜华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即使她在小说里颇为无情地把现实世界的“魔”展现无遗,不避讳阴暗、残忍、肮脏的东西,但还是在古昊、燕小小的爱情里精心地种植了浪漫与理想的种子。
《魔界》总让我觉得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它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接着写下去,还有一些被作者精心埋下的线索可以生发出新的情节,还有一些在小说最后部分失踪的人物……未完待续,我想这大概也是作者自己的意图。
反思与救赎
——在陆家四代女人激荡情感史的深处
王红旗
施玮,是一位有独特个性的旅美华文女作家。她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诗刊》发表诗歌,至今有诗集《大地上雪浴的女人》《被召唤的灵魂》《歌中雅歌》,宗教诗剧《创世纪》,长篇小说《柔情无限》《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以及圣经中的女人系列诗体小说等等。丰盈的作品蕴含着她对人类社会未来、对女性爱与命运的独特解读。尤其是,她倡导“灵性写作”的创作理念,把“疼痛的感知”锐化为“灵性”、“灵鉴洞照”的书写经验,以历史与问题意识关照社会现实,探索当代信仰危机的“人类病症”的社会原因与心理情绪,寻找人类灵魂深处的“同构性”密码,试图构筑起疗救的大厦的写作实践,在世界华文女性文学文坛上,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位置。
她创作于1996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柔情无限》,经过精心修改更名为“世家美眷”,如今第三次再版。这不仅是施玮给世界华文文坛带来的惊喜,如果从这部家族史小说以女性生存命运为中心的价值而言,我更感觉到出版家关注女性文学的别一种慧眼。但是,我认为叫“陆家的女人们”可能更有历史感。因为,小说的叙述者“我”作为陆家的第四代女人,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口述历史,是一部讲述陆氏家族四代女人,如何忍受、挣扎与反抗封建男权性政治压迫、绽放出灵魂的本源生命与自我尊严的心灵史。
小说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蕴含着施玮反思与救赎的理性批判。讲述者“我”,敢于“说出真相”,敢于还原历史,敢于撕裂男权文化体系以天经地义的方式、以爱的名誉包裹与尘封已久的性政治之网,敢于唤醒活在自己家族史“中心”的女人们的真实灵魂,敢于用心去触摸那一段伤痛、耻辱、却闪烁着生命本色之光的心灵地带。这是一种女性自我生命“我不能忍受我自己”的哲学追溯。正如施玮在解释“灵性文学”内涵时所言:“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灵性的苏醒,文学写作是我对自己挖掘的一种方式,是载我渡向彼岸的船。其次,是希望灵性文学能够把人心中那颗模糊的,被淹没的,甚至是被人有意识忽略的灵魂唤醒。”这部小说唤醒的应该是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男权文化从未正视过的女性内在灵魂光彩,是女性被囿于“家(家族、家庭)”的樊篱内生成的另一种自我生存智慧。
小说的讲述者“我”,对陆氏家族的第一代曾祖母形象的生命遭际诉说的扼腕叹息,对第二代女人祖母陆文荫内心那个不可战胜的自我的高山仰止,都会使人感受到一种女性内在生命的本我力量。她们虽然经历了诸多改朝换代的社会革命,甚至一次次的女性解放运动,但是,革命仿佛都是男人的革命,女性解放运动也没能给予其经验资源。因此,她们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身份,即便在解放后获得了所谓的社会身份,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文化观念的影响,由于都生活在封建男权家庭伦理秩序还在延续着的家族大院,由于自我的“被解放”而自我意识的未觉醒,她们的家庭观念、日常生活方式与情感角色等等生存现状,与封建社会家族妇女相比并没有太大改观。更无从改变或摆脱男权文化性政治的歧视、伤害与侵犯。
陆氏家族的第一代女人形象陆夫人,至死自我主体意识都没有觉醒。她常常押着自己懦弱的丈夫进书房,仿佛是一位强势的主妇。她与自己的状元公爹陆老太爷性乱伦生出自己的儿子,她嫉妒、仇恨与凌辱府里年轻漂亮的丫鬟秋水,是因为陆老太爷对秋水的女色垂涎加骚扰。陆夫人临死前对秋水盛气凌人地问话,揭开了她与公爹之间的感情秘密。但是,最终她怀揣对男权文化命定的性角色的坚不可摧的信念与傲慢,走向死亡,走向那个“认命意识”的慢慢长夜里。因为,按照封建男权家族的伦理秩序,公爹陆老太爷是陆家的最高“家长”,可以向任何家族里的女人以各种手段行施“最高统治者”的性政治强权。而陆夫人在封建男权家族里的一种本源的、悲惨的性体验心理,已经长期内化为一种女人的“自我意识”,即女人生来就是女人,就是为男人传宗接代、为男人****服务的工具,是一位被男权文化彻底“异化”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