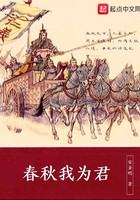工厂进入了停产整顿的时候,他病了。生病之前,他已变得异常消瘦,突如其来的病痛更加重了他每况愈下的身体。一个礼拜后,他已嘴巴开始溃烂,不能吃饭,不能说话。那个时候,活下去成了他最大的苛求。是的,虽然他弄不明白活着的意义在于什么,但他渴望活着、他必须活着,他渴望阳光、空气和会,他渴望妻儿、甚至不切实际的梦里人沈静琴。他的房间里没有医生、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实物,甚至没有最基本的消炎下火药。
就如同呱呱落地的时候一般,他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空荡荡的世界,找不到继续存在的理由,尽管他知道自己必须存在下去。
为了给家里攒钱给家里寄工资,他尽量节省生活成本。他租了成了最便宜的房子。那房子仅能容纳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0元(他工资的六分之一)。月底房东太太多来收房租的时候,发现他病痛已经把他折磨的几近失去知觉。
“去看病吧!”
“给我点水……休息两天就好了!”
房东太太没提房租的事,叹了口气走出了院落。
房东太太走后的第二天黄昏,他感觉身体好了许多,便强忍着病痛从病床上爬了起来。外面火树银花不夜城,各种豪车排着好浓浓的尾气从他身边呼啸而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的忙碌着自己的事情。近来才兴起的迪厅、酒吧或是KTV泛滥着糜烂的彩光。一种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的感觉涌上了心头,对这个世界、乃至自己,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
路过景宁大街的时候,他看到了平日在工厂里耀武扬威的工头。他正给一辆奔驰车开口。两个浓妆艳抹、超短裙、高跟鞋的女郎从车后座走了下来,接着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那人他远远的看到过一次,那是他们工厂的老板。下车之后,他搂着那两个女郎朝着他身边的迪厅走了过来。
他们走过来的时候,眩晕冲上了他的脑门。他撞到了老板拥着的左边的女郎。女郎摸了摸满是污垢的大腿,尖叫了起来。
“嗨,你他妈眼睛长哪去了……”说着,工头一脚踢了过来。
他打起力气,眼巴巴的望着对方,想表达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对方认出了他,缓和了下来,“不是病了,还来这种地方玩……这地方是你能玩得起的?”
他摇了摇头,费力的张开嘴,声音极其微弱的说道:“曹哥(别人这么称呼工头),上月工资发了没?”
“没有”工头有点耐不住气了。
“能不能借我点钱……去买药……”
“去你妈的,没有。”工头失去了耐心。
这时,一言不发的老板在他旁边扔了两张五十块钱,示意了一个工头,消失在了灯红酒绿中。
他费力的站了起来,继续沿街向前走,留下了孤零零的两张孤零零的五十块钱。原本就阴冷潮湿的天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小雨没多久便让原本就潮湿、泥泞的街道更加泥泞了起来。一家诊所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但眼前突然一黑,便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