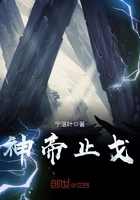川陕交界处有一座横亘南北的大山名叫秦岭,秦岭中有一个无名深谷,谷深七八百尺,四周悬崖绝壁光滑如磨,从谷顶往下看,谷中云封雾罩目不测底,此谷人称无名谷,相传谷底有冤魂厉鬼,每逢夜黑风高之时,便可听见谷底传来厉鬼嚎叫呜咽之声,声声撕心裂肺,让人闻之毛骨悚然。
欧阳妙弋没有体会到,她此刻正昏睡在无名谷底的沙滩上,在她不远处,亦昏睡着一个少年男子,那男子便是大闹丐帮大会夺走打狗棒的那少年。现在打狗棒已不见了踪影,少年怀中抱着的依旧是那根青黑木棒,沉睡在那。那日二人的风筝刚过了渭水便遭遇了一股莫名大风,风筝绳子被刮断,大风卷着风筝刮了三天三夜,把二人活活送到了这无名谷底,若不是下坠时候有风筝的阻力,二人定已经被摔得粉身碎骨了,故都被摔晕了过去,境况堪忧。
这时,一个金黄色的巨大身影朝妙弋缓缓行去,那粗急的喘气声在她眉宇间飘荡,沉睡的妙弋被那家伙弄醒过来,当她睡意迷离,眨巴着大眼睛看眼前的世界时,一张长满粗毛的巨脸吓得她惊叫一声睡意全无,她花容失色弹身跳起,没头没脑在沙滩上发足狂跑,那金黄大影原来是一只金钱豹,它见妙弋飞身逃命,立时发出怪鸣,拔腿飞追上来。
妙弋哪跑得过它?饶是一个壮年男子,也未必是这巨大豹子的对手。只见妙弋已吓得哭出声来,她平生见过最大的动物无非山下农户家养的牛马,可这野豹,乃是不通人性的杀生动物,想必它已把她当成了猎物,这么穷追目的就是要掠食她!这么想着,妙弋不觉脚下被一块石头一拌,身子趴塔一下跌倒在地,那豹子刚好赶到,飞身一扑跳了过来把妙弋按在爪下,血盆大口一张,迎着被吓得快要窒息妙弋脖子一口咬去,妙弋心想这下死也!说时迟那时快,但听身旁一声暴喝,一人闪电般扑身过来,握拳捶向豹子大脑袋,那只手因收不住势,竟深深插进了豹口。
豹子嚎叫叼着那人在沙地上滚打了起来,那人正是沉睡的少年,他亦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的,他醒之时刚好是豹子准备咬妙弋脖子那刻,千钧一发不容多想,便扑过来相救。怎料此刻他右手已经插入豹口,只得搂住豹颈,双腿紧紧夹在豹腰之上;豹子喉咙被他拳头卡住无法合下嘴来,拼命在地上打滚想甩脱少年,少年却像胶一样愈夹愈紧,任它怎么折腾也甩脱不掉。
二十多圈后豹子动作逐渐慢了,因为它气管被少年堵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很快巨大的身躯瘫成了一堆烂泥,伏在地上一动不动,少年使劲抽出了自己的手,满手尽是豹子唾液闻着奇臭无比,少年皱眉往衣服上抹了抹,看身上无碍,向那吓傻在地的漂亮女孩走了过去。
“你还好吧姑娘?”少年蹲下身问妙弋,但却不凑近,他吃过这女孩拳头,此时还有些害怕。
妙弋心有余悸,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当然不会有多好,现在她哭得像个泪人儿,那日的泼辣早荡然无存,现在更像一只小猫,可怜楚楚,她摇头,像还没回过神来。
少年安慰她道:“放心吧,有我在,那畜生伤不了你。”
“呜哇。”不料他刚话毕,妙弋哭声却更大了,她边哭边用脚去踢少年,像使小性子还强辩:“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那么不要命,你难道不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人家人情吗?”
少年哑然,无奈回:“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若知道,打死我也不会救的。”
“你敢,你若敢眼睁睁看着我被那畜生吃了,我做鬼也会回来吃了你。”岂料她又这么说。
少年一时哭笑不得,这救也错,不救也错,你倒是要让我如何?
妙弋在又哭又闹之间,肚子却“咕咕咕”叫了起来,这下她立时捂着肚子,尴尬地看了少年一眼,哭声止住了,羞红脸低下头去。
少年见她这般,正想发笑,谁知自己肚子也不争气地擂响如鼓。
妙弋忍不住噗嗤一笑,莞尔看着少年:“你刚才还想取笑我,自己的声音比人家还响。”
少年无奈地看着面前这女孩,她脸上有一双稚气的,被长长睫毛装饰起来的美丽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葡萄,那张小嘴蕴藏着丰富的表情,高兴时,撇撇嘴,扮个鬼脸,生气时,撅起的小嘴能挂一把小油壶。
这女孩是不是天生是水和阳光的结合体,前一秒还数九寒冬,后一秒便阳春三月,想到这,少年只得叹女孩的心思,是最难琢磨的。
他回话与妙弋打趣:“我自然饿了,刚才与那畜生拼命不饿才怪,不像某些人是被吓饿的。”
妙弋小嘴一扁,捏拳头在少年面前晃了晃,威胁到:“你再敢取笑妙弋,小心又让你吃拳头。”
少年最怕她那拳头,吐了吐舌头,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妙弋也只是吓吓他,她不会这么快就对自己救命恩人动拳头的,她忽然想到了什么,拍了一下自己脑袋:“哎呀,这么半天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傅夕歌。”少年答。
“唷,好大气的名字,谁给你取的?”妙弋歪着脑袋眨眼问。
傅夕歌说:“我自己取的?”
妙弋奇怪的问道:“你自己给自己取名字?”
“很奇怪吗?”傅夕歌反问。
妙弋吐了吐舌头:“那你猜猜我叫什么?”
傅夕歌头也不回,直接答:“欧阳妙弋。”
妙弋大奇,脸上满是惊讶表情,她说:“怎么可能,你我第一次见面,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名字?”
“切。”傅夕歌白了她一眼,道:“你自己刚才自报了家门。”
傅夕歌得意的扯了扯眉毛,显出几分高傲的神情,让飞雪看得甚是不爽:“臭美吧你,我以为你是神人,原来你不过记性好一点而已,但并不代表你在本小姐面前可以张狂就算你再厉害,在我欧阳妙弋面前,你永远只能做一个挨拳头的臭小子,明白否?”
她这话像套了枷锁,想一辈子把对方扣在她那温柔的小拳头下,傅夕歌心中一动,顿觉眼前这姑娘不但可爱而且还很天真,此时他不禁想起那小村的竹林里和师妹的那一个勾手指。
想到这,心中顿感索然无味,世间再美好的感情总敌不过现实之苦恼,也不知那苦命的师妹,现在在哪,今生还能有缘再见吗?
傅夕歌四下打量这绝谷谷底,面积大约几十丈,谷底有一水潭,而他们所处的位置便是潭边的沙滩之上,谷崖石壁上长着一些低矮树木,这四面崖壁光滑得如同打磨过一般,就算猴子都难攀上去,四十余尺开外的树丛上方,挂着一大块红毯布,显然是风筝的一部分,被撕得不成样子挂在那里随风飘弋。
看这样子二人倒抽一口凉气,这个绝谷显然没有出口的,若非长了翅膀,就别考虑出去了。
“看来我们得在这里生儿育女,相守终老了。”傅夕歌绝望的开起了玩笑。
妙弋白了他一眼,反斥:“可以啊,你可以跟它生儿育女啊。”她纤指指向瘫痪在不远处的豹子,想回击取笑傅夕歌,目光不经意瞄向豹子,吓得一声大叫,兔子般跃到傅夕歌身后,浑身颤抖口齿不清,显然已经吓得不轻。
原来那豹子已经缓了过来,傅夕歌忙捡起木棒戒备着,把妙弋护在身后。此时那豹子摇晃着爬了起来,转过那颗硕大的脑袋,两只铜铃般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他们,不过眼神里却没有了杀意,还隐约有了惧色,人豹对峙约摸半刻钟,豹子见他们这边无异动,晃晃悠悠拖着沉重的步子,向不远处的水潭爬去,想必刚才与傅夕歌打斗时候失水过多,此时要去喝水解渴。
躲在傅夕歌身后的妙弋,贝齿紧咬大气也不敢出,脸紧紧藏在傅夕歌背心,心脏快要跳出来。其实傅夕歌比她还害怕,他明白刚才自己误打误撞才弄晕这庞然大物的,如果平地上放开了,六个男人也未必是它对手。
豹子郁闷的走到水潭边,饱饮一通水后体力似乎有恢复,它又回头看了看那边的二人,还不甘心但又怕被傅夕歌弄晕,它又在水边徘徊了一圈,忽然水里的一个东西吓它一跳,正想逃回岸上可为时已晚,只见潭中腾起一满身鳞片的怪物,张开锯口一嘴咬住了豹子的腿,顿时水花乱卷,两条怪物在水中一阵翻腾,那豹子被那水中长着四条腿的满身鳞片怪物拖进深水处去。
豹子发出一声哀鸣,最后哀求地看了一眼与它对望的傅夕歌,像是在向他求救,而后整个被拖进了潭水中去,傅夕歌心中一震,突然脑顶冲血怪叫一声,着了魔般提棒跳进了水潭。
妙弋一时呆了,她以为傅夕歌是发疯了,那两只畜生相斗与他何干?竟跑到水里凑热闹,是不是嫌活得太长了啊?但她只有着急的份,因为她已拉不到傅夕歌了,慌乱之中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上別着一把短剑,她忙拔出短剑拿在手中给自己壮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