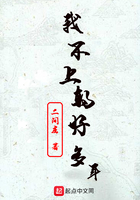“嗯,是的,‘乐于时傅’的于,渔网的网,生蛋的生,我今年7岁,家住渔村,我爹说我是他7年前一天夜里用渔网捞起来的,他又姓于,就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糊弄我说我是渔网生的。”
“哦,呵呵,是于网生,人不可能是渔网生的,尤其是你这聪明伶俐的孩子。你口中的爹,可是父辈?”
“嗯,说是爸爸,可他又老又丑又凶狠,爱称自己‘爹’,我就叫他‘老爹’了。他一点都不疼爱我,每天只会叫我干活……”于网生说到这里,想起过去种种不幸,眼角又积攒起泪珠,不住地往下涌。
“原来如此,你被爸爸抛弃了吗?”老人从于网生模棱的话中推测他的遭遇,由是关切。
于网生对此并不愿过多的提及,直接就转移了话题:“老爷爷,您喂给我吃的、还有身上贴的是什么神奇的药?雪莲还是灵芝,肚子、身体怎么会好得那么快呢?”
“呵呵。”老人摇摇头,端起桌上那碗浓香的面,抚抚于网生的额头,让他平静吃下,才渐而回答他的问题,“这面汤用到了香砂六君子,益气健脾,和胃降逆,你呕吐的症状,表面上是胃纳不佳、脘腹痞闷,实则是因为倦怠乏力后暴食引起,方才送进你嘴里的那粒药丸也是如此制法,本来药效并无如此之好,只因你体质极强,些许芍药即可缓解,再敷予杏仁、栀子、红花、蝉蜕磨制的消肿散,休息片刻便觉得容光焕发、病症痊愈。在老夫看来,这世上珍贵神奇的药,不是那冰原上的雪莲,也不是那绝壁上的灵芝,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这个药一旦发挥作用,会挽狂澜于既倒,救膏肓返平安,这就是——爱。”
“爱?”于网生擦擦小嘴上的面汤,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生活的这些年里,你生了什么病,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连你最亲近的爹都没有做到基本的照料和呵护,几乎可以说是随你自生自灭,只管你是否有干过他布置的任务,因而你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许多,却因为长期干重活而比同龄孩子坚韧许多,可是连基本的照料都让你受宠若惊,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你的爹是个丧心病狂的人,一种是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不是?”于网生对于这个答案露出惊讶的一面,而内心此时却是尤为爽朗。
“所以与其说你是被这药治愈的,不如说是坚强的你体会到了从没感觉过的爱,而振奋自愈。”老人拿出纸巾,帮于网生擦擦嘴,面露出莫名的哀愁,“孩子啊,说了这些,老夫对你还是理解甚少,我觉得,像你这样流落无助的孩子若是落在那店员手上,最多也只是皮肉之苦,而落在像我这样的人手中,你岂不是要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会呢?爷爷对我这么好,怎么会害我?”于网生更无法明白这话的意思。
老人言语低缓,意味冗长:“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任何不能杀死你的只会令你变得更强,对于那个店员的打骂,可以当作是一次教训,以后不吃不新鲜的食物既可避免,而像我这样莫名其妙对你好的人,他们表面上对你呵护有佳,让你感激涕零,也许心里在惦记着该把你卖到哪里才好,或者干脆就地拿走你身上值钱的器官,不日,你便生不如死。”
“啊——”于网生吓得一下子坐在地上,害怕地大叫出来。
“哈哈,别怕,我虽然把你带到这儿也是有目的的,可不是要拐卖你,拿走你的器官。”老人欢笑着扶起于网生,觉得他的情绪特极端,一会儿感动,一会儿惊颤,好有些童趣,“说起来,我跟你之间还是挺有缘,你啊……和他真像。”
“他……是谁?”一阵惊悚过后,又是云里雾里的,让一贯寂寥的于网生好不习惯。
老人没有回答于网生的话,而是从一旁的背包里,拿出两条米黄色的斗篷,一条是于网生穿戴过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另一条是和这条一模一样的崭新的,于网生一见了那斗篷面色立即变得铁青。
“孩子,是我的一个朋友,叫欧阳千爵,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手里还抱着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当时没有毛毯,他就把儿子用你身上这样的斗篷包住、捆绑起来,带着妻子消失在了人世,后来听说,他们都死了,而儿子却失踪了,那是7年前的事,假如他儿子还健在,那么就有你这般大了,而且,我知道他的儿子左瓣臀上有一块碗口大的椭圆深红胎记,你的臀上恰好有这么大一块,位置也对,今天若不是那店员撕破了你的裤衩,恐怕我就不会那样注意、要错失这次天赐的机遇了。”
于网生拿过老人的斗篷,细细观摩,双手竟颤抖起来,他有一种预感:他的命运,将会在今天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斗篷,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老爹说过,捞起我那会儿,我身上就绑了这斗篷,老爹说这件斗篷可以防水,就拿去改做雨天的蓑衣了。”
老人一听于网生这话,变得很激动,蹲伏下身子到于网生面前,拉着他的双臂,于网生可以清晰看见老人的泪充满了他晶莹的锐眼,“若世上没有那么巧合的事,那就错不了了:7年前一天夜里你在渔村被你爹用渔网从塘里捞起来,那时身上捆绑斗篷;我朋友和妻子就在那段时间的夜里死在你们那村子附近,那时他绑有斗篷的幼子刚好失踪;你和那孩子有相同位置和大小的红色胎记,除此之外,老夫目测你和孩子的父亲极为相像,尤其是和他一样如同针叶一般的薄嘴唇……如此一来,恐怕你就是那个小孩儿了,你的亲生爸妈因为什么原因将你遗落在那塘中,恰巧你爹在塘中捕鱼,万幸地救了那本来要溺死的你!”
于网生一语不发,老人揭示他命运的论断虽然头头是道,但他显得并不高兴,对于他这个孤独的小渔夫来讲,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会有许多的事实还需要等待他去适应,比如他期盼见到的从未谋面的父母,在得知他们的存在时,他们却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样的命运更迭,没有亲情从中洗礼,其他的再能变化,又有什么区别呢?
“孩子,爷爷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你了,找你找得好苦啊……爷爷很想见一见你那个老爹,或可进一步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于网生,不知你爹现在何处?”老人却异常高兴,像重逢了痛失很久的孙子一样,不断用亦哭亦笑的面容,表达内心的复杂。
于网生轻轻摇头,他自己都无法料想,在一个童年被折磨扭曲的七岁儿童心中,天真无邪成了表现,而伤痛迷惘却成了本能,这是一个儿童不该有的体味,是世人容易忽略的现象,如果仅用“坚强”二字来概括这种孩子的特征,那无疑永远也进入不了他的内心世界:“老爷爷,您不用找他了,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了。”
“为什么?”老人是那种迫切地想要得知一切的眼神,于网生看着老人的眼睛,看他一个白发彬彬的老人,眼睛却是如此的清澈明亮,这样的目光在深深吸引着他坠入深渊的晦暗童年,也许是同情老人与自己相同的那种挖掘命理的渴望,也许是厌倦了看不到未来的惨淡现状,他欣然倾诉了这些年的痛楚和包括今天的这段时间发生的连串事件,然后等待老人给他的批命亦或新生。
老人的模样又是哀愁的,看样子他听得很认真,似乎把于网生的遭遇当成了是自己的遭遇:“很难想象你一个七岁的儿童可以做出这么翻天覆地的大事,爷爷尤为敬佩!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欧阳千爵在少年时,也是如你一般英勇,只可惜天妒英才,他就那么早逝了……”老人说着,竟又见于网生跪了下来,连忙搀扶,劝阻道:“哎呀,你是英雄好儿郎,膝下有黄金,不可在给我这个不中用的老朽跪下了。”
“于网生已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但求能做爷爷身边的杂役即可,让我干什么都行,若是爷爷不同意,我就跪着再也不起。”想着亲人已不在世上,于网生便视这老人为唯一的亲人。
“傻孩子,你可知道你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侄子,即便万一不是,你小小年纪就这般有为,将来必定堪可大用,可不忍你再受不公的苦难!”老人心痛地抱着如获至宝的于网生,不准他再下跪。
“那爷爷您是同意了?”
“嗯,只是……”老人不知为何,很是犹豫。
“只是什么?”
“只是爷爷不是这尘世的人啊,你要是跟了我,必定要吃非一般人能承受的苦。”
“不是这尘世的人?”
“是的,说来话长,此处也不是说话的地方,现在还为时尚早,你走得动吗?我想带你出去叙叙。”
“我没问题的,爷爷,咱们走吧。”
二人离开茶馆,牵手的背影有那么些温馨,同时也掩藏着其他复杂的气氛,因为于网生和那个老人,此时都在想着不一样的事情。
他们慢慢走在了不夜城的海鲜小吃街,这里的游人大多都被山珍海味引诱去了,情景热闹非凡,没有人可以注意或辨清他们的谈话。
“老爷爷,既然我会是那个小孩,那我的爸妈又是谁呢?”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看着一家家相亲相爱,于网生迫不及待想知道关于自己亲人的一切。
“直接说,你不会明白的,咱们慢慢聊,聊到那,你自然就知晓了。”
“哦……老爷爷,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爷爷我小的时候,也是孤儿,那时比你还惨,连个管饭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也没有名字,惯用无名作称号,你以后就叫我无名老爷爷便可。”
“嗯,无名老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