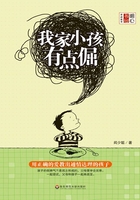“怎么不对劲儿?”我问。
“你这么聪明的人,没看出来么?”梆子一着急脑门上就爱出汗,这又是一头,“你看见了,现在下着这么大的雨!”
“是啊。”我点头。
“他!”梆子想大声喊,又怕外边的人听到,压低声音:“他就这么进了你的家门。”
“不是,外边下大雨和他进我家门有什么关系?”我问。
“雨啊!”梆子竟然口吃起来,“雨!雨下这么大!你看刚、刚才送外卖的人!淋的!”
他说到这儿,我突然间也意识到了,江虎和外卖员几乎是同时到的我家门口,江虎身上一点也没湿,而外卖员却淋得像个落汤鸡。外边狂风暴雨的,这个江虎甚至连把伞都没拿,这么说,他一早就在我家的楼道里了,那他会不会是歹徒?
“他不干净。”梆子小声说。
“什么?”我没太反应过来梆子的话,“他不是挺干净的么?就是太干净了……”
“不是,他是那种不干净!”梆子继续说着,刚说到这儿,就被我一下子打断:“去!”
我是彻头彻尾的非惟心主义者,所以梆子这些鬼啊神的在我这儿根本行不通,我也最烦他说这些个东西,让人听完毛骨悚然的。
就在我们俩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谈下去的时候,天晴了。
“我回家了。”梆子连饭也没拿,直接拎着包就走了。
我跟着他从卧室出来,看到江虎还老老实实地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着我。
“那个,江虎。”我走到他跟前,他对我微笑了一下,拿出一个信封:“一万。够不够?”
接下来,就是我二话没说地收了钱,然后把他领进我和卢丽丽中间的那间卧室。
天渐渐黑了,我坐在卧室里,点了根烟看网页,没听音乐,怕吵到两个房客,不过这两个人都特别安静,几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那个卢丽丽进了屋就再没出来过,江虎也是,我都有点儿奇怪他们不上厕所不洗澡么。
晚上看了个无聊的电影,紧接着是我爸从南方打来电话,问了问我最近身体如何,店还顺利不顺利,一切可否安好,都是客套性的,其实可能不认识我的人想不到,我爸我妈都是鼎鼎大名的房地产商,几乎各个城市都有我们家的楼盘,也许是我爸教子有“方”吧,可能听着这话说得有点儿自夸,他除了把我养大之外,其它的东西都和我分开,房子我自己买,做生意,本钱借我,还的时候还要利息。
其实我也没当什么二世祖,说白了,我爸我妈的企业做得再大,我从小是一点儿便宜也没占,和一个双职工子女没什么两样,现在我经营的小店的钱,早就连本带利还干净了,别和我提赞助,就连“股份”都没他们二位的事儿。
因为我从来没考虑过他们的钱和我有关系,所以也许我们现在还维持着相当美好的父子关系吧,他们两个人在我面前就是单纯的父母,其它的就再也没有了。
眼下我爸我妈正在湖北开发一个旅游项目,听说山青水秀的一个地方,具体的我没问,只知道是个度假村,钓鱼湖还是什么的,这样的地方,您打开旅游网站大的小的中国能有一大堆,我觉得吧,像这种无聊的场所,要么就是固定的一批人去,要么就是根本没人去,当然了我也没钱去,所以根本也就没多想。
关上电脑的时候已经挺晚的了,喝了杯牛奶躺下,打开空调往被子里一钻就睡了。
这一觉睡得很特别,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这儿第一次住了两个陌生的房客,或者我们还没有过什么深刻的交流,二是我好像没有做梦。
习惯性地按上手机,把那段闹铃关掉,我从床上起来,顺手就把枕头下的“日记本”拿出来,刚要落笔却突然间愣了,梦呢?
本来就不太清醒的我一下子就傻了,对啊,梦呢?我常做的那些被人数落的梦哪去了?想了大概有个五分钟,我把日记本又塞回了枕头下边。慢慢下地,刚想光着上身出门,一想不对,家里有别人,还有女的,随手抄了件T恤衫套在头上,穿了条裤子,打开卧室的门。
“金先生,你起来了。”
我一抬头,江虎正围着围裙站在我的客厅里,这一下让我莫名其妙了起来,还真没见过这样租房子的,跑我这儿当钟点工来了这是?
“江虎?你这是?”
“我早上去跑步,路过市场就买了点东西回来做了早餐。”说完把围裙一解,光着上身坐到桌边,“顺便把您的也做出来了。”
江虎这小伙子身条很不错,人长得也标志,就是办事儿有点儿二。我走到桌边看了看。就两个碗,一个还在他跟前儿,你说这屋里住了三个人,哪能早点就做两人份的,而且人家还是一个姑娘,你一个男的,光着膀子也不太合适,又不是熟人。
“江虎。那个。”
“怎么?”江虎抬起头,看了看我,“蛤蜊汤。”
我一看可不是,大早晨起来,煮了一盆儿蛤蜊汤!还有各种水果切的块儿,这丰盛的。
“江虎,你回去再套件衣服,旁边那屋住的是小姑娘,一会儿人家起来看见你光着不合适。”
我说着就往厨房走:“我再给她添副碗筷。”
“金先生。”江虎叫了我一声。
“我没比你大几岁,叫金天就行了。”我说着接着往厨房走。
“金天,邻居家住着女孩儿,也看不见我光着上身啊。”
我说这江虎二人说二话吧,回过头,指着卢丽丽那屋的门,小声说:“不是邻居,这屋里住的是一个女学生。”
江虎直愣愣地看着我:“这屋?”
“啊,这屋。”我点头。
“这屋没人吧。”江虎眉头一皱看了看我。
我一想,确实,江虎不知道这屋住着人,不过他昨天来的时候我好像也和他交待过我还租了一间房子出去。
“有。”
“没有。”江虎看着我,“里边是空的。我昨天晚上没听见房间里有动静。”
“什么?”我听他这么一说,白毛汗都出来了,这不胡闹么!赶紧走到卢丽丽房间的门口,敲了几下:“卢丽丽!卢丽丽!”叫了几声没人答应。
“坏了,是不是出事了!”我心里有点儿起急了,这要是这姑娘在我这儿上了吊还是自杀了,我以后也甭住这儿了,就说赵伟那儿的人靠不住。
我推了推门,门没锁,但里边的插销是栓住的,这证明她这个人还在屋里!我大喊了几声还是没人应,我心想豁出去了,那卢丽丽要是生病或者昏过去了,也不会计较房东一大早就把她的房门撞开。
我一分钟也没耽误,绻起胳膊撞到门上,一下就把那门给撞开了,还没等我定睛看上一眼,一股烧焦的气味传出来,把我的鼻子呛得要命,我下意识的用手在鼻子和眼睛前边搧了搧,睁开眼睛,没有黑烟,定睛再一看,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包括卢丽丽的行李和她这个人,没有了。
还没多久,一股恶臭就传出来,闻着好像是坏了的牛奶一样,混着刚才的焦味,一起袭击我的鼻子。
“这什么味啊!”我回头看江虎。他一脸严肃地站在大门口,门已经打开了。
“不知道。”江虎站在门口摇头,大门打开大概是他想通风。
“那个女的不见了。”我走进卢丽丽的房间,急急地把窗户打开。但是半天那股味儿也出不去。
江虎摇了摇头,走到餐桌跟前,想再去吃那些东西,但这一屋子的臭味已经把食物的香气给盖住了。不论是谁现在对着美食也下不了筷子。
我到顾不上吃饭,直接拿出手机给赵伟打过去。
“喂,昨儿那个哥们儿去了吧?”赵伟接起电话先问我。
“哪个哥们儿?”我问。
“就是昨天上午我和你说那个外地的研究生,叫,你等会儿啊!”我听见赵伟好像翻了翻本子,“江虎!”
我回头看了江虎一眼,道:“来了。”
“你看要是没问题,过来我这儿签合同吧。”
“他都住这儿了。”
“住这儿?你说他住你家了已经?”
“是啊。”
“老兄,这程序不对啊,没事没事,你过来我这儿补合同,我回来把合同给他再签一份。”
听赵伟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愣了,对啊,合同应该是我和赵伟签的啊,可是昨天的卢丽丽怎么和我签了,换句话说,我怎么能做为房东直接和卢丽丽签了合同,要是这样,那个中介的刘小姐算是干什么吃的,这不符常理啊。
“哎?老兄,在不在?金天?”
“啊,我听着呢,那什么,赵伟,昨天你不是还介绍一个人过来了么?”
“昨天?没有啊。昨天我上午打了你的电话,然后告诉江虎你家的地址让他自己过去看一下,我昨天下午一直在外边办事。我这儿人手也不够,所以就让他自己去的。”
“那,那昨天下午你不是让一个刘小姐带着一个卢丽丽过来的么?”
赵伟一听,停了几分钟:“金天,你没开玩笑吧?”
“没有啊!”
“我们单位没有姓刘的女的,连姓刘的都没有!妈的这他妈是谁这么可恨,敢锹老子的客户!”
“赵伟,我昨天下午明明给你打过电话,我和你说我这儿来了两个人,你还说是你叫他们来的。”
“不可能!”赵伟有点生气了,“金天,你一间房子租给别人不要紧,你也别编这种瞎话啊,你是我客户啊,还是我朋友,你不从我这儿走单,我难道还能吃了你么?”
“你听我说完行么?”
“你说。”
“我能理解你现在生气,但是你听我说完你就不气了,这个女学生昨天搬过我家的,然后今天早上人就不见了。”
赵伟又安静了一分钟左右:“我靠!哥,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啊!赶紧看看你们家少没少东西!妈的,最近倒霉事儿全让我赶上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才反应过来,真是疏忽,很可能那两个女的是小偷,挂了电话赶紧就在屋里翻了一通,什么都没少,客厅里就一个电视机值钱,安安稳稳地摆在那儿,其它的东西都在我屋里,存折现金一分没少,我昨天刚进的平板电脑也就撂在床边,纹丝没动。
江虎坐在沙发上,餐桌上的东西已经全扔掉了,他看我忙里忙外的一通,问道:“你找什么?我帮你吧?”
“噢,不用。”我看了看他,“你不用上课么?”
“不用,我得过了夏天才有课。”江虎说完继续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猴子一样在屋里上窜下跳的,他却安稳地像只高傲的波斯猫。
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屋子里什么也没少。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我拿出一根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事?”江虎问我。
“就是昨天来的那个女的,一下子不见了。屋里的门还栓着。窗户也是关好的,不可能跳楼啊。”
“这屋子昨天我来的时候是三个人。”
我一听,马上问他:“三个人吧!你刚才怎么说就两个!”
“另外一个男的,不是我来之后没多久就走了么?”江虎反问我。
我一愣,他说的是梆子:“你的意思是,昨天晚上,这屋里就咱们两个人?”
“是。”江虎点头。
只有两个人,这是江虎给我的肯定答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明明昨天他来的时候,屋子里是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