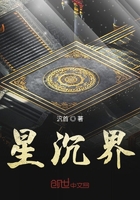北京和上海的比较,一直以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问题,熟识这两座城市的林语堂对此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我们且来听听他的说法。
京沪岁月
在中国,除了自己的家乡之外,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对林语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样对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也是如此。如果再细比这两个城市,上海对林语堂的“眷顾”似乎要远远超过北京。
林语堂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假如没有在圣约翰接受到当时中国最好的英文教育,恐怕也就没有后来“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林语堂在圣约翰杰出的表现传到了附近的圣玛利亚女校,其未来的妻子廖翠凤听说后对他心生仰慕,这也成为他们俩缘分的导火线,可以说,上海又间接给了林语堂婚姻。
此后,于1927年到1936年,林语堂又在上海居住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大作家,创办《论语》等刊物让他名声大噪,《开明英文读本》等的出版又让他财利滚滚,包容万象而又气象万千的大上海让林语堂成了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英雄。
1936年,受赛珍珠之邀,林语堂带着一种功成身退的成就感离沪赴美,当时码头上几十名各界人士拿着花篮为他送行,让他感受到无限荣光。
反观北京,林语堂在这座城市待的时间不足上海的一半,留下的不堪回忆却何止上海的一倍?彼时的北平尚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的腐败和专制让林语堂触目惊心,反动政府枪杀请愿学生更是给林语堂一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相比上海,林语堂离开北京的方式也有点“灰溜溜”,据林语堂《自传》自述,1926年,狗肉将军张宗昌长驱入北平,枪杀两个最勇敢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同时又有五十个长期与军阀斗争的教授进入黑名单,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消息传出后,林语堂带着家眷东躲西藏,并在一个早上拖家带口悄然离开北京。在北京的岁月里,林语堂最为人称道的成绩只是加入《语丝》战斗,并被鲁迅引为“革命同志”,可惜这充其量只是在别人的旗帜下摇旗呐喊,比起在上海的自成一家境界迥然而异。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对林语堂百般眷顾的上海在他眼里竟然犹如地狱,他不断地批判上海,痛骂上海,仿佛这是一个欠了他很多钱的无赖,就连他的女儿林太乙在许多年后回忆父亲时也感叹道:“父亲憎恶上海。”而北京,这个毫不留情地把林语堂扫地出门的城市,反过来在林语堂眼里成了天堂,他不仅写了《动人的北平》《辉煌的北京》等作品来歌颂这座城市,而且在言谈举止中处处表现出了对这座城市的偏爱,乃至于他最重要的小说要写“京华烟云”而不是“沪上风云”。
性格双城
时人研究林语堂对京沪两座城市的爱憎,最后总要总结到文化二字。而我个人认为,文化这样的字眼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我更愿意从性格的角度来解读林语堂对待双城态度的由来。
林语堂热爱北京的“慢”而厌恶上海的“快”,在他眼里,北京是自然的而上海却是功利的。
“在北京城的生活上,人的因素最为重要。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腔调上,都显而易见的平静安闲,就足以证明此种人文与生活的舒适愉快。因为说话的腔调儿,就是全民精神上的声音。”北京人的悠闲让林语堂颇为欣赏,他在《京华烟云》里把北京描述为一个田园与都市的合体,“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时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内,城市生活极高度之舒适与园林生活之美,融合为一体,保存而未失,犹如在有理想的城市,头脑思想得到刺激,心灵情绪得到安静”。
田园的北京,安静的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这里的人们从不快步疾走,甚至连黄包车夫在拉车的时候也要彼此边走边开玩笑。北京人安逸而又知足,他们在四合院里种上花,提着鸟笼和鸟儿一起漫步,地上有落叶也不一定及时打扫,坐在竹椅上或是杉树下的藤椅上,喝一下午的茶才悠然回家,这样的生活让崇尚慢节奏的林语堂大呼过瘾。
而此时的上海,笼罩在“远东第一大城市”以及“冒险家的乐园”的光环下,十里洋场莺歌燕舞,物欲横流。无数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汇聚到上海的人们熙熙攘攘,脚步匆匆,为了追逐名和利甚至没有时间坐下来喝一杯茶。对此,林语堂在《上海颂》里面略带惊慌地描写道:
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东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它那浮面的虚饰,在它那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在它那空虚,平凡,与低级趣味。上海的可怕,在它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劳力,乏生气的报纸,没资本的银行,以及无国家观念的人。上海是可怕的,可怕在它的伟大或卑弱,可怕在它的畸形,邪恶,与矫浮,可怕在它的欢乐与宴会,以及在它的眼泪,苦楚,与堕落,可怕在它那高耸在黄浦江畔的宏伟而不动摇的石砌大厦,以及靠着垃圾桶里的残余以苟延生命的贫民棚屋。
此外,林语堂热爱北京的“和”而厌恶上海的“乱”,在他眼里,北京是和谐有序的,而上海却一团乱糟糟。
在《动人的北平》里,林语堂描述北京的一团和气:
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与着木屐的东北老妪并肩而行,北平却不理这回事。胡须苍白的画家,住在大学生公寓的对面,北平也不理这回事。新式汽车与洋车、驴车媲美,北平也不理这回事。在高耸的北京饭店后面,一条小路上的人过着一千年来未变的生活,谁去理那回事?离协和医院一箭之地,有些旧式的古玩铺,古玩商人抽着水烟袋,仍然沿用旧法去营业,谁去理那回事?穿衣尽可随便,吃饭任择餐馆,随意乐其所好,畅情欣赏美山——谁来理你?
在北京,达官贵人和引车卖浆者彼此相得益彰,旗袍和西装并行不悖,古典与现代共存,高雅和低俗同列,这样的北京包容万象,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合适而感兴趣的活法,以至于林语堂认为任何一个人在北京住上一年半载就无法离开它了。
而在上海,到处可见的却是一幅光怪陆离的景象,声色犬马之徒横行其道,人们为了利益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在这里,林语堂看到的是趾高气扬的外国人,肥头胖耳的银行家,狐假虎威的洋场买办,油嘴滑舌的旅馆茶房,满身脂粉气的小开,以及越来越排外的新上海人。乱世容易出英雄,也容易出流氓,而这两者在上海往往又合二为一。这样的上海是赌徒、政治家、商人、投机者的至爱,而在崇尚单纯的林语堂看来却是糟糕之至。
在林语堂的眼里,北京像一个历尽人世沧桑的老头,他饱经风霜而能够洞察世界,他老成温厚,与世无争而又带着几分超脱老滑,他因循守旧但却因此能知足常乐,这也正是林语堂所一直赞赏的中国人的性格。而上海,简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小伙,他进取心十足,却在名利面前迷失自我,不知所措;他对生命有极高的热情,却轻率,浮躁,对天地缺少应有的敬畏之心,不够厚重;他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却也因此躁动不安,被欲望所俘虏。
林语堂所描述的田园而诗意的北京,在许多现代作家的笔下我们都可以发现其踪影,老舍、郁达夫、梁实秋等人都不吝笔墨歌颂了这样一个适合生活而又充满情调的老北京,令我们重温他们笔下的北京时都会充满一股悠然向往之情。然而,这些大师若能重生,再回今日之北京,必被气得七窍流血。林语堂更是无法预料,今日之新北京与他笔下昨日之老上海何其相像!
图片上如此惊心动魄的堵车场景在今天的北京并不罕见。如今的北京已不见了林语堂笔下的田园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油烟味。当四合院和胡同渐渐被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所替代,当马车和驴车变成现代化的汽车,当老外可以坐在故宫里喝咖啡,当行色匆匆的人群闪过音乐厅和博物馆,我们发现,如今的北京城已经失去它的韵味和特质,渐渐被现代文明所同化,只剩下一些历史的骨架还在苟延残喘。
何止是北京,如今的整个中国都有变成停车场和工地的趋势,全国各地都笼罩在一片拆旧盖新的亢奋情绪中,一座座规划中的新城正在拔地而起,谁也不在乎它们会不会在某一天变成传说中的“鬼城”。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人们正在倡导和推行一种环保的上班方式,鼓励大家用走路和自行车代替四个轮子的汽车,前者正在成为发达国家一种新的时尚。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像当年林语堂所批判的美国人,而现在的美国人却越来越像当年林语堂所歌颂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