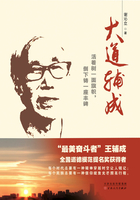《苏东坡传》的英文原名为“The Gay Genius”,意为“快乐的天才”,当林语堂遇到苏东坡,两个快乐天才的相遇碰撞出了夺目的火花。
两个快乐天才
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厦门的中学时期,在寻源中学读书时他已经开始系统地阅读苏东坡的作品了,而这样的热爱还将贯穿他的一生,并与日俱增。
1936年,林语堂赴美写作,他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随身携带了一百多种关于苏东坡的研究资料,并为此忍痛割爱放弃了许多其他的珍本古籍。这些研究材料也构成了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主要资料来源,剩下的就是他个人的记忆了。在当时,囿于条件,林语堂不能像现代的作家一样广泛地查阅各种资料,他能够写活千年以前的苏东坡,靠的更多的是个人对苏东坡的拳拳之情。
《苏东坡传》的英文原名为“The Gay Genius: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意为“快乐的天才——苏东坡的生活岁月”,可见作者认为快乐到了苏东坡这里已经臻于化境了。林语堂说“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一样过了一生”,像风一样轻快和自由,不可捉摸又永远清新,一直行进永不停滞,这就是苏东坡的快乐精神。
林语堂认为苏东坡这种快乐精神来源于其元气淋漓的生命力,“他身上有一种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遏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有力地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欢笑才停止。”(《苏东坡传序》)
快乐的林语堂与快乐的苏东坡金风玉露一相逢,自然是充满了惺惺相惜之情,所以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讲道:“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乃至于在为其作传时竟不惜用了“曲笔”。
譬如研究苏东坡二十余年的学者东方龙吟就认为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许多地方都在臆造苏轼的经历。其中最典型的一件事是:苏轼终身都在暗恋他的堂妹,为此还专程到镇江探望她。东方龙吟认为这是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误读,他把苏轼两封信里所说到的苏辙孙女“小二娘”和苏轼堂妹“十二娘”混作一谈。而这样的“误读”居然是有意的,原因是林语堂想借苏东坡之“酒杯”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寄托他对陈锦瑞的相思之情。
我觉得东方龙吟的提法很有见地,因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类似的事情苏东坡自己就干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记载了苏东坡20岁时应进士考试时做的一件荒唐事,为了论证贤君唯才是用,他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试卷上杜撰了这样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尧曰宥之。”当时的判官梅圣俞阅卷时虽然心存疑惑,但又不敢发问,怕因此被人嘲笑自己知识浅薄,苏东坡遂侥幸蒙混过关,高中进士。后来在一个私下的场合,梅圣俞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就此问题向东坡询问,苏东坡笑着说:“是我所杜撰罢了,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梅圣俞听了,不禁目瞪口呆。
这一种“想当然”的做法,绝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狡黠,而是一种陶渊明式的“不求甚解”的自然与随意,这也是快乐天才的标签。当前,有学者对林语堂的“错误”义愤填膺,专门写了《林著宋译苏东坡传质正》来驳斥此事。
行云流水的人生
苏东坡有一段论作文的话千年以来一直为我们所击节赞赏,他说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林语堂对此也深表赞同。
其实,“行云流水”又何止是苏东坡的为文之道,他的为人之道何尝不是如此?
苏东坡一生于宦海浮沉,大起大落,但他始终如滴水随浪花般跳跃,淡定自在。在党争激烈的国都开封,苏东坡屡次请求外放,希望以此摆脱政治漩涡,但政治漩涡却一再无情地将他吞噬。他曾经是锦帽貂裘的太守,也曾经是刑部大牢垂死的罪犯;他是当朝被贬距离最远的士大夫,可是在海南岛上他却异想天开地欲“食阳光止饥”,快乐得像个小孩子;他今天还官居二品,明天却已沦为七品之下,屡屡遭贬,却屡贬屡赴,屡赴屡安;自欧阳修之后,他已是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可他的文章却不时被查禁。
后来,苏东坡曾经感慨万千地概括自己的人生:“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牢骚过后,他都学会了坦然处之,不以为意,就像流水一样,在奔行途中遇到阻碍,并不强求一定要越过,而是换个方向,继续且歌且行,在这个途中他也渐渐大彻大悟,终于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和苏东坡一样,林语堂的一生同样颠沛流离。他少小离家,老大也没有机会再回来,行踪漂泊,走的距离比苏东坡还远。不过林语堂的行走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这是他幸运的地方,但也造成了他的生命体验远不如苏东坡深刻。林语堂的后半生大部分于美国度过,美国在很多人眼里宛如天堂,但在中式的林语堂看来始终不是宜居之地,他待在美国只不过是想在乱世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写作之地,后来也证明了林语堂的选择是睿智的,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全是用英文写就。如果没有美国,也就不一定有今日之林语堂。
1944年,林语堂曾一度回到重庆,但旋即又返回美国,此举被许多人诟病,指为“懦夫”,“士可杀,不可辱”,这对一向崇尚丈夫气节的林语堂来说简直是难以容忍的。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后来林语堂在美国宣传抗战取得了巨大的效果,被国民政府授予荣誉勋章,对他的非议才渐渐平息。
如果当时林语堂选择留在国内,只不过又多了一个爱国的典型,但很快会被人们忘记,孰得孰失,不言自明。所谓“常行于所当行”,此之谓也。而当人至晚年,台湾的现状也渐趋稳定并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台当局此时又恰到好处地向他抛出橄榄枝,林语堂认为一切已经瓜熟蒂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在美国半生的功业,立即卷起铺盖去往台湾,这又是“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样的人生当然也是行云流水般的人生。
行云流水式的人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不强求,不固执,顺其自然。林语堂年轻时被迫与至爱之人陈锦端分离,他既没有借酒消愁,更没有为爱跳楼,而后在与陈锦端截然不同的廖翠凤相处时,他照样其乐融融。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一下子给苏东坡戴了一二十顶的帽子,而这段话的精华在于其以“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开头,以“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收尾,它最终聚焦于东坡的旷达与乐观的品质上,这也是苏东坡带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岛的时候,当地缺医少药,他却写信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如果依此类推,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庆幸了:没钱买房,不用当房奴;没钱买车,不用担心油价高涨;老婆长得丑,不用担心她有外遇;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这一点苏东坡已经替我们解答了,他在50岁时老来得子,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写了一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当我们为疯长的肉价菜价而苦恼时,或因升职的压力而焦虑时,不妨看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它的确是一剂疗伤的良药。
林语堂曾经提出了一个作家间的“灵魂转世”说,他说:“苏东坡乃是庄周或陶渊明转世,袁中郎乃是苏东坡转世。”如果苏东坡在现代还能继续转世,那么承接他的灵魂的非林语堂莫属。世上的传记何其多,而好的传记又何其少,盖因作者与传主的气质品性相差甚远,未能达到心有灵犀的境界。从这一点来看,苏东坡和林语堂都是幸运的,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则更为幸运。
最后,以最能体现苏东坡旷达精神的《定风波》为本文作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